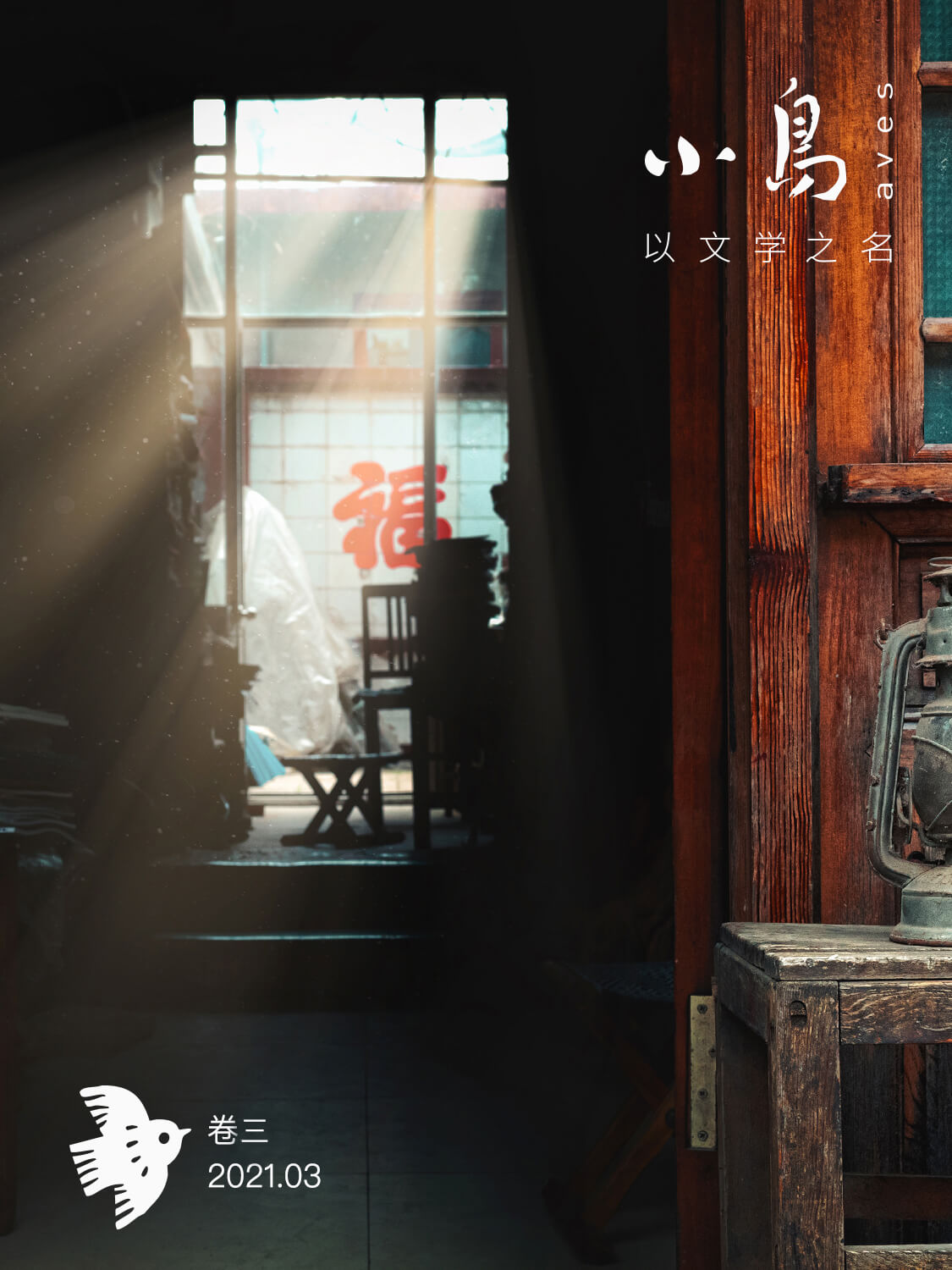都说艺术没有目的,听得多了,信七八成;但你总觉得,就算艺术没有,艺术家不像是一群没目的的人。一个很重大的目的,似乎是造出一样东西,让它精致到别人误以为是一段未经雕饰的生命体验。就像拉金,问他诗歌是干嘛的,说是用语言让一个不认识你的人感受到那个促使你写诗的感受,然后用了两个押韵的字假装不容置辩:preservation by recreation,用重塑去留存。阿里斯泰尔·麦克劳德讲道理就朴实得多。采访者问他,若是读者觉得你写的都是自传,说“我敢打赌这些都是真事”,你怎么想?麦克劳德宽宏大量地应付道:这是我辛辛苦苦想要达到的效果,就是要让读者觉得这些事真的发生过;当然有些人后来发现它们是编的,会不开心;就像你画了一个苹果,别人以为是真的,上去咬了一口,说这根本不是苹果的味道啊,你只好承认,这苹果不是真的,心里偷偷得意,他居然当真了。
但要细究麦克劳德的苹果存在学,似乎又是很直白的功课。矿工家庭,长在农场上,父亲铅中毒,骨骼钙化,三十几岁身体就垮了。麦克劳德从小发现自己会读书,一路读到本科、硕士,都在加拿大东岸,然后去美国印第安纳州拿了个博士学位,论文做的是哈代,然后在大学教了三十多年的文学、写作,直到退休。不过,读书时候,他又很喜欢放假去伐木、捕鱼、开矿,就这样挣出学费;后来当老师,有课的时候他一般也不写,只等长假回到新斯科舍,每天清早出门,半山小木屋,迎面动人心魄的景致,平均下来,差不多一个夏天一个短篇。1999 年出了一个长篇,叫好叫座,赶紧把他的所有短篇结集出版,一共才十六个。这些故事的主题连同那部小说,有种执拗的同心协力,感觉就像一个摄制组到了麦克劳德的新斯科舍布雷顿角,在那个渔民矿工社群里把镜头对准了不同家庭而已。麦克劳德写那种生活有种混不费力的逼真、接近苦痛的深情,写它如何追溯到十八世纪末苏格兰人如何不得已离开故土,写这种生活如何承受当代变革的重压,写新的一代人身份散佚带来的迷惘。
麦克劳德生活和文学间的对应,不承认是没有意义的。但如果只把好文学看作一个信达雅的译者,那是既高估了文学,又小瞧了它。写作不是那么理所当然的。生活的样貌,生活的内核,都不会那么心甘情愿地听任你编排成字母和笔画。生活必须经历与生活分外相关的种种化学反应,才产生好文学,我们的任务是探测它如何发生。
麦克劳德文学最上乘的地方,在我看来,与他生命最深层一丝如鬼似魅的“不好意思”纠缠在一起——或许称不上羞耻,但至少是某种歉疚。他总写现代人想摆脱那种闭塞、严厉的生活;但别处的快乐,一眼也没让我们瞧见过。只要跨出那一步,就是无边无际的迷失。《船》是麦克劳德写成的第一个故事,可能也是最有名的。我们都记得里面写了一个爱看书的父亲,牺牲小我,成全家庭,但短篇开头,读者还瞥见“中西部一所了不起的大学”的一个失眠的老师,被这种无忧无虑的重复生活简直逼到活不下去。拿我们了不起的现代化的价值观去看,初读那个故事,总觉得母亲像电视剧里的反派;她凭什么非要孩子再活一遍她的人生?年轻的叙事者背离父母,念文学去了,小说当然没有怪罪他,但我们也明确无误地感觉到,故事把更多的敬意留给了父亲——“花一辈子去做自己厌烦的事,比永远自私地追逐梦想、随心所欲要勇敢得多。” 读了足够的麦克劳德之后,一个丝毫不认同其他任何生活方式的母亲,似乎也很让人暖心。
麦克劳德只写过那一个长篇,新版译作《布雷顿角的叹息》,开场是一个牙医开车去见他酗酒的兄长。整部小说基本都是闪回,所有麦克劳德的主题不断变换形貌扑腾组合,现代和传统的冲突,苏格兰族裔的悲怆历史,家族的纽带和个人的身份怎样由传说和故事编织,等等。要说这本书有个情节梗概,应该是从一场童年悲剧开始的,几个兄弟姐妹活下来,人生自此开始分岔。其中的一个就是叙事的牙医,在某种可见的意义上,他算是走出了那个阴影。毕业的时候,除了似锦的前程,他还拿到了一个夏季的科研项目。爷爷说,以后你再也不用干活了。但一个血缘很近的表亲在矿井底下掉了脑袋,于是他放弃了一个吉祥如意的夏天,去顶替充数。“红头发的亚历山大·麦克唐纳死了,关于他的死,我也意识到某种负罪感;虽然不确定自己该在其中承担什么罪责”。那种朦胧的不自在是因为时间上不凑巧,那位表亲高中结束下了矿井,我当然可以说服自己,那是他自认为不是读书的料,但这种选择不也是这个地域世代相传的穷困所逼迫的。那场光鲜的毕业典礼一结束,载我回来的这辆车,说不定两个后轮就是靠他起早贪黑买的。我时常想到当年他摸着我的后脖子,说我父母早就不在了,“运气不错”,他手上的老茧和我脖子后面竖起的汗毛永远粘在了一起。
后来,有个美国亲戚为了躲避越战征兵,潜入加拿大,藏在自己的族人中干活,但偷了敌对族群的一块手表。酒吧斗殴,那个酗酒的哥哥为了保护这个小偷,失手杀了人,判了终身囚禁。现在,他保释出来,已经成了酒瓶间的一个废人,小说开始,“我”就是要去多伦多的一间廉租房找他。宽厚如麦克劳德,不可能去审判主角的人生选择,但对牙医这个工种,整本书从头至尾飘荡着一股质疑,觉得不是什么正经的行当。花费一辈子给富人装点门面,有种说不出的荒唐。而那个醉醺醺的哥哥则成了某种象征,像是他们血脉在现代世界碾压下仅存的那点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