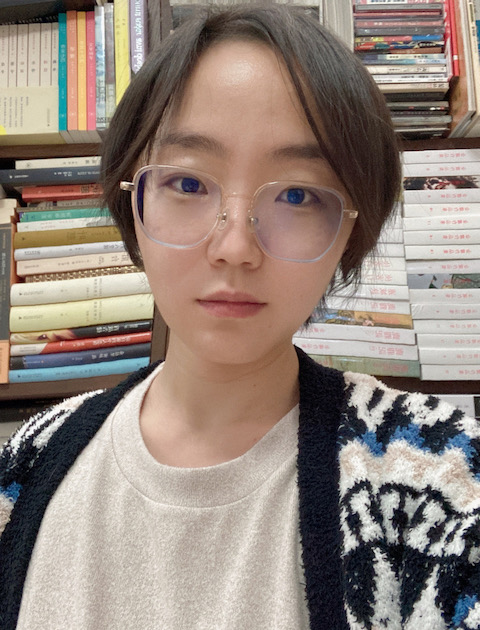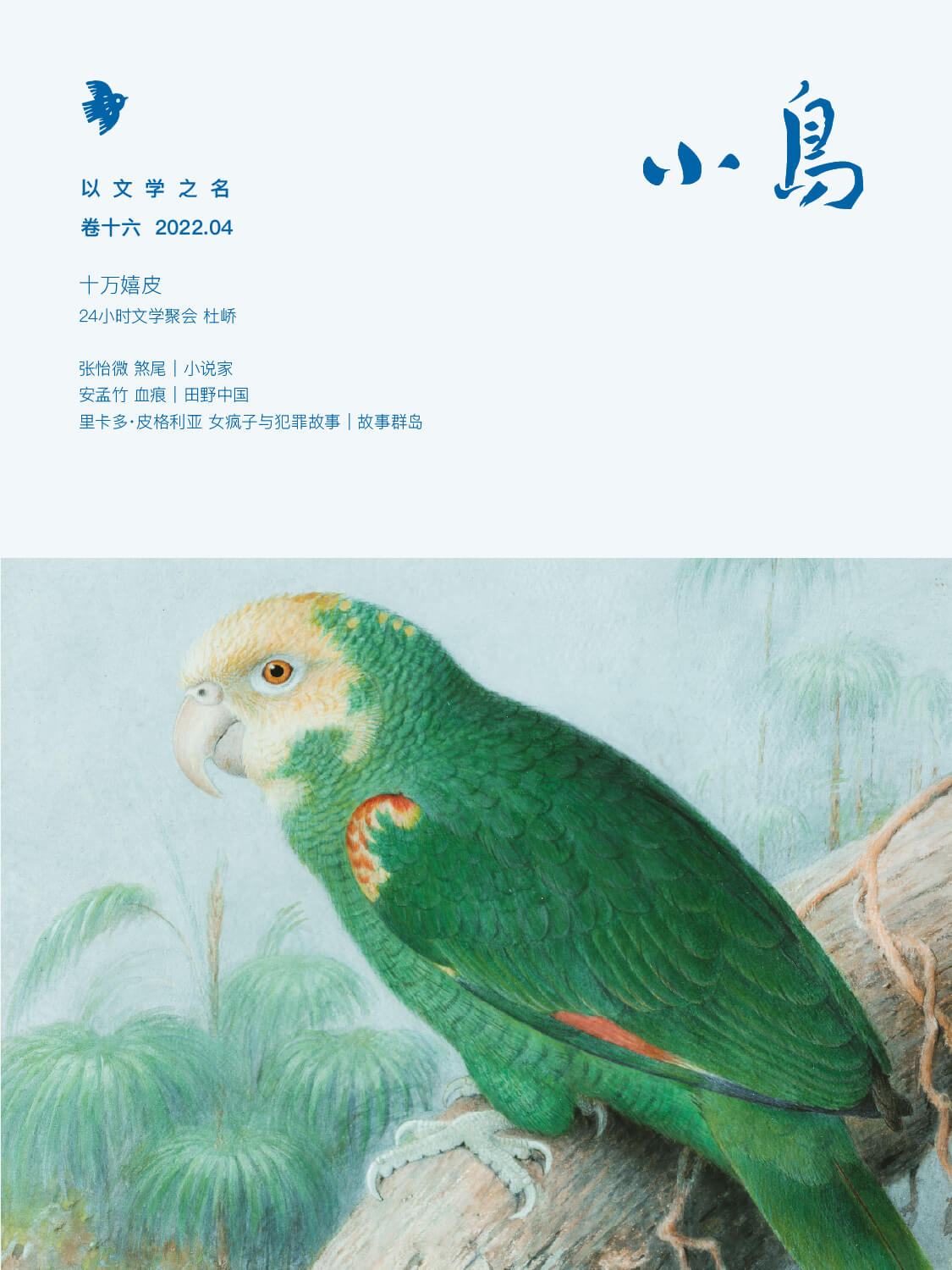01
纠纷
“你听说了么?机构里出了打孩子的事,家长微信群昨天晚上‘炸了’!”
一大早,和我关系最好的小段老师就跑来传递“情报”。我听得瞠目结舌,还没从田野倦怠期里重新振奋起来的自己,一时不知如何应对这桩突如其来的大新闻。
2017 年 9 月,我从香港中文大学来到位于珠三角的彭城,开始进行关于自闭症家庭养育实践的博士论文田野调查。这家我称为“向阳干预中心”的民办特殊儿童康复机构是我田野的起点。向阳干预中心成立于 2000 年初,坐落于城市北部一栋旧式公寓楼的二层,低矮的教室一间挨一间,挤在走廊两侧,昏暗的灯光下,墙上动物图案的漆色已经有些剥落,乍看之下,这里像是一间硬件条件不怎么好的幼儿园。但这并不是一间普通的“幼儿园”,这个空间所服务的,是一群被诊断为自闭症、唐氏综合征、脑瘫、智力障碍、多动症、发育迟缓的“特殊儿童”,其中自闭症占了绝大多数;为他们提供康复训练的则是像小段老师这样的“特殊教育老师”,简称特教老师。
小段老师是河南人,严格来说还不算一位真正的特教老师。她在贵州一所师专读特殊教育专业,比我早两个月来到向阳干预中心进行毕业实习。我则是在这间康复机构里“做研究”的常驻志愿者。在这个空间里,我和小段老师都被叫做“老师”。我每天穿一件印有“义工”字样的红色马甲,和那些拿到了康复教育上岗证书的“真”老师们一起,在教室里辅助孩子们上课,课下带他们去厕所,午餐时给孩子们喂水喂饭,忙里偷闲时一起聊八卦、吃零食;在稍显平淡枯燥的日常中体验着老师的工作,时日渐长,自己也对“老师”这个群体有了归属感。当小段老师告诉我康复机构里发生了“老师打孩子”的事,我的第一反应是错愕、震惊——这群相识已久、已经成了朋友的人,怎么会对孩子施加暴力?!
中心的气氛明显不同于往日,窸窸窣窣的议论之声在教室内外流窜。已经在这间机构工作了两年的李老师掏出手机,为前一天请了假的我补充这场“伤害事件”的背景。她滑动微信群里的聊天记录翻出几张照片:其中一张照片里,一道暗红色的血痕划过手掌,肉嘟嘟的手心里,破了皮的地方还在微微渗血。另一张照片里,白皙的手臂上印着一块暗紫色的淤青。
受伤的孩子名叫丁晓珍,再过几个月就满 18 岁的她,严格来讲并不算是个“孩子”了。事情爆发在前一晚。晓珍妈妈突然在中心的家长微信群里贴出几张“伤痕照”,指控大龄班的陈老师打了晓珍。这位在孩子身上发现不止一处伤口的母亲恼怒不已,她隔空质问中心的老师们“是不是在长期虐打晓珍”,声言如果机构给不出满意的处理,就要把这件事在网上“曝光”。
面对家长言之凿凿的控诉,晓珍的班主任蓝老师赶忙出来解释,说晓珍胳膊上的淤青是上周末秋游时摔的,并不是“长期遭受虐打”的结果。晓珍妈妈却并不买账,她言辞激烈地回应道:“没那个资质就别碰我女儿!以后谁再打我女儿我就打他!”
伤痕照似是铁证如山,晓珍妈妈的语气也信誓旦旦、不容置疑。群里其他家长开始纷纷站出来声援,帮这位母亲向机构“讨说法”。终于,干预中心的负责人、正在外地接受培训的杨主任发话了:“晓珍妈妈说的是怎么回事?大龄班班主任请好好调查这件事,给家长一个交代!”
家长责难,领导施压。蓝老师不得不再次道歉,承认自己看护的失职。她向晓珍妈妈保证,一定会把晓珍受伤的原因调查清楚。群里一位家长跟着附和:“一定要好好调查,让我们家长放心!”
今天的中国城市里,面向特殊需求儿童的康复和教育机构已经不像十几年前那样稀缺。在彭城这样资本不断涌入的淘金之地,康复市场的急剧扩张反倒伴随着另一重隐忧。进入田野之前,我曾在网上看到过许多关于特殊需求儿童在康复机构遭遇暴力伤害的新闻。这类报道大多将暴力事件发生的康复机构描述为利欲熏心、缺乏行业监管、乃至非法经营的存在。然而向阳干预中心是一间经过彭城残联认证的康复机构,这里的老师们经过了数次职业培训,谙熟主流的干预方法。在这样的机构遭遇如此严重的伤害纠纷,的确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面对我这个“外人”,谨慎的李老师并未就晓珍妈妈的指控发表看法。同为班主任的她只是对蓝老师的处境颇感同情。李老师一面收起手机一面叹息,“闹大了,蓝老师可惨了”,我却难以压抑心中的一连串疑问:晓珍到底有没有被打?晓珍妈妈为什么如此笃定女儿身上的伤来自陈老师?如果说,晓珍胳膊上的淤青确实是秋游时摔的,那道掌心的血痕又是怎么回事?
02
晓珍
被怀疑遭受虐打的丁晓珍,是整间干预中心年龄最大的自闭症学员。在干预中心,晓珍被老师们戏称为“老丁”。中文里,老丁的“老”字不仅代表年纪和资历,也是一种亲密的揶揄。“老丁”被老师们叫惯了也不生气,总是笑眯眯地和每一个在走廊里相遇的成年人打招呼:“老师好!”。
“老”字用在晓珍身上或许并不过分。从向阳干预中心成立之初,年幼的晓珍就成为了在这里接受康复训练的一员。因为在这间机构的年份超过了许多年轻老师,晓珍有时也会被调侃为“干预中心的元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