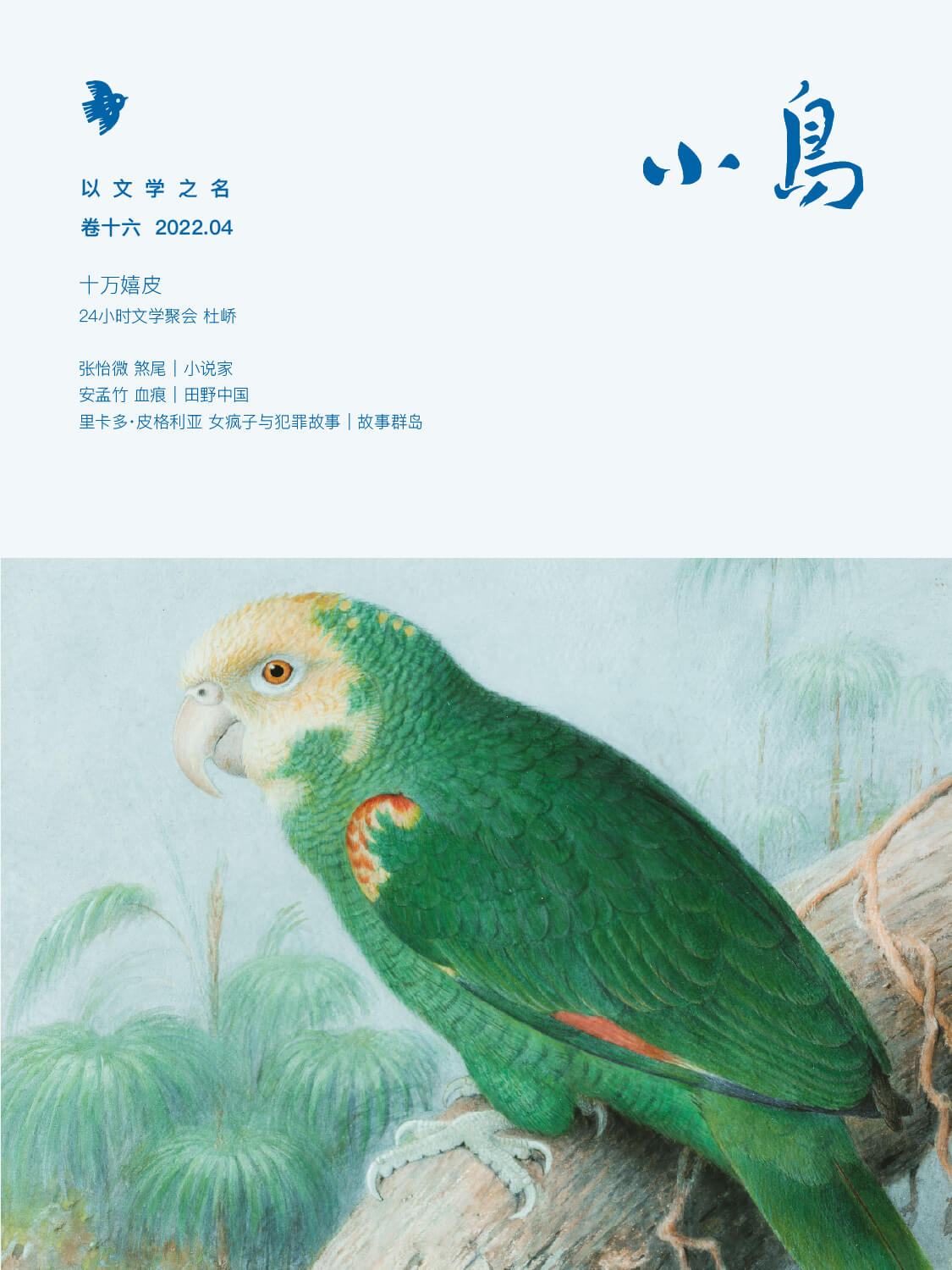面对性,一个女人所能做的最无趣的事之一就是同意了。可近来,我们看起来更喜欢谈论男性的侵害而非女性的情欲。
一方面,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谈论性伦理的时候,人们会最先想到有无同意。在一个性犯罪如此常见(可悲地,在美国,每六个女人中就有一个是强奸或强奸未遂的受害者,并且 81% 的女人都遭受过某种形式的性骚扰)的文化中,人们难免要关注强奸和性侵。
不过,至少和性强迫一样常见的,还有空洞的同意。仅仅是经过同意的性不会带来内心的痛苦,但这样的性就和仅仅是可以下咽的食物一样让人提不起兴趣,就和没有糖霜的蛋糕一样乏味。甚至在我们表面上“解放”的时代,女人也面临着各种外部强加的、她们自己不安地内化了的情感和社会压力,被逼着以牺牲自己的享受为代价取悦男人。
异性恋的女人一直在许可激不起她们兴趣的关系——这也许是因为她们已经绝望了,觉得不可能有像令人兴奋的男人那样的东西存在;或者是因为她们甚至不再坚持这件事情必须随兴;又或是因为整个社会都在预期她们向让人提不起兴趣的男人低头,而通行的关于浪漫的描述也总在美化这样的迁就。
就像出色的牛津大学哲学家阿米娅·斯里尼瓦桑在她的处女作论文集《性的权利》中写到的那样,她的女学生经常跟她说,她们认为自己的情欲生活“既不可避免又不够”。简而言之,斯里尼瓦桑课上的年轻女性向她们同意,但索然无味的性屈服了。
谁又能怪她们呢?当代几乎没有人会教、或者鼓励女人要有性趣,要主动地去要。在公众的想象中,她们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被动地同意、接受或拒绝男性的提议;在最坏的情况下,还会沦为色狼的不幸的受害者。在这幅图景中,性的能动性主要被留给了玩弄、捕猎女人的男人。
#MeToo 运动把注意力集中在是否同意性要求的女人,而非主动提出性要求的女人上,这点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难怪运动的支持者几乎从来不问这个问题(当然,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是出于策略的考虑):对女人来说,什么样的性才是“好的”(我的意思不是“道德的”,而是“可口的”)?在什么条件下才会有好的性?
今年连续出版的几本书提出了这些遭到忽视的问题,敦促我们审视我们的欲望和不满的政治和社会根源。2021 年 3 月,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创意写作教授凯瑟琳·安吉尔出版令人激动人心的《明天性又会好的》。5 月,芝加哥大学著名哲学与法学教授玛莎·纳斯鲍姆出版了《骄傲的大本营:性侵害、问责与和解》。9 月,斯里尼瓦桑也出版了她的《性的权利》。
这三本书超越了标准的同意模型,对我们在性方面的偏好和实践的起源发起追问。它们从“我们和谁发生性关系以及怎样发生性关系是一个政治问题”(这是斯里尼瓦桑的说法)出发,想象了一种不只要求同意的情欲文化。
重要的问题不只是女人是否同意,还在于她同意的语境是否有利于快乐和正义。事实证明,快乐和正义可能是相互依赖的,老一辈对性持正面看法的女性主义者,如卡洛尔·S.凡斯(Carole S. Vance)、艾伦·威利斯(Ellen Willis)深知这点。正如安吉尔敏锐地指出,在这样一种文化中,女性的快乐,往好处说是陌生的,往坏处说是被憎恶,“糟糕的性是一个政治问题”。因此,反对厌女既有了伦理上的理由,也有了情欲上的理由:在父权制下,女人不但被压迫还被压抑,而男人不但可怕,还不幸地,他们在床上也很糟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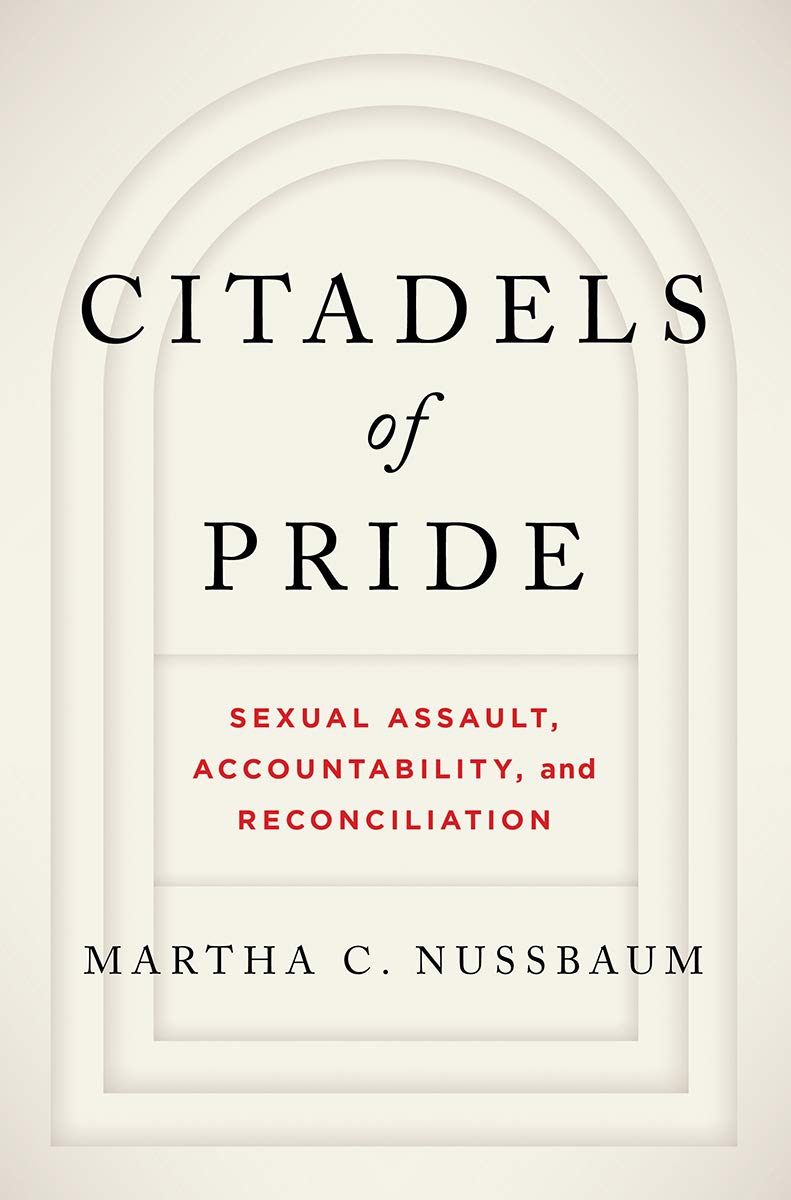
- 《骄傲的大本营》
乍看起来,纳斯鲍姆不像安吉尔或斯里尼瓦桑那样,对性侵害中性的维度感兴趣。在《骄傲的大本营》中,她坚称 #MeToo 提出的“根本问题”,“不是性,而是权力”,特别是有头有脸的男人行使的权力。相应地,她用更多篇幅来谈论强奸者和骚扰者的心理和社会化,而非性暴力的受害者。不过,她也感觉到(并且有时也指出了)这点——她对男性侵犯的分析,对女人来说也有重要意义。在父权制下,她们被迫把不能给她们带来快乐的东西,当作快乐来追求。
这本书由三个庞杂的部分构成,纳斯鲍姆在书中想做的事情很多,也许有些太多了。第一部分提出一个理论,论证了性骚扰和性侵在道德上令人反感之处;第二部分感觉像是出自于另一本书,它全面概述了美国关于不当性行为的法律(虽有信息量过大的问题);第三部分本身就是一部专著,它集中分析了书名中提到的“骄傲的大本营”——司法界、艺术界和大学体育界,它们都是性犯罪的温床,并且事实证明,这些地方尤其抗拒变革。
纳斯鲍姆是哲学家,不是历史学家或记者,她更擅长理论思考,而非经验或应用调查。她在第一部分提出最抽象的反思,既是这本书的重要寓意,又是它最有说服力的贡献。纳斯鲍姆的核心论证是,男人之所以行为不当,是因为他们物化了女人——而父权制社会在男人身上培养“骄傲的恶习”,反过来又构成了这种物化倾向的基础。
纳斯鲍姆在其他地方也大量(且出色地)论述过物化,但就她在这里的目的而言,物化现象涉及对女人的自主性和主体性的否定。所谓自主性,指的是她们“为自己做出某些定义人生的选择,而非任由他人决定自己的生活”的能力和权利。而主体性,则指她们作为“对她们来说,很重要的内心深处经验的中心”,而存在的能力和权利。
性侵和性骚扰否定了女人的自主性,因为它们“往往无视或践踏女人同意的能力,或通过威胁取得虚假同意,把女人当作方便使用的物,认为她们的决定对男性的满足来说毫不重要。”性骚扰者和性侵者也不尊重女人的主体性,他们认为受害者的“想法和感受无关紧要,就好像只有处于支配地位的男性的欲望才是真实和重要的”。
为什么男人如此倾向物化女人?纳斯鲍姆的回答虽然老套,却也有些道理:至少在我们的社会中,男人骄傲。和但丁一样,她认为骄傲使人的欲望变得畸形。与向外看到美好事物,从而追求它们相反,骄傲的人向内看,只对自己个人的扩张感兴趣。用但丁的话来说,骄傲者“像箍一样弯成一个圈,看不到外面的世界和他人”。
虽然人们常说人为身外之物感到“骄傲”,但对纳斯鲍姆来说,人为某物感到骄傲,一定是因为他觉得这个东西提高了自己的地位:“(你)爱你的房子,不是因为它漂亮或舒服,而是因为你认为它提高了你的社会地位”。这种骄傲永远是比较,绝不是内在。因为“重点在于……把自己抬高到他人之上”。
正常来说,在不断定自己的孩子比其他孩子更好的情况下,为自己的孩子感到“骄傲”完全可能,但按纳斯鲍姆的说法,骄傲总会蒙蔽人:它会引起物化,因为它涉及一种强烈到让我们看不到他人现实的“孤芳自赏”。美国式的男性气概,它执着于通过财富和性征服来确保“高人一等的地位”,就充满了这样的骄傲。结果就是,女人经常被看作“金钱和地位的象征”,而非一个完整的人。
至少在我们的社会中,男人骄傲。
批评者可能会抗议说,纳斯鲍姆的叙述把政治困境个体化了。但她并不认为骄傲是个人的问题。相反,骄傲是扭曲的制度(尤其是书名所说的“大本营”)在男人身上养成的毛病。从纳斯鲍姆的角度来看,“性暴力不只是孤立的‘病态’个体的问题”,毋宁说是“美国的等级结构”和“长久的传统”作用的结果。
纳斯鲍姆的诊断没有问题,虽然“骄傲”的说法不一定比常见的“特权”(“entitlement” and “privilege”)更有说服力。问题在于她提出的解决方案,其中的许多看起来太过于法律主义(legalist),以至于无法消除骄傲的祸根(她自己也承认是这个祸根是由文化造成的)。
如果男性的骄傲的确是普遍风俗作用的结果,那么,在缺乏更加全面改造的情况下,纳斯鲍姆推荐的制度干预能不能根除它就不好说了。比如说,纳斯鲍姆建议我们在性骚扰法规中引入更加清晰的语言,这种法律层面上的干预很难起到移风易俗的效果。
不过,我们能做的,可能也只是稍微撬动我们的制度,希望法律的变化能在规范上引发下游转变。适度而有针对性的改革(比如鼓励女人站出来指认大学校园里的性侵),哪怕没法从根本上改变法律之外塑造男性性格的结构,至少可以在短期内对骄傲的男人形成威慑。
这个相当“紧缩的”结论置作女性于何处呢?女性是男性骄傲的对象。事实证明,在女性那里,也有一种和男性骄傲相应的病态。虽然女性主义者有时不太强调这点。纳斯鲍姆最敏锐的洞见在于,父权制的压迫通过扭曲女人的性情和欲望,对她们造成巨大侮辱。
虽然“女性主义者倾向于相信受害者永远是纯洁正确的”,但事实上,纳斯鲍姆写道(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也观察到这点):“在不平等之下,女人的人格和志向也变糟了。”的确,正如纳斯鲍姆指出,要是我们能够毫发无损地躲过整个“教我们屈从,剥夺我们自主勇气”的社会,那才叫怪呢!要严肃对待父权制的危害,就要认识到这点——它不但危害,也腐化它的受害者。
父权制通过激起“报复性愤怒”——不同于鼓励人追求正义的愤怒,这种怨毒的愤怒会“摧残人格”——腐化女人。女性主义者原本对刑事司法系统残酷的惩罚方式持批判态度,但报复性愤怒使她们在谈论性侵时,抛开应有程序,通过推特审判,诉诸暴民而非法官。
甚至更加令人担忧的是,在父权制下生活的女人,还经常会发展出社会科学家乔恩·埃尔斯特(Jon Elster)所说的“适应性偏好”(adaptive preferences),或者说形成一种所谓“酸葡萄”心理。于是,女人开始“表演她们的支配者给她们提供的负面形象”,学着想要自己够得着的东西。在她们实际上什么也没法指望的情况下,她们不但学会以酸葡萄为生,还忘记自己曾经有能力渴望更丰富的食物。
父权制的压迫通过扭曲女人的性情和欲望,对她们造成巨大侮辱。
枯萎果实扎根的葡萄园,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斯里尼瓦桑《性的权利》的主题。在最初(2018年)发表于《伦敦书评》上那篇令人激动的同名论文中,斯里尼瓦桑坚称,人与人之间的性吸引(attraction)以政治为媒介。不然,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人在罗曼蒂克的领域表现出如此显著的“种族主义、体能歧视、跨性别恐惧,和其他一切压迫系统的痕迹”呢?不然,为什么所谓的“非自愿独身者”(incels, involuntary celibates)——那些到网络论坛哀叹自己在性上遭到疏远,痛斥拒绝和他们睡觉的女人的愤怒男人——会只喜欢在电影和广告中被吹捧为“美”,在色情片中被描绘为“顺从”的瘦小金发女人呢?
《性的权利》的论题既大胆又有说服力,斯里尼瓦桑也没有回避它凸显的棘手张力。一方面,一旦我们接受欲望是由社会、政治建构出来,那么,欲望就不再是除接受之外,我们别无选择的自然、不变的东西。现在,我们可以批判那些令人不快、排除性的,即反映和强化种族主义、体能歧视、性别主义等压迫系统的性偏好了。
另一方面,一旦我们趟入审查欲望这摊浑水,我们又会有助长“性权话语”的危险,而这种性权话语,又会起到鼓励非自愿独身者和潜在强奸犯的作用:如果欲望是可争论的,如果否认对另一个人在性方面的兴趣可能是错误的,那么,最终我们就可能在无意间验证那个想法——有时“不要”,真的应该是“要”的意思。
斯里尼瓦桑正确提出一个无定论的结论:“不存在性权,每个人都有权想要自己想要的东西,但个人的偏好……很少只涉及个人。”就像她在最后一段话中表述的那样,根本的问题“不在于有没有性权(实际上没有),而在于我们有没有义务,尽我们所能把自己的欲望变得好一些。”
那么,有这样的义务吗?我们中的很多人想知道答案,但斯里尼瓦桑没有告诉我们,她更喜欢“停留在那个矛盾的立场,一方面,承认没人有义务‘想要’别人,也没人有权被人‘想要’;另一方面,也承认谁被‘想要’、谁不被‘想要’,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人们经常通过更加普遍的支配和排除模式来回答这个问题。”
用一篇甚至是两三篇论文的篇幅来论述这点可能发人深省,斯里尼瓦桑对此立场的想象之巧妙,描述之漂亮尤其令人印象深刻。但随着论述拉长,原本令人兴奋的论证也开始变得让人受不了了。虽然这本由论文拓展而成的书增加了一个新的结尾,但新的材料没有尝试解决原论文指出的两难,只是在漫无目标地回应斯里尼瓦桑的批评者。它没有为不那么矛盾的结论铺垫。它还充满了因为没有得到回答,显得像是反问的问题——“不好看的人是一个被压迫的阶级吗?矮子呢?害羞成性的人呢?”
斯里尼瓦桑的论文讨论了像色情片的伦理和教师引诱学生在道德上有没有问题那样的主题,它们的形式大同小异,大体上都是从识别冲突的压力开始,以提出能不能协调我们相互冲突的评论的问题告终,这既令读者翘首以待,又让人大为恼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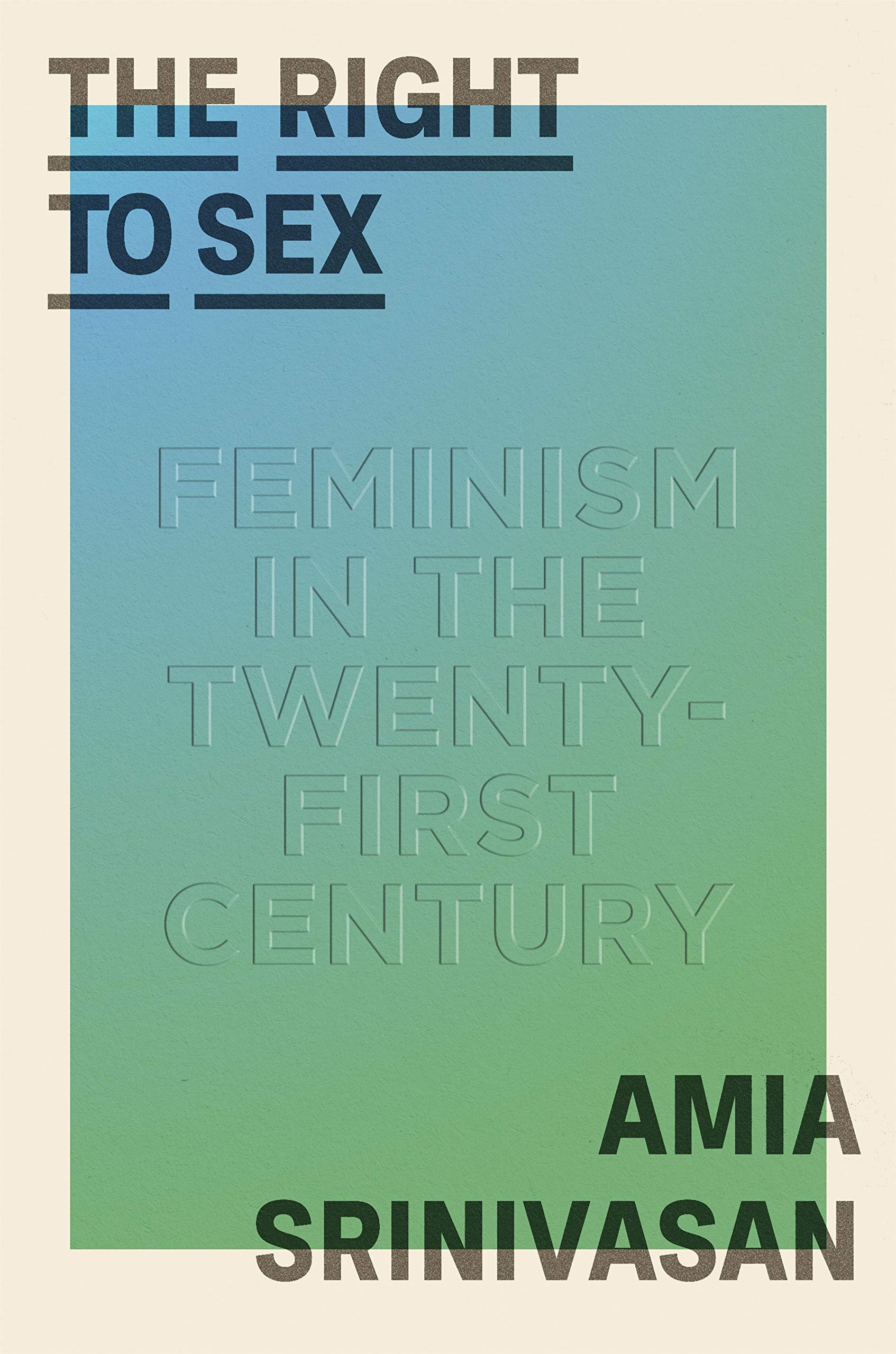
- 《性的权利》
也许,《性的权利》最正面、最明确的地方在于,它强调我们要注意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而支撑这点的想法是,有价值的女性主义不能以所有女人的“共性”为荣,这样的行动策略造成的后果是,女性主义将因此专注于为那些“最不受压迫的”女人服务,而不去保护最容易受到伤害的女人。
这个指导性的命令引出了对 #MeToo 各方面的重要批判。它也让人想起约翰·罗尔斯的差别原则,根据这个原则,不平等只有在有利于最弱势的社会成员时才是正当的。比如说,号召人们要相信女人,是在和那种不把女人的证言当回事的有害倾向做斗争,但它也会有用“说自己被强奸的白种女人”的话,来打“坚称自己儿子遭人陷害的黑种或黄种女人”的话的危险。当然,和解总是复杂的,但我们有不大胆提出临时决议的奢侈吗?
《性的权利》敏锐地勾勒出我们在性问题上面临的道德困境,但说到底,在我们实际上该怎样应对这些困境上,它并没有提供多少指导。文集中的最后一篇、也是最长的一篇论文,有力驳斥“监狱女性主义(carceral feminism)”,即“一种想通过强制性的国家权力——警察、刑事法庭和监狱——来实现性别公正的政治”。
和纳斯鲍姆一样,斯里尼瓦桑也对过度惩罚性暴力持怀疑态度,但和纳斯鲍姆不一样,她认为,#MeToo 之所以会有报复性色彩,是因为它过度依赖法律措施。《骄傲的大本营》认为,“#MeToo 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而非法律这个事实造成一个问题”——“在惩罚不是由中立的法律机构进行,而是通过羞辱和污名化来完成的情况下,怎样保障正义和保护平等的尊严呢?”斯里尼瓦桑则相信。“总的来说,#MeToo 的女性主义者看起来很相信强制性的国家权力。”
孰是孰非?监狱的解决方案和法律之外的解决方案都有其危险之处。纳斯鲍姆觉得“法律和‘法治’体现了一种平等尊严和公平的正当程序愿景”,考虑到实际存在的刑事司法系统中掺杂的种族主义和阶级主义,这种感觉太过于乐观。但纳斯鲍姆花很大功夫归纳的那段历史——人们怎样征用法律来保护女人——也强调这点:有时,向国家求助是有益的,虽然因此获得的好处是脆弱的。
我们有理由认为,法律对 “性骚扰”范畴(由活动人士在 1970 年代引入)的承认开启了一场范式转移:就像一位著名女性主义者回忆的那样,在这个术语出现之前,职场虐待“只是生活而已”。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有时,法律框架的缺乏也可能给斯里尼瓦桑告诫我们要重视被边缘化的社群带来危险。校园法庭就是一个例子,它不一定会给被告提供免费律师。
鉴于所有这些复杂情况,斯里尼瓦桑明智地坚持,“把惩罚坏男人视为主要目的的女性主义政治,永远不会是解放所有女人的女性主义,因为了它遮蔽了使大多数女人不自由的东西”,这些东西就是经济不义和随之而来的物质剥夺。
但这个说法并没有把这点说清楚:我们生活在令人遗憾的严重不平等之下。有鉴于此,在不远的未来,具体来说,除监狱女性主义外,我们还应该追求什么?难道女性主义者应该在争取更加全面正义的时候,放弃加强对性侵或性骚扰受害者保护的努力?难道我们应该拒绝指控强奸我们的男人?
这些药苦口,但我很可能还是可以说服自己把它们吞下去,甚至还会觉得它们比酸葡萄更好。问题在于,斯里尼瓦桑没有解释我应该选哪盘菜,以及,为什么我有义务,或者说,我到底有没有义务克制我更加放肆的渴望?渴望性支配或力图与父权制的美丽规范保持一致的女人,应该纠正或无视自己的欲望吗?我们几乎可以肯定,这些欲望是从沙文主义者那里继承下来的。她们是不是应该放弃满足起源不义的色欲,而去选择长久的不满?在我们永远没法驯服我们难以控制的胃口的情况下,我们该怎么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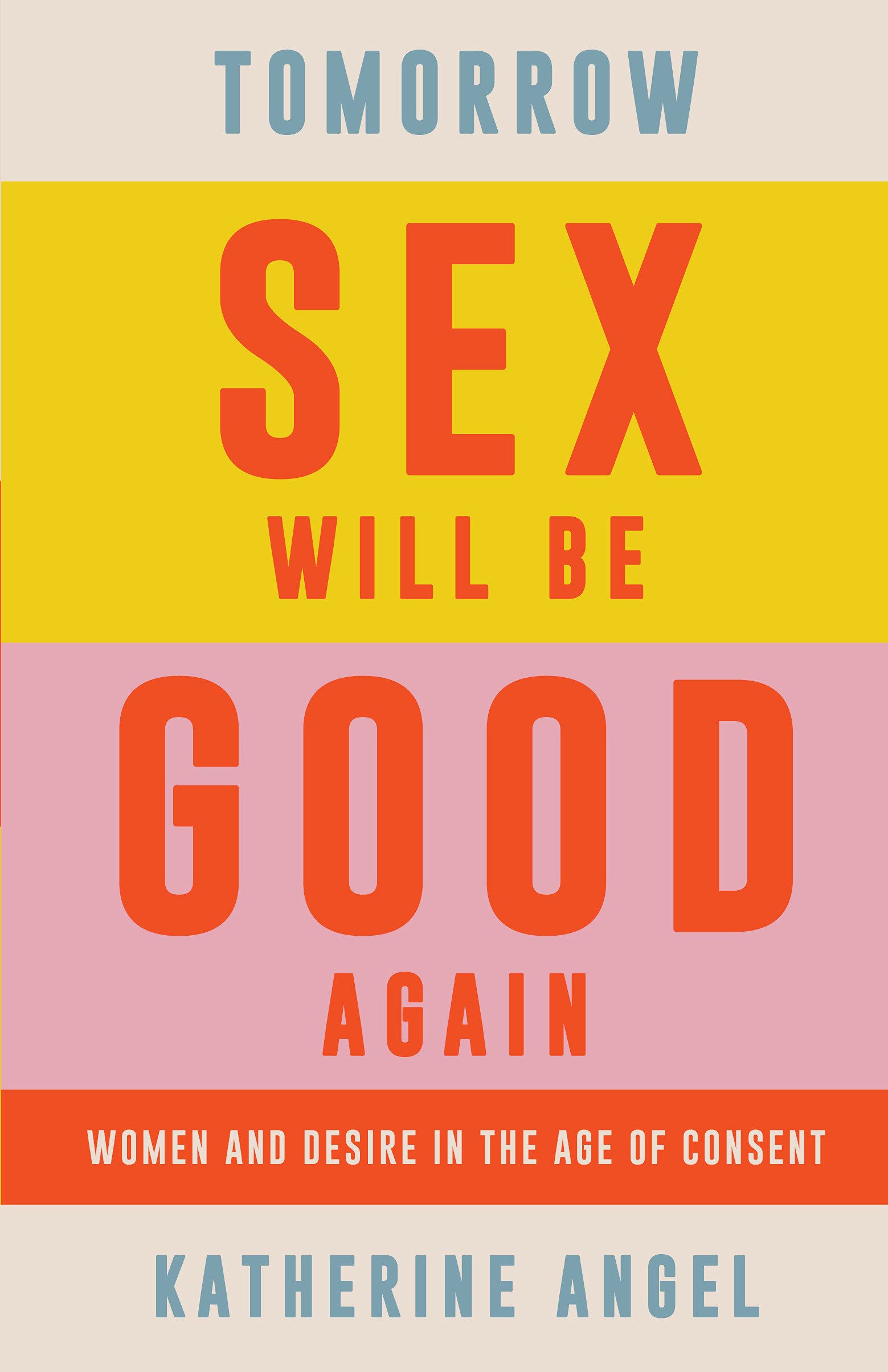
- 《明天性又会好的》
也许我们不需要驯服它们。最终拯救我们的,正是我们不受控制的胃口——安吉尔在她透彻而优雅的专著《明天性又会好的》(也是迄今为止这方面最令人振奋、最具原创性的一本书)中这样论证道。在四篇深挖细究的论文(它们依次讨论了同意、欲望、唤起和脆弱)中,安吉尔没有拒绝法律和物质的补救措施,而是超越它们,到我们情欲关系的间隙那里,到欲望本身纯粹的力量和事实那里去寻找帮助。
她从“同意和自知”开始探究。一般认为,同意和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是好的性需要满足的“两大要求”。“在性的领域,同意(至少是同意的理想)最重要”,她写道,在这里,“女人必须说话——她们必须说出自己想要什么。因此,她们也就必须知道她们想要的是什么。”
但女人应该怎样弄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呢?在一个笛卡尔主义重新抬头的年代,我们太过于仓促地忘记了,所有人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说都看不穿自己,尤其是女人,她们一直在被各种关于我们要不要相信自己的本能或放纵自己的倾向的矛盾信息轰炸。PUA 高手一直在告诉我们,在我们说“不要”的时候,我们的意思是“要”,并且我们更广泛地“因为我们被要求培养的自信、坚定的姿态和行为而遭到惩罚和批评(说我们刻薄、专横、凶)”。希望破除“女人没有男人好色”神话的好心的科学家,甚至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他们论证说,女人甚至在表示没有欲望的时候,也会展示出唤起的生理表征。
是我们渴望的身体掩饰了我们含蓄的心灵呢,还是相反?我们的抵抗在多大程度上来自压迫性规范(根据这样的规范,女性以纯洁为特征)的内化?我们的渴望在多大程度上来自于厌女的命令(根据这样的命令,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满足男人)?我们可以从性别歧视教导的泥水中提取出纯粹的欲望吗?除此之外,如果真有这样的东西存在,稀释了的欲望就不如纯粹的欲望正当、有力吗?我们就不能给自己我们想要的东西吗,哪怕我们只是因为被虐待了才想要那个东西?
如果说这些问题在理论上没有答案,那么,在实践中,私密的直接性又让它们甚至更难回答。评论者从他们遥远的扶手椅中建议要爬出那个“矛盾的地方”,但床上的女人只能躺在那里。最终,同意的拜物化把“好的性的互动负担”放到女人身上,而后者已经被巨大认知负担压得步履蹒跚。
“为确保性对双方来说都是快乐和非强制性”的女人,“必须表现出自信的性自我”,但一切又都在合谋阻止女人培养出那样的自我。安吉尔的结论是,“如果我们想要好的性(令人激动、欢乐、非强制),那么,我们需要不被要求像我们总是知道的那样行为和说话。”
当然,这不是说,我们要搞不经过同意的性行为。同意是“基本的”,是“最低要求”(虽然我们不太清楚在安吉尔看来,在不可能存在同意,看起来要求的那种确定性情况下,我们应该怎样确保这个条件得到满足)。要好的性意味着,经过同意的性还不够好,因为“很多经过同意,甚至明确得到同意的性并不好:它难受、不愉快、羞辱人,单方面和痛苦。”
当前盛行的在快乐上的性别差异“很重要,哪怕它严格来说算不上侵犯。” 使如此之多的性如此之糟糕的原因,除人与人之间化学反应失败(这方面因人而异)外,还有“性别规范,在这样的规范中,女人不可能是和男人平等追求性的能动主体,而男人则有不惜一切代价得到满足的特权”。
换言之,同意范式把一个事实上要求政治回应的问题,要求一场改变我们为女人提供的,用来探索她们饥渴资源的革命,给私人化了。
“想要”经常伤害我们,却也会给我们翅膀。
甚至革命也不能挽救当前模型,这个模型假设,先有静态、稳定的偏好,然后,人们借助同意表达这些偏好。在关于欲望的章节中,安吉尔解释说,一些性学家区分据说是男人特有“预期性的(anticipatory)”欲望,和据说女人特有“回应性的(responsive)”欲望。前者自由流动、自成一类,后者由特定的人激起,并附着于促成它的那个人。
根据流行想法(在这么长时间里,这种想法一直占主流),男人有会让他们扑向碰巧在他们身边任何一具身体的生物欲望,而女人则会被特定刺激吸引。那些认为这样的两分是性别歧视的人会说,女性的欲望和男性的欲望一样极具生物性:所有的欲望都是预期性的。
安吉尔创造性地提出相反论证,她认为,是男性的欲望像女性的欲望:所有的欲望都是回应性的。我们不应该“把男性的欲望当作基本的生物学事实”,而应该把它看作“社会赋能、许可和强加的行为”。
说到底,平等也有一个度;男人事先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女人也一样,因为欲望不会先于引起欲望的语境。在发现自己处在想要一个东西的火热、粘稠阵痛中之前,没人真的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快乐包含风险,而且这个风险永远没法被排除或避免……当我邀请某人进入——当我想让他们进入——的时候,我永远没法确定他们会以我想要的方式进入。我也永远不可能事先知道我想让他们以怎样的方式进入。”不可预知性不只是性生活不可避免的一个事实,也是情欲的本质。就像安吉尔在她关于脆弱的极其欣悦的章节中写道的那样:
“确切来说,性的一部分乐趣就在于发现新的、不同的被触摸的方式:就在于对未知的东西脆弱……这就是为什么性的邀请吓人,为什么它如此动人。在一个人的欲望中被满足,在一个人的欲望中被惊讶,是在练习相互信任和克服恐惧。在成功时,那感觉就像是奇迹。”
好的性、可口的性就像有糖霜的蛋糕,在于发现自我以一种心怀欲望的个体,永远没法以独自想象或预期的方式被夺走、被改造。
这意味着,我们受制于不是我们选择,并可能反映和复制我们不认可的文化病态的欲望。这也意味着,欲望可以把我们从习惯性的狭隘中拉出来,打破意识形态硬壳,开启某种温柔超越。
在《菲德罗篇》中,柏拉图生动描述一个与美丽少年相遇,被欲望的混乱击垮的男人。这个男人的“整个灵魂都在悸动”,他脸红、流汗、头晕目眩,开始忽视他原本追求的东西,对家人和朋友也不那么感兴趣。他以不同的方式安排自己的时间,力图按少年的光辉形象重写自己的人生。最终,他变成一种新的造物,开始长出翅膀。
在《性的权利》少数充满希望的段落之一中,斯里尼瓦桑一定也有类似想法,她写道:
“欲望会让我们惊讶,把我们引向某个我们不曾想象过自己会去的地方,或把我们引向某个我们从来没想过自己会渴求、会爱的人。在最好的情况下——也许,这些情况也给了我们最好的希望——欲望会反对政治为我们选择的东西,并为自己做出选择。”
欲望经常不顾我们的抗议,通过我们来起作用,出于这个原因,它可以比我们更好。当然,它也可能更糟。无论内容是什么,至少在一个方面,就其结构而言,抓住我们的欲望是合乎道德的。指责的渴望,是骄傲的人怀抱渴望的反题,它起源于外部而非内部。
纳斯鲍姆的物化者把粗鲁的幻想强加于他们的对象,但被意料之外的欲求砸开的人,会被促成这欲求的人迷得神魂颠倒。好的性,就其坚持其对象的独一无二而言,会提升我们。欲望总会带来大规模重新创造的风险,因为在欲望行动本身中就隐藏着革命的潜能。只要我们还能“想要”,我们就还没输:“想要”经常伤害我们,却也会给我们翅膀。
这是一篇书评,评的是玛莎·纳斯鲍姆(Martha C. Nussbaum):《骄傲的大本营:性侵害、问责与和解》(Citadels of Pride: Sexual Abuse, Accountability, and Reconciliation), W.W.Norton, $27.95(cloth)。
阿米娅·斯里尼瓦桑(Amia Srinivasan):《性的权利:二十一世纪的女性主义》(The Right to Sex: Feminism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8(cloth)。
凯瑟琳·安吉尔(Katherine Angel):《明天性又会好的:同意时代的女人和欲望》(Tomorrow Sex Will Be Good Again), Verso, $19.95(cloth)。
译者:王立秋
云南弥勒人,北京大学比较政治学博士,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
原文来自 Becca Rothfeld, “Pleasure and Justice”, Boston Review, September 20, 2021。经作者许可翻译。
题图来自 Benjamin Disinger @ flick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