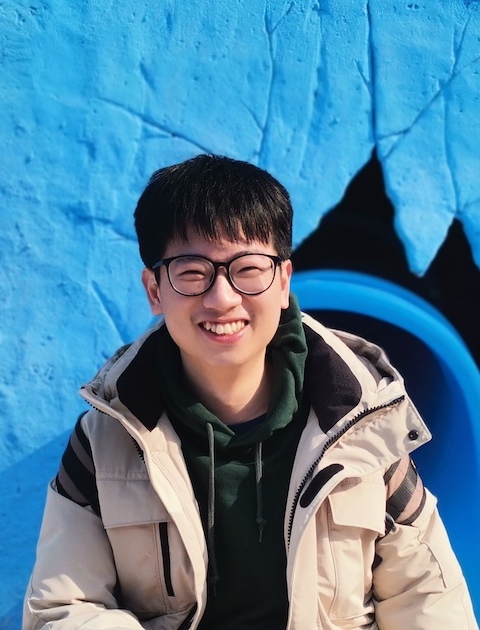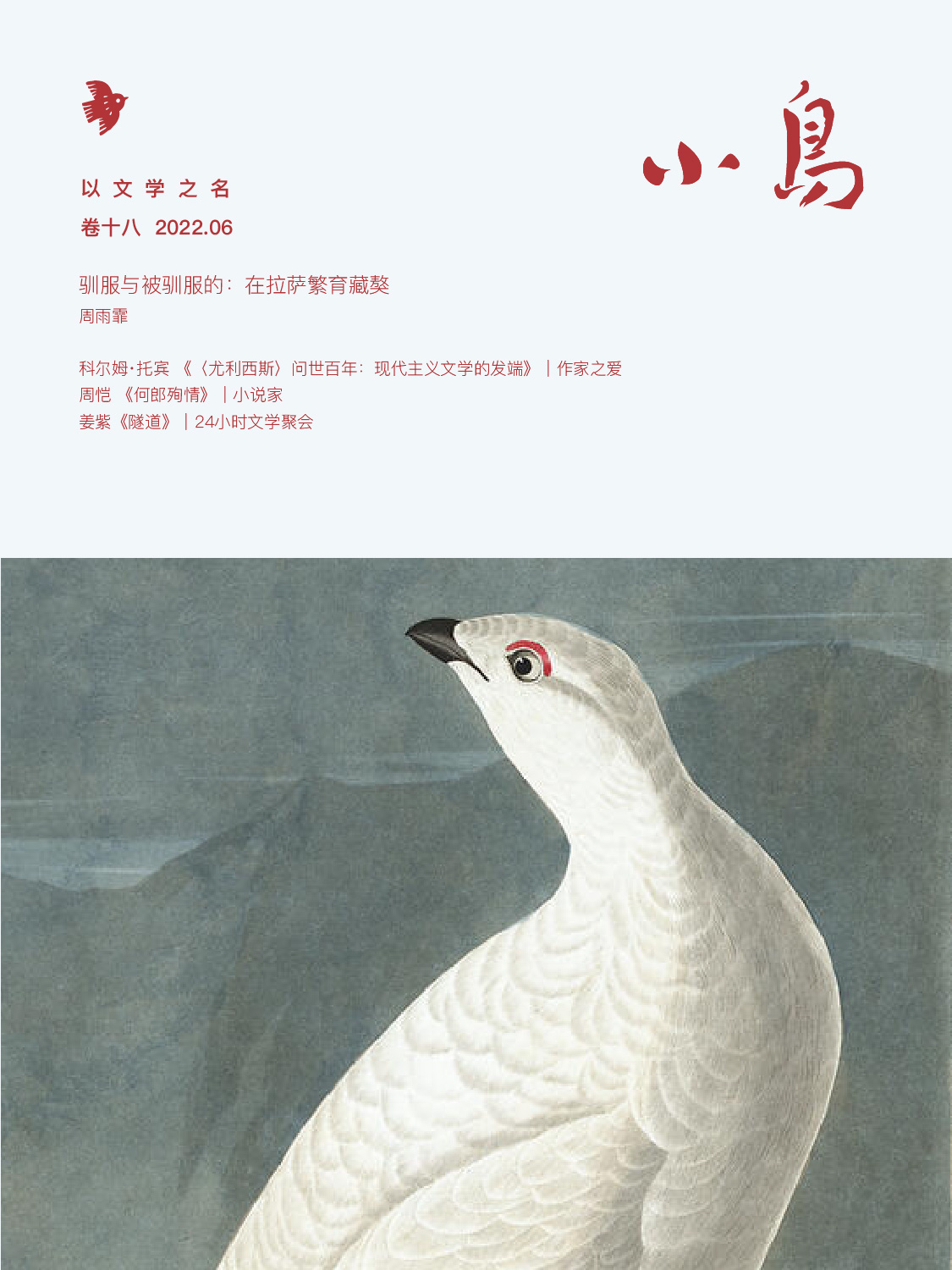在过去的讲座和课堂上,陈映芳曾多次把胶州路事件当作案例,向学生讲解“何为城市文明”。
胶州路事件指 2010 年 11 月 15 日下午,上海胶州路 728 弄 1 号一幢 28 层的公寓大楼(教师公寓)发生火灾,造成 58 人丧生、71 人受伤。火灾发生后,上海市民自发、持续地展开追悼活动,并在“头七”那天,10 多万人来到受灾大楼现场,井然有序地向罹难者鞠躬、献花,被外界赋予“上海觉醒”、“公民社会”等意义。
陈映芳觉得,“上海觉醒”、“公民社会”这类说法,有过度解读和拔高之嫌。火灾之后,除了受灾群体自身的维权行动,公众没有展开以立法或体制变革为宗旨的公开大规模联合行动,政府也只是象征性地将 11 月 15 日设立为上海的“城市公共安全日”,没有对城市防灾体制和市民防灾系统做出重要改变。
不过,事件仍然有着积极意义。“芒福德反复地强调,城市就是一座剧场,正是在城市中,人们表演各种活动并获得关注,而社会戏剧的出现需要借助于各种集体活动的汇集和强化。从这个意义上讲,胶州路上参与集体祭奠的市民,是通过扮演‘文明的市民’的角色行为,表达了对现代城市文明和社会公正价值的集体认同,并成功地向全社会展现了其对理想价值规范的实践能力。”陈映芳在新著《秩序与混沌:转型中国的“社会奇迹”》中写道。
她认为,“作为对中国国情特殊性的一种反证,长期以来,‘上海’的都市性一直被赋予了中国现代性的意义,成为‘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可能性’的想象依据。这样的想象在某些特殊的时空中,会一次次被论证和强化。事实上,自 2020 年初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上海因为在承担繁重的国际航运任务的同时,以较为开放的防疫模式恢复、维持了经济生活秩序,并多次较为快速有效地控制了本土病例的扩散,由此再一次被网民们誉为中国现代化的榜样。”
在“文革”时期度过童年、少年时代的陈映芳如今是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她 1977 年考入江苏师范学院(1982 年改名为苏州大学),本科和硕士均在历史系就读。到了 1980 年代末、1990 年代初,“焦躁不安”的她有机会赴日本京都大学访学,却难以维持自己的历史专业兴趣,转而到大阪市立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
博士毕业回国的 20 多年来,她将上海作为中国研究的田野,在青年、城市、家庭等领域均有贡献,是国内少数将社会学理论与实证结合出色的社会学者,著有《“青年”与中国的社会变迁》《城市中国的逻辑》等,编有《移民上海》《寻找住处》《都市大开发》等。
最近十几年,陈映芳致力于转型社会研究,去年在台湾出版《秩序与混沌:转型中国的“社会奇迹”》一书,是近年难得关于中国社会现实的学术专著。在书中,她试图解释一个被称为“中国稳定之谜”的现象:
“在 20 世纪 70 年代特别是 90 年代以来的社会经济/社会体制变动中,中国发生了诸如价值规范大转折,数百万职工下岗,数亿农民流动,土地/城市大开发,社会急剧分化……这样的一系列社会剧变,可是,总体而言,社会群体之间并没有发生激烈的冲突,城市也没有出现大规模的骚乱,人们的生活秩序看似也没有崩溃……所有这些,究竟是如何可能的?”

- 上海市民哀悼胶州路事件的罹难者。图片来自 Wikimedia
2022 年春天,上海因疫情封控两个月,涌现各种乱象,让人百感交集。一些人哀呼上海何以至此,另一些人转而批评上海。随后多地疫情的爆发和处置,又让不少批评上海的人意识到,病根绝不是单一城市的问题。那么,如何理解此次疫情中的上海,以及在更大图景下思考中国社会的转型?于是,我在 5 月联系了陈映芳教授,希望她能谈谈疫情期间她在上海的生活、感受和观察,也就《秩序与混沌》中的一些问题加以讨论。
陈映芳说:“城市治理中的国家-社会关系演变,以及城市生活秩序的脆弱性,原是我这两年重点关注的几个问题,去年我们团队成员就一直在浦东一些社区做调研。但无论如何也没有预想到,突如其来的灾难性事件是以目前这种方式降临到这座城市,说实话也没料到我们自己会统统被卷入到这样的生活危机状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