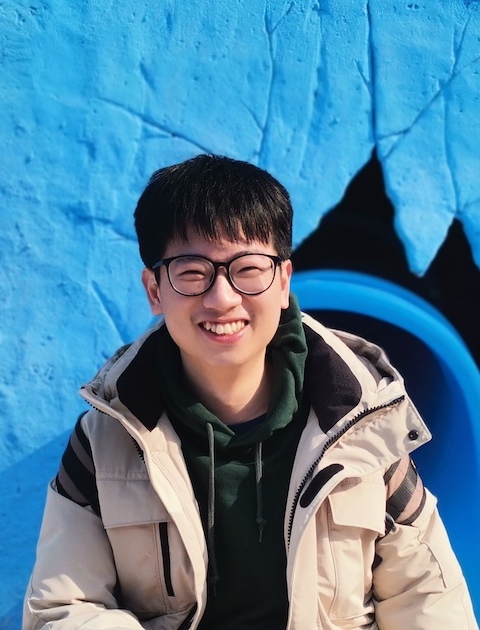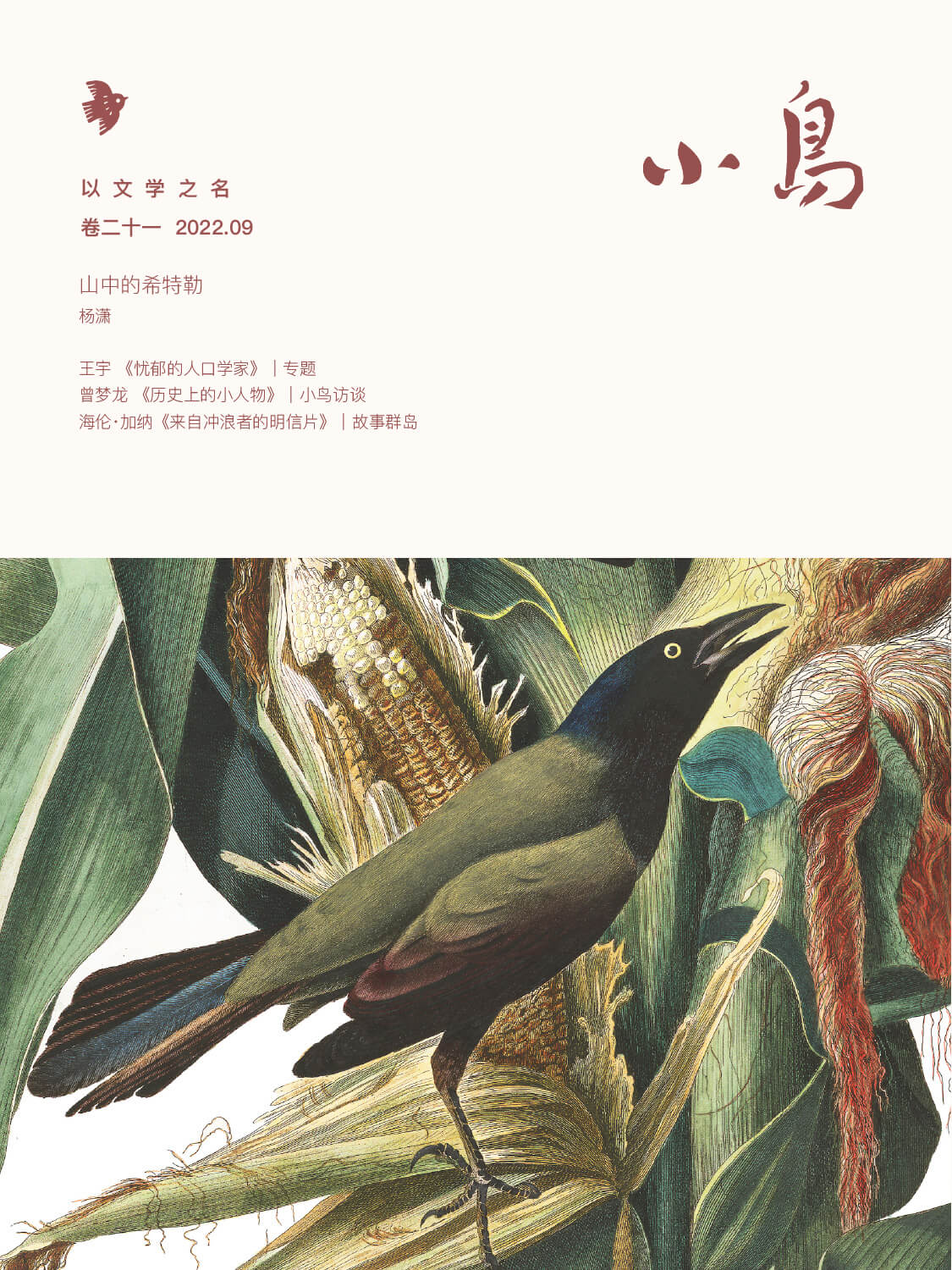作家萨曼·鲁西迪遇刺后,在西方世界掀起一场关于“言论自由”的辩论,和近些年“取消文化”的背景相呼应。比如英国作家凯南·马利克(Kenan Malik)称,某种程度上,许多社会已经内化追杀令,并在我们谈论彼此的方式中引入某种自我审查;美国作家大卫·里夫(David Rieff)认为,如果《撒旦诗篇》是在今天提交出版,将会与“敏感读者”发生冲突。作者会被告知——就像教令所说的那样——语言即暴力。
大卫·里夫等人实际上是在批评欧美当前的“取消文化”风潮,希望借此让人们看到语言和暴力的界限。正如《纽约时报》所概括:“随着年轻进步人士越来越多地批评言论自由原则经常为仇恨言论提供掩护,攻击性言论属于‘暴力’的概念越来越流行。‘言论自由’成为保守派的战斗口号,他们把它作为反对自由派的武器,指责自由派想要审查异议。”这在 2015 年美国笔会决定向法国杂志《查理周刊》颁发勇气奖、2020 年鲁西迪参与联署的《关于正义与公开辩论的公开信》等事件中都可看到其争议。
不过,将原教旨主义或神权主义者的暗杀与当代西方左翼言论联系起来的看法也遭到一些批评。批评者同意必须要尊重言论和暴力之间的明确界限,因为冒犯你而试图杀死某人是可怕的,但认为这不能等同用来批评“取消文化”。“言论自由”不是独白,恰恰是有人反对的自由,而任何言论都会遭遇社会制裁的风险。
和反对《哈泼斯》那封公开信人士的角度类似,作家奥尔罕·帕慕克关注的是刺杀背后暴露出的社会问题。他在文章《仇恨从何而来?》(Where the Hatred Comes From)中,讲述自己因为对亚美尼亚种族灭绝的评论遭遇威胁,十多年来被保护性监视,感到窒息和厌烦的经历和感受。所以,他经常想起那些制造威胁的人,觉得我们要关注基于阶级的文化差异和民族主义怨恨等。
帕慕克称,如果我们希望看到言论自由的原则在社会中蓬勃发展,只有像鲁西迪这样的作家的勇气是不够的,还必须勇敢地思考他们遭受强烈仇恨的根源。事实上,刺杀鲁西迪的嫌疑人哈迪·马塔尔只读过几页《撒旦诗篇》,在一家折扣店当店员。这在某种程度上佐证了帕慕克的敏锐,也符合米兰·昆德拉曾在文章中讽刺人们纵情谈论《撒旦诗篇》攻击伊斯兰教,但几乎没多少人读过这本书的窘境。
“他们在支持拉什迪的请愿书上签名,同时却风度优雅地、带着花花公子般的微笑说:‘他的书?噢,不!噢,不!我没读过。’……没有人还在怀疑鲁西迪攻击了伊斯兰教,因为满世界只有指控是真实的,而小说的文本再也没有任何意义,它不再存在了。”昆德拉写道。
还有什么值得想想……
01
8 月 30 日,前苏联最后一任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逝世,享年 91 岁。4 天后,他的葬礼在莫斯科举行,但俄罗斯没有宣布全国哀悼日,也没有为其举行国葬,只是遗体告别仪式有国葬的部分元素。普京缺席了葬礼,由于俄罗斯回应西方制裁实施入境禁令,所以也没有西方领导人出席。某种程度上,这场葬礼的“低调”暗示了戈尔巴乔夫的复杂与争议,以及一些人对他的选择性遗忘。
在俄罗斯,戈尔巴乔夫不太受许多人待见。虽然普京在声明中称,“戈尔巴乔夫是一位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政治家和国家领导人。他深深懂得改革的必要性,力求为紧迫问题提供自己的解决方案”。但事实上,普京是戈尔巴乔夫的严厉批评者,曾将苏联解体称为“该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
许多怀念“帝国”的俄罗斯人也对戈尔巴乔夫持批判态度,认为他是共产主义事业的“叛徒”,要为苏联解体及随后的经济危机等问题负责。另一边,像《新报》总编穆拉托夫等人会向其致敬,认为戈尔巴乔夫“鄙视战争”,更喜欢“和平”,而非“个人权力”。
在西方,戈尔巴乔夫广受赞誉,认为其和平终结冷战。比如美国总统拜登赞扬他具有非凡远见,接受民主改革,使世界更加安全,也让数以百万计的人享有更大自由;法国总统马克龙形容他是和平主义者,为俄罗斯人民开辟自由之路,对欧洲和平的承诺改变了我们的共同历史;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赞扬他是坚定的多边主义者和不懈的和平倡导者。
美国学者威廉·陶伯曼(William Taubman)曾花 11 年写作传记《戈尔巴乔夫和他的时代》(Gorbachev: His Life and Times),认为戈尔巴乔夫改变了自己的国家和整个世界,但这些改变都没有如他希望的那样大。回想起来,他的最终失败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但正如已故俄罗斯学者德米特里·弗曼(Dmitry Furman)所说,他有资格被誉为“俄国史上唯一掌握绝对权力却坚守道德情操,自愿限制权力甚至冒险失去权力的政治家”。
“当戈尔巴乔夫 1985 年上任时,他拥有几乎不受限制的权力。他本可以无限期地维持现状。然而,他彻底摧毁了苏联体制,把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和思想自由带给了不识这些权利为何物的人们,他还引入了自由选举和真正的议会制度。是他而非别人结束了冷战,降低了人类因核战争而毁灭的风险。他默许了苏联帝国的解体,在解体时没有出现其它帝国崩溃时常有的暴力。他梦想建立一个禁绝武力的新世界秩序,在这个新世界秩序中,东西方不再有分歧。” 陶伯曼写道。
在苏联的前加盟国和卫星国,乃至更远的非洲等地,戈尔巴乔夫的面貌更加多元复杂,其评价和当地的历史与影响紧密相关。比如在德国,因为戈尔巴乔夫促成两德统一,所以很受人们欢迎,像德国导演沃纳·赫尔佐格近年还制作过纪录片《会见戈尔巴乔夫》。

- 《会见戈尔巴乔夫》(2018)剧照
但在高加索地区,如阿塞拜疆,戈尔巴乔夫 1990 年曾派兵镇压其独立运动,造成 100 多人死亡,所以该地区的民众至今认为戈尔巴乔夫是个屠夫。类似的,在波罗的海地区,如立陶宛、拉脱维亚,戈尔巴乔夫血腥镇压过它们的独立运动,造成人员伤亡,所以被长期谴责。
乌克兰的情况更复杂一些。一方面,切尔诺贝利事故给乌克兰造成至今无法弥补的创伤,人们认为戈尔巴乔夫需对其负责;另一方面,他也的确为乌克兰的独立开辟道路,受到民众赞扬。
至于非洲,由于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使得安哥拉、南非等地迎来和平转型,人们对他的评价也就比较高。
回顾戈尔巴乔夫的政治遗产,内政和外交是两个核心。内政,主要是备受争议的改革部分。历史学者沈志华认为,在苏联解体的问题上,过多追究个人责任的做法并不可取。恩格斯在总结 1848 年革命失败的教训时,也特别批驳了“领袖出卖”论。勃列日涅夫时期堵塞了经济转型、政治转型和社会转型的所有通道,苏联已经走进死胡同。就像一个人已病入膏肓,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只是想对病人进行手术,结果发现是癌症晚期,病人死在了手术台上。
陶伯曼则将改革失败的原因追溯得更长:“改革的障碍源于俄罗斯的历史:沙皇专制主义演变成苏联体制,民众盲目服从权威却又不时以血腥的暴力运动反抗权威,仇视妥协(‘妥协’这个词在俄语中有负面含义),没有自我组织的民主传统,缺乏运行自由市场的经验,没有真正的法治。”
在回忆录《苏联的命运》中,戈尔巴乔夫说,自己坚信改革是历史的必然。“尽管有错误和过失,我们却把国家带出了历史的死胡同。我们给了它自由的初步经验,解放了人们,使他们有可能凭自己的智慧生活。我们给‘冷战’、核武器竞赛画上了句号。”
关于外交,一大争议问题是戈尔巴乔夫在促成两德统一,保留其在北约内的成员国地位时,条件是结束冷战后的解决方案将会考虑苏联的安全利益。那时,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向他口头承诺,北约“向东不进一英寸”,但他没有将口头承诺正式写入文件签署,使得多年后北约东扩,双方出现巨大争论。
他的另外两大遗产,与西方对话和推进核裁军,逐渐烟消云散。目前,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跌至冷战结束以来的谷底,核威胁的阴云笼罩在世界上空。戈尔巴乔夫的母亲和岳父都是乌克兰人,但他逝世前没有公开评论俄乌战争。不过,曾为他当翻译 37 年的帕拉日琴科(Pavel Palazhchenko)数周前与其通过电话。
帕拉日琴科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令戈尔巴乔夫“震惊和困惑”。“不只是 2 月 24 日开始的军事行动,而是过去几年来,俄罗斯和乌克兰关系的整个演变,对他是很大打击,真的是在情感和心理上彻底摧毁了他。”
02
据财新统计,最近疫情波及 23 个省市自治区的近百座城市,其中有 33 座城市处于部分或者全部“静态管理”,超过 6500 万居民受到影响。一些防疫政策也受到争议,比如四川泸定地震发生时,一些居民被阻止逃离住所和小区,消防通道也被封锁;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在“静态管理”中出现很多问题,包括就医难、采购物资难、防控措施不够精准等,当地政府在发布会上向市民道歉;
国务院批评多地过度防疫、层层加码,包括河南的商丘、三门峡、开封,河北的邯郸市邱县,江苏的苏州,浙江的台州、湖州市德清县,宁夏的吴忠市盐池县。此前,河北、辽宁、青海等地也被国务院批评过度防疫、违反防疫“九不准”;烘焙品牌“巴黎贝甜”在上海封控期间让无法返回住处的工人前往培训中心过渡住宿,烤制面包自食自用,后向周边急缺食物的居民平价出售,但被上海市场监督管理局认为违反食品安全法,罚款 58.5 万,引发争议。
03
9 月 7 日,电影《隐入尘烟》票房过亿,出乎许多人的意料,此前该片的票房预测只有 200 万。电影以诗化语言呈现乡村现实,讲述在西北农村,两个被各自家庭抛弃的孤独个体,在日复一日的耕耘中相濡以沫的故事。导演、编剧李睿珺称:“中国有六亿人月收入一千、有五亿农民,但在八万块银幕上很少有机会看到他们的形象和生活,有责任让更多人看到他们。”
面对《隐入尘烟》美化苦难等争议,李睿珺解释道,自己作为高中学了三年美术的美术生,可能没有办法放弃对构图影调的处理方式,但乡村和里面的人是真实存在的。劳动既有残酷,也有美。
他还说:“每次都会有很多观众说,我拍的是边缘人群。我说,怎么能是边缘人群?中国现在老龄化程度那么高,是谁在把谁边缘化?我拍《老驴头》《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其实都是在讲述西北乡村留守老人的故事,这也是《隐入尘烟》里出现的问题。在乡村,没有退休金,还没有家人和子女,它是精神和物质上好几重的困境。我们在今天去改善现在老人的困境,那就是在改善我们自己的未来。”
景军是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长期关注中国的养老问题。在《我们该如何面对“老去”》一文,他也指出现在中国养老形势面临的挑战,比如 70% 大中城市的老年人家庭属于空巢家庭,农村留守老人有 1600 万,另外全国还有 4000 多万失能老人,研究了当前四种积极应对的模式,包括幸福守门人、时间银行、老人会、病友会。
在“老去”的问题之后,紧接是“离去”的问题。景军介绍了安宁疗护的历史、现状和国内几种模式,称安宁疗护也称为临终关怀、末端期关怀或者姑息治疗。它不同于“安乐死”,是致力于在减少患者身体病痛的同时,平静他们的内心,最终帮助患者从容、有尊严地离去。据国家卫健委 2018 年的数据,中国只有 28.3 万人接受安宁疗护,尚在起步阶段。
04
9 月 8 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逝世,“君主制”成为争论焦点。在一些英联邦国家,“脱离君主制”、“成立共和制”的讨论兴起。去年 11 月,东加勒比海岛国巴巴多斯就正式脱离英联邦成为共和国。最近,一些活动人士借机再次呼吁取消英国君主在这些国家的国家元首地位,并要求英国为历史上的奴隶贸易支付赔偿。
英国白金汉大学教授格雷斯(Anthony Glees)认为,21 世纪的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接受和赞成君主制,主要取决于君主如何扮演自己的角色,而伊丽莎白二世对此驾轻就熟。她履行其义务,严肃认真地为国家效力,特别是严格避免对政治的任何干预。因此,女王逝世后的情况将很难说。而且,英国正陷入严重的社会和经济危机,新任首相特拉斯才刚上台,情况加剧。
05
8 月底,一篇署名“中国历史研究院课题组”的论文《明清时期“闭关锁国”问题新探》引发争论。该文称,“闭关锁国”不是对明清时期对外政策的客观描述,面对咄咄逼人的西方殖民势力,明清时期的中国当政者从军事、经济、文化等不同层面,采取了以“自主限关”为主要特征的限制性政策。这一政策没有阻断明清时期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和中西文化交流互鉴,但造成了消极防御和漠视西方先进科技的负面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为近代中国陷入被动挨打局面埋下了伏笔。
一些批评者认为,该文是在为“闭关锁国”翻案,也是中国政策发展动向的反映,还引用或转发历史学者戴逸 1979 年刊发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闭关政策的历史教训》批驳。也有人觉得,上述批评有点过度,中国目前强调的还是开放。但是,人们说明清两朝“闭关锁国”,是在表达明清限制对外交流的荒唐程度,不能把它机械理解成完全关闭国门,断绝同国外的一切贸易和来往。需要反思的是,明清统治者既自大又封闭的心态通过实施政策传染给民众,导致整个社会和民众心态和精神的闭关锁国。
支持该论文的,代表如梅新育(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称,“经过 40 多年发展,明清闭关锁国论在国内外学界中都遭到越来越广泛的质疑,明代及清代前期、中期白银通过贸易顺差渠道持续大量流入中国已成为学界常识,在社会大众中也日益广为人知,表明中国的历史研究进步很大。我从小被灌输明清闭关锁国论,到武大读世界经济系研究生之后,读到国内外那么多明清对外贸易、白银内流的专著、论文,才发现不是这么回事。……如果现在还有人几乎没有读相关文章,也不了解相关学术研究进步,就随着别人的片言只语人云亦云掀起舆情浪潮,要把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强拖倒退回几十年前甚至一百多年前,那不仅可笑,更是可悲。”
06
9 月 29 日是中日建交五十周年,学术杂志《二十一世纪》推出“中日关系︰回顾与前瞻”专题,邀请四位中日问题专家撰文探讨。比如林晓光认为,在 1972 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路径上,两国在“政治解决”(中方)和“法律解决”(日方)之间博弈。最终双方通过“政治解决”模式,就结束战争状态、战争责任赔偿等问题达成共识,《中日联合声明》的签订为日后两国解决争议提供了良好先例;
张望则觉得,中日关系长期以来跌宕起伏,与两国之间的不信任密切相关。这种战略互疑正是源于 1972 年未完成的和解,很多历史遗留问题在当时求同存异的氛围下被搁置,为日后冲突埋下伏笔;林泉忠聚焦 21 世纪中日国力变化后,两国未作出合宜的心理调适,归泳涛关注 2009 年以来,中美日三边关系的变迁。
07
几条文化新闻值得一看。在美国一项艺术比赛中,一幅获得数码艺术门类一等奖的作品引起争议,因为它完全由一款软件生成;波兰执政党向德国提 1.3 万亿欧元二战罪责赔偿,但德国外交部回应称,德国联邦政府的立场没有改变,赔款问题早已解决;作家王朔时隔 14 年的小说《起初·纪年》备受争议,反响不一;
美国政府公布 2021 年高校毕业生数据,除哲学外,所有人文类学科毕业生都在大幅减少,而在 2000 年到 2010 年间,人文类学科毕业生增幅可观。彭博专栏作家诺亚·史密斯(Noah Smith)据此认为,彼得·图尔钦的“精英过剩”(Elite Overproduction)理论在 2000 年代到 2010 年代与现实高度契合。
图尔钦觉得,2010 年以来,美国高等教育“大跃进”,学费暴涨,生产出大量高学历人口,但却没有提供符合这些学费支出和学位预期的工作岗位,那么根据历史动力学的“结构人口理论”(Structural-demographic Theory),这些“过剩精英”就变成社会不满的活性因子,转向激进甚至破坏性的政治立场。这可以用来解释过去近十年美国政治和社会思潮变化。
08
几部英文世界的新作可以留意。J.K.罗琳的新书《墨黑之心》(The Ink Black Heart)讲述漫画创作者伊迪·莱德威尔(Edie Ledwell)的漫画被批评为种族主义、对残障人士和跨性别的恐惧症。一些评论认为,罗琳在小说中代入自我,但她本人予以否认;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诗人露易丝·格丽克将出版首部小说《万寿菊与玫瑰》(Marigold and Rose);作家杰克·凯鲁亚克的私人日记及部分尚未发表的作品将结集为《荒凉峰》(Desolation Peak)出版;
伊恩·麦克尤恩出版新小说《课》(Lessons),通过讲述罗兰·贝恩斯(Roland Baines)的故事,串联起苏伊士运河危机、古巴导弹危机、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撒切尔主义、伊拉克战争、英国脱欧、新冠疫情等重大历史事件。他想探讨,我们无法控制的全球事件如何塑造我们的生活和记忆?我们能从过去的创伤中真正学到什么?
09
8 月 15 日,法学家亨利·梅因诞辰 200 周年,他被看作近代法律史、比较法学科的开路先锋,著有《古代法》等;8 月 22 日,作曲家阿希尔-克洛德·德彪西诞辰 160 周年,他被认为是西方现代音乐的开山鼻祖;8 月 24 日,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诞辰 120 周年,他是法国年鉴学派的领军人物,代表作为《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等;
8 月 29 日,哲学家约翰·洛克诞辰 390 周年,他是英国经验主义的代表,被广泛形容为自由主义之父,著有《政府论》《人类理解论》等;9 月 9 日,顾毓琇逝世 20 周年,他文理兼修,在科学、诗歌、戏剧、音乐、佛学、教育等方面均有贡献,被称为“现代中国的达·芬奇”。
10
8 月 17 日,作家张北海(1936—2022)逝世,他被侄女张艾嘉说是“中国最后一个嬉皮士”,陈丹青称其为“纽约蛀虫”,姜文的电影《邪不压正》改编自他的小说《侠隐》;8 月 20 日,鄂温克族老人玛丽亚·索(1921—2022)逝世,回到了森林和驯鹿身边,她被誉为“中国最后女酋长”,也是《额尔古纳河右岸》主角原型;
8 月 24 日,企业家稻盛和夫(1932—2022)逝世,他曾创办京瓷、KDDI 两家世界级公司,挽救日本航空于破产边缘,并以其管理学思想和人生哲学影响了许多人;9 月 1 日,作家芭芭拉·艾伦瑞克(Barbara Ehrenreich,1941—2022)逝世,她是活跃的女性主义者、民主社会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长期关注美国底层社会,著有《我在底层的生活》等;9 月 4 日,作家彼得·斯陶伯(Peter Straub,1943—2022)逝世,他以恐怖小说闻名,探索人类未知,曾与斯蒂芬·金合著作品。
题图来自 Marjan Blan | @marjanblan on Unsp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