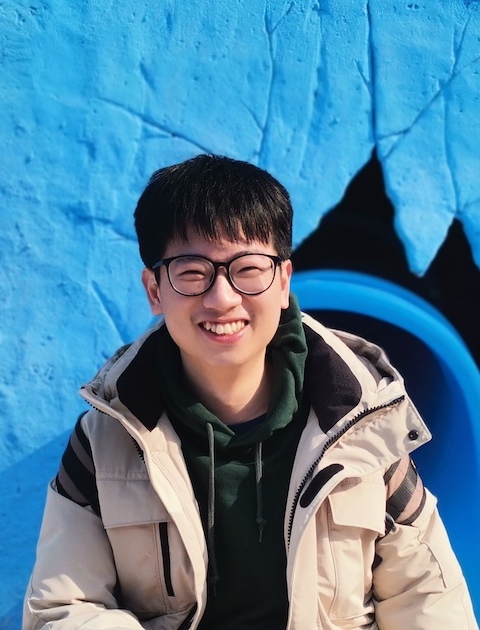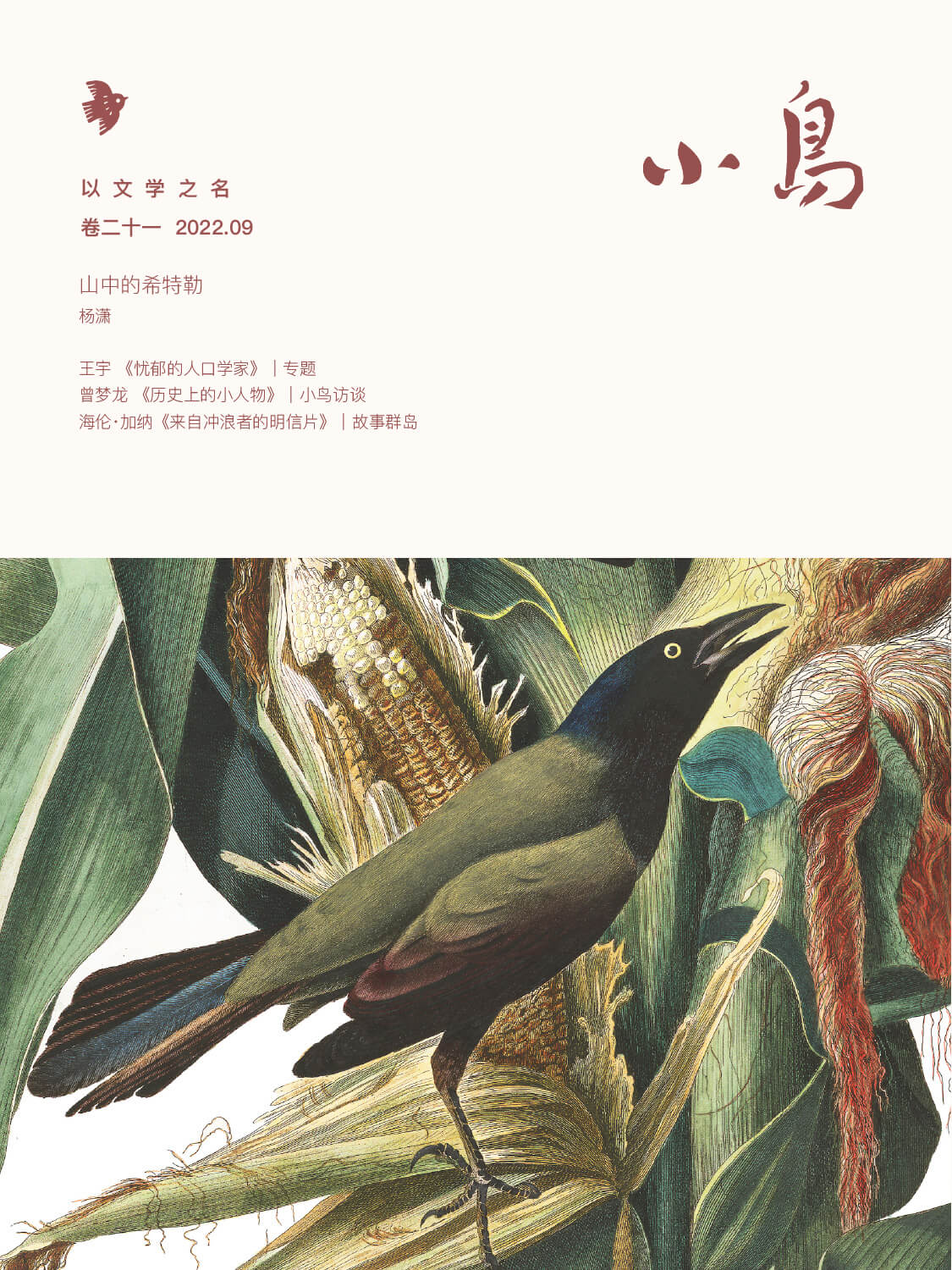9 月 6 日下午,我在北京的圆明园南门见到了罗新。他身穿浅灰色徒步服,戴着遮阳帽和墨镜,背着双肩包,装备看起来非常专业。
一个多月前,他跑到四川,和美国记者、作家保罗·萨罗佩克(Paul Salopek)一起徒步三周,参与其跨越大陆的“走出伊甸园”之旅。这段时间前后,他的新书《漫长的余生》恰好出版,受到许多媒体关注,在线上接受了几次采访。所以当我 8 月底联系他时,他说最近采访接受得比较多,严重影响表达欲望,建议在外面边走边聊,这样可能放松些。
《漫长的余生》讲述了北魏宫女王钟儿 86 年的人生,并以她的视角看她身处的时代。“我们关注遥远时代的普通人,是因为他们是真实历史的一部分,没有他们,历史就是不完整、不真切的。我们还应看到,对普通人的遮蔽或无视,是传统历史学系统性缺陷的一部分,是古代社会强烈而僵硬的不平等体制决定的。……关心弱者、为边缘人发声,不正是当下历史学人的重要责任吗?”罗新在书中写道。
罗新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他 1963 年生于湖北随县,博士毕业于北京大学,师从田余庆,专研魏晋南北朝史和中国古代民族史,著有《中古北族名号研究》《王化与山险》《黑毡上的北魏皇帝》等专业著作,以及为一般读者更熟知的旅行文学《从大都到上都》、学术随笔集《有所不为的反叛者》。
碰头以后,我们开走。他回忆道,自己本来对圆明园不熟悉,熟悉这里是在 40 年前,刚上大学的时候,那时没有院墙、门票,这里就是农民的稻田。下午四点左右,他经常会从北大东门出来,走到这里,转一两圈。那是当时的生活方式。不过,上研究生之后,他就不来这里了,直到今年。
“我整个半年没有离开过北京,在北京也不能随便逛人多的地方。那阵朝阳也不能去,听起来像魔鬼一样,所以就哪儿也不去。最惨的是有一段时间不能进学校。那我怎么办?人又不能不动,不动不知道哪一天要出什么状况,所以就跑到圆明园来。那是我好多年之后再次进圆明园,开始摸索圆明园是什么样子,对我来说太新了,当年是到乡下,现在是个公园。我就有一个探索的过程,现在基本上搞清楚,大概是想在结构上像清代。”罗新说。
在他的带领下,我们穿梭在圆明园不同的景观之中,路上还碰到了长得像灵芝的菌类,被狂风刮倒的树木,嘴里咬着核桃、蹦蹦跳跳跑过的黑鼬[1],话题也从《漫长的余生》出发,涵盖普通人与历史的关系、权贵们被皇权的裹挟、早期佛教提供的自由、历史学如何介入不平等、计划写的崔宾媛和她家人的故事,以及从 1980 年代至今,罗新从文学到历史、从中心到边缘、从为学术而学术到关心和参与现实的转变过程,等等。
相比视频中呈现的腼腆,徒步过程中的罗新放松许多,表达也更为铿锵有力,有时他还辅以手势或者拿周边事物(如围墙、建筑)加以说明,生动有趣。绕圆明园一圈后,我们走到北京大学东门分别。他最后说:“我去做一个核酸。”全程大概十一公里,耗时两小时十五分钟。
以下是《小鸟文学》和罗新教授的访谈节录,因内容过多,分两篇发布,这是第一篇。他觉得,“普通人的故事,才是时代的主流”。不过,这里的普通人不再仅仅是政治法律和社会经济地位的普通,更是人格意义上的普通。即使是皇帝,七情六欲也使他普通,在人格意义上跟我们一样,也会悲哀、畏惧、胆怯、愤怒……归根结底,普通人的历史是人的历史。“历史学家的最终关心应该回到人,而不是任何政权、文化、人群。”罗新说。
01
以普通人的视角看世界
小鸟文学:在《漫长的余生》中,你希望通过讲述北魏宫女王钟儿的一生和她的时代,书写普通人的历史。不过,一些读者看完全书后,有点心理落差,印象最深刻的倒不是王钟儿,而是她身处时代中的各种权力斗争和杀戮。我觉得这一方面是现有材料所限,你以历史学家的技艺已经让我们极大程度上接近王钟儿了;另一方面,这或许也是普通人在大时代下的命运,常常身不由己,没有什么选择。
不知道你是什么感受?我们又该如何理解你倡导的普通人视角,它有什么特点?你又怎么看普通人和时代、社会之间的关系?比如同样是关注普通人的历史,有些历史学者会强调普通人的能动性,写他们同样参与和塑造了历史,比如霍布斯鲍姆的《非凡小人物》;也有一些社会学家,比如布迪厄的《世界的苦难》,更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与宏观社会历史之间的有机联系,从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视角揭示苦难根源。
罗新:我对任何关于普通人与历史关系的说法都没有反对,包括说任何人都是能动的,弱者也有自己的武器,弱者也有塑造历史的强大力量,像詹姆斯·C.斯科特那种讨论,我很赞成,我很喜欢。可是呢,涉及到这个写作,我无能为力。我不能多说违反(历史)学科规矩(的话),说我找到王钟儿在做各种努力,发挥能动,没有的。但是,我想任何人都在能动之中,她选择屈服,选择在屈服之中仍然努力,这是可能的,但我们不知道。从历史学意义来说,不知道的最好不要说,讨论这个是危险的,所以我就不说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