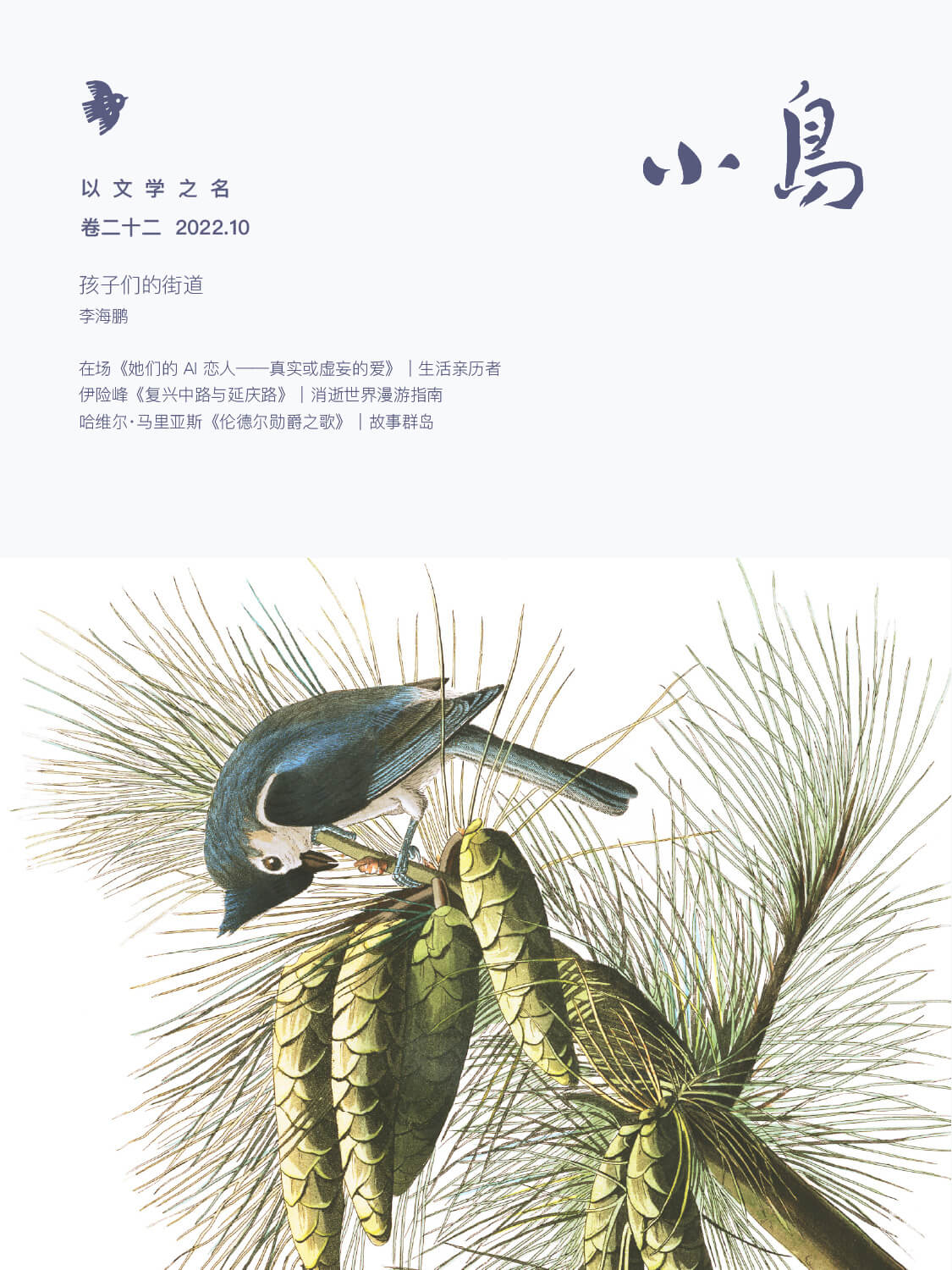有场比赛别人可能不记得了,2010 年 12 月 14 日在老特拉福德。阿森纳球员们走出通道的样子我还有印象,身体语言不好。阿尔沙文显得疲惫,尽管他才 29 岁,比曼联队最老的队员小了 8 岁。查马克,实力不足的摩洛哥前锋,抱着胳膊,紧张不安,一副自我保护的样子,即将原形毕露。我们最好的出场球员纳斯里,不断地往伤手上缠着绷带。没有人吼叫,没有人笑,甚至没有人说话。不是放松和自信的迹象。作为对比的是,在曼联一方,纳尼像个拳击手那样摇晃着脖子,里奥·费迪南德横着膀子,一头扎进了万众欢呼的声浪中。在赛前,推特上,他声称他们将赢得比赛。比赛胶着,两队一点点地彼此消耗,正是曼联希望的。第 63 分钟阿森纳不得不派上两名明星伤员法布雷加斯和范佩西,然而于事无补。阿森纳队又一次输掉了比赛,比分只是零比一,但是场面上没有机会。现在积分榜上的第一名是曼联了,被取代者正是阿森纳。赛后,俄国媒体采访阿尔沙文,你们何时才能战胜曼联?这也正是我们赛后讨论的问题,阿尔沙文回答说。
整场比赛,曼联都在密集地逼抢阿森纳的右后卫,阻止他传球给前面的纳斯里。有点儿反常,但孤立你唯一的威胁点称得上毒计一条。那名右后卫多次回传门将,而曼联的前锋不断游弋,伺机断下回传球,就像三条猎狗驱赶兔子,第四条等在预留出的线路上。我看到的是,兔子们,阿森纳全队,徒然挣扎着,束手无策。
当时阿森纳已有很长时间无法与最强的球队抗衡了。我曾假想自己给主教练温格先生发一封 email,我会说:
“尊敬的温格先生,我是一个中国的阿森纳球迷。对我身边的很多阿森纳球迷来说,你和阿森纳俱乐部是一个象征,几乎是理想主义的同义词。我们不希望看到理想主义失败,因为我们已经看过太多的理想主义的失败了。无论如何,请为我们去获胜。”
这场比赛让我停止了关于邮件的假想。有句令我印象深刻的电影台词,“没春袋的都好麻烦”,出自《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春袋”是睾丸。那一天我发现我支持的是一只没有春袋的球队。那是我第一次对阿森纳产生失望感,但它是决定性的,恰如恋情生变的那一刻。此后 7 年多来,一般无二的情节不断重演。每年一到 11 月,天冷了,阿森纳的困难时节就到来了。曾有连续 5 年,他们在 11 月的比赛中得分低于 14 分。12 月,圣诞赛季,也难。此后起起落落,时喜时忧。待到春暖,球队又似恢复元气,可是尘埃已定,冠军旁落。好消息是,寒冷季节过去了,我们又将希望托付给时间。失望的阴影以一个缓慢到难以察觉的过程四处爬伸,于是终有一日,对我来说,阿森纳已经成了当初我喜欢的那支强大的球队的幻影。我仍然看直播,期盼它赢,仍是它的百分百的球迷,依照着习惯。但是球场上已经没有一个球员是我愿意认同的了。我尽量不再为它而情绪波动,只是带着一种超然的态度盯着屏幕,想,不对,不是,这不是阿森纳。
* * *
在此之前,阿森纳是创造了 49 场不败纪录的无敌舰队和英国足球的革新者。阿森纳的主教练完全令人信服,“In Arsene we trust”。阿森纳踢的是取悦观众的攻势足球,它的追求是“艺术”。它甚至是体育精神的化身,拒绝对己方有利的误判点球而要求重赛。如果这一切延续下去,阿森纳将成为一种虚假的东西:过于完美。你可以从曼联队员的回忆中听出那种本能的文化厌恶感:阿森纳似乎高高在上。曼联本是一个“Win with style”的伟大俱乐部,但在终结阿森纳 49 场不败纪录的那场比赛中,通过今天依旧随处可见的集锦,你可以看到,曼联球员暴力犯规的程度和数量触目惊心,火气十足,怀着深重的恶意。
不同的人会对那场比赛做出不同的解读,英式斗志的胜利,或者对足球的犯罪。但我看到的是一种类似于阶级战争的东西,两组年轻的富豪站在不同阶级文化的阵营,在规则被打破的前提下,更残酷的一方获得了胜利。
回顾往昔,我想,在事情顺遂的时候人们总是不能警惕,最好是好的敌人。阿森纳仍想在完美之路上再进一步,建造新球场。首先提出计划的正是温格。“我已经不太记得我究竟在什么时候向董事会提出兴建球场的建议了。”他曾回顾,无论如何,“这是阿森纳队史上自从 1925 年请查普曼执教以来最重要的决定。”
那是阿森纳球迷的体验感变坏的起点?是的。但是在背负了新球场带来的沉重债务那些年里,美好事物依旧闪烁着。它包括了温格的风度,冷静,始终如一地充当俱乐部、董事会和球员们的保护人的胸怀;包括了依旧美丽的足球,一种逼人的锐气。包括了 07-08 赛季的闪耀,包括了在已经进入下滑周期后,10-11 赛季欧冠 1/8 决赛两回合仍旧表露出的精神力,尤其是考虑到面对的是巴萨。在那个时期,巴萨创造了全新的足球,令人绝望,无与伦比。看他们的比赛,如听音乐是为了音乐之美。同样地,如果你喜欢足球,你也会喜欢阿森纳 2 比 1 战胜巴萨的比赛。任何时候我都能清晰地想起那条传球路线,本特纳-威尔希尔-法布雷加斯-纳斯里-阿尔沙文。那是令人窒息的压力之下,一条一闪即逝的美丽的生路。明亮的希望感重新照临了。法布雷加斯说,“我没踢过更棒的比赛了。”威尔希尔说,“这是我在阿森纳最辉煌的一个夜晚。”
可是自从阿布带着石油金元来到英超之后,“希望感”已经不可能兑现。一切都变了,阿森纳没办法与对手竞争。温格固执地穿越窄门,任凭对手对他和阿森纳的敬畏消失,开始了奚落和攻击。“恋童癖”是一个滑稽的例子。2010 年 12 月 14 日那场比赛之后,曼联球员埃弗拉则说,阿森纳是个青训营,曼联打阿森纳就像大人打小孩。他已经不止一次这么说了。在情感上球迷们好似自己也受到了攻击,一切都让人恼火不已。
关于“理想主义”的那封邮件显然太温和了,那更多地是客气的说法。“尊敬的温格先生,睁开眼睛看看这个功利主义的世界吧,”在我真正想写的另一封信里,我会更加急切,“睁开眼睛看看这个真实的世界吧。”
那是令人窒息的压力之下,一条一闪即逝的美丽的生路。
让人感到“日了狗了”的时候太多了,球迷们感到的不只是失望、愤怒,还有难以索解的困惑。这一切怎么可能发生?为了那场联赛杯决赛,法布雷加斯的父母和姐姐都来到了伦敦观赛——仅是“米老鼠杯”而已。可是难以解释地,阿森纳输给了即将联赛降级的对手。被升班马双杀。总是不能战胜曼联。对阵热刺连吞三弹之际,“德神”笑得心无芥蒂。在欧冠对阵利物浦的一场戏剧性的比赛中,最后时刻,以盲目自傲著称的本特纳出现在对方球门线上,挡出了队友的本可以决定比赛的射门。至今我仍记得他试图躲开时的笨拙动作。球来了!为时已晚。4 比 0 领先被追平。鲁莽造点,在为保留夺冠希望而战的比赛的最后一秒钟。那个赛季就此结束。这些事怎么可能发生,如果我们喜爱的球队还叫一只球队的话?最终,这些年里为之喜为之忧的阿森纳球迷的记忆,总会被一种天不佑我的感觉带回到爱德华多断腿的那场比赛。那是 07-08 赛季,阿森纳正在创造一个新的奇迹,过分年轻却夺冠在望,而且踢着英国足球史上最漂亮的足球。在粗暴的犯规发生、爱德华多的左腿胫骨完全折断并刺穿了球袜之际,直播镜头不得不移向别处。在不怎么移动的远景镜头中,双方球员不时地抱头,有的球员在大声呼喊,医生在草坪的远处忙碌着,担架,氧气瓶,球迷们在祈祷,震惊感弥漫了整座球场。这也是阿森纳命运的决定性时刻。比赛恢复后,对手打进一球,球队的队长竟然放弃了比赛,独自走进中圈里坐了下来,好似在生闷气。一场悲剧,又由荒谬点缀。随后球队军心摇动,连续失分,竟让冠军旁落。可是这时候还有什么是重要的呢?就连球迷们,向来索求胜利永不餍足,那时也只想祝福爱德华多早日康复。阿森纳的运气耗尽了。从此一切都走向反面。
* * *
晚至 13-14 赛季初,如果说曾有一些球迷在厄齐尔到来那一刻感到隐隐的不安,甚至不无失落,那么这个奇怪的阵营中也包括我。我当然为俱乐部终于摆脱财务困境迎来巨星而感到开心,但另一面,我也感到,在买来厄齐尔的那一刻,那个“实验”已经终结了。温格在对他的年轻球员政策做出的一段解释中提到了这个实验:
“让球员完整融入我们的足球文化,依靠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价值观,在尽可能年轻的时候得到他们,然后培养出一个集体。我认为这会是一个有趣的实验,看到这些球员依靠他们的实力一起成长,带着对俱乐部的热爱。”
终将令我难忘的阿森纳故事,就是这个从未被正式认证过的“实验”。它体现着一个真正的故事的要素:愿望、难以逾越的困难、自身的心魔、悬念。曾予取予夺的阿森纳,只是日常生活中的壮丽景观,还算不得故事。实验故事,始于 2004 年 3 月 1 日,终于 2013 年 9 月 3 日。酋长球场动工那一天——买来昂贵球员的那一天。
* * *
必然地,温格的实验让我想起莫丽尔·斯帕克的灵巧、优美的小说《布罗迪小姐的青春》。在 1930 年代的爱丁堡,女教师布罗迪小姐正值青春,将 6 个女孩视如己出。“给我几个正当可塑年纪的女孩,我将把她们变成人类的精华。”她的热情全部倾注于此。不幸的是她把女权跟对法西斯的浪漫想象结合到了一起。一个女孩,桑迪,终究是出于年轻一代反抗权威的动机,背叛了布罗迪小姐。温格的实验,与此如出一辙。
其他人难以理解阿森纳球迷对“背叛者”的气愤。区别是,或许他们多多少了解“实验”,但并未“经历”它。
宋的买入价是 100 万英镑;科洛·图雷是 15 万,原俱乐部含羞草,位于一个我只在《大航海时代》中见过的地方阿比让;克里希是 25 万。你就是买我,我妈也不会光跟你要 15 万。这是实验的璀璨一面:财政拮据的阿森纳,凭借实验的质量,让资质平平的年轻人获得成功。阿德巴约则代表了实验的暗面。刚加入俱乐部时,他是个每次停球都停到 10 米外的球员。有一次亨利向他不耐烦地怒吼。你是队长,我在心里对亨利说。就像亨利的性格中始终有急躁一面一样,温格的显著长处是对球员的潜力保持超人的耐心。阿德巴约在他在阿森纳的最后一个赛季打进了很多球,然后想另谋高就,频繁地告诉媒体,米兰等几个球队就是他的碧昂丝女神。球队因此变得不安定之后,俱乐部把他卖去了曼城,就像一个本想主动分手对方却先开了口的恋人,他开始恨阿森纳。对阿森纳进球后,他报复性的庆祝纵贯了球场,飞奔 90 米之后向阿森纳球迷所在的看台滑跪。弗格森说了他的观感:这个男孩的睾酮真高。我想他指的是失控。愤怒消退之后,我开始想一个有趣的问题:阿德巴约会不会终有一天也说,他感谢温格?就像那几年间陆陆续续地,几个“叛逃者”,赫莱布说过的,纳斯里说过的,范佩西说过的。后者们的情形不同。他们本来就是天才,很难评估如果没有温格的话他们的成就会减色几许。但是还有人记得 09-10 赛季之初范佩西说了什么吗?他说他不该踢中锋,他不适合。是温格让他成为了禁区里的杀手。对“叛徒”们的愤慨全在于他们欠温格的情。无论如何,几年之后远在土耳其联赛的范佩西回顾说,温格是最好的教练——在他经历了弗格森爵士之后。
最终他们都说了《布罗迪小姐的青春》中桑迪说过的话。在小说的结尾,一个来访者问桑迪是否有谁影响过她的一生,桑迪抓紧了眼前的栏杆,想到了她背叛过的那个人,她说,有过一个正值青春年华的琼·布罗迪小姐。
真正的桑迪——停留在比喻意义上——是法布雷加斯。他从 16 岁零 177 天起为温格出场,是成熟度远逾年龄的天才,也是对阿森纳最近的历史和温格本人来说最特别的一个球员,他几乎就是“实验”的象征。在别的以惊人廉价买来年轻球员中间,他鹤立鸡群。温格为了他而卖掉了维埃拉,49 场不败时期的队长——他们不能配合,温格后来说。这是我唯一一件不能原谅温格的事,为了给新苗腾出地方,伐掉了大树,事功迷人眼目,况于亲炙之者。其后几年间,温格与“小法”情同父子的形象几乎就是足球世界中“教育”的代名词。可是最终,法布雷加斯离开了,在 2001 年低价转回巴塞罗那,在至少持续了两年的一系列充满戏剧性的公开策反与放风之后。他的新里程难以概述,虽然成功,但再也没有重现阿森纳时期的那种光亮。三年后他加入切尔西,投身于温格最著名的一位攻击者麾下,也恰如小说中,桑迪竟跟劳埃德先生睡了觉。当然,另一立场的反问也是无法辩驳的:法布雷加斯跟温格签了奴隶合同了吗?没有,的确没有。
或许他们多多少了解“实验”,但并未“经历”它。
“实验”曾熠熠生辉,尤其是当年轻人在次要比赛中获得机会时。平均年龄 20.5 岁的阿森纳压得尤文图斯喘不过气来,平均年龄 19 岁的阿森纳则 6 比 0 战胜谢菲联。“天才云集”,是之谓也。法布雷加斯的离开则是阿森纳实验室的一次宕机,动摇了实验依托的信念。更冷静地说,在年轻球员身上的投资,到了考虑止损的时候了。温格还要继续把希望寄托在实验上面吗?他在坚持,显然非如此不可,但是坚持不了多久了。
“尊敬的温格先生,能赢得年轻人的忠诚的从来不是爱与教育。”我假想这样一封邮件,“我想我们都该减少一点儿理想主义了。”我想说,“我希望你是不得已,而不是想这么做,我希望你一点儿也不想这么做。”
“一位真正的绅士”,就在几天前,在温格宣布他将在赛季末离职时,他的队员和前队员们都在推特上这么评价他。“父亲般的”,他们的说法彼此接近,“感谢你给了我机会”,“始终对我抱有信念”。其中也包括了已成“老法”的法布雷加斯。整个英国都在说着感谢与珍重。场面如此真挚温馨,以致温格开玩笑说像在参加自己的葬礼。说得好。也许我太冷酷了,但我想起的是《套中人》的结局,令所有人感到不舒服的别里科夫死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又要隐藏轻松感,于是在葬礼之后,“所有人都露出了谦虚的神情”。自然,这也是对完美风格的致敬,是投向过去的温情一瞥,是实至名归。只是,冯唐易老,布罗迪小姐已经青春不再。
* * *
中国的一个政治性神话是卧薪尝胆,柯文教授就此写成了一本书。经过历朝历代的政治性建构,卧薪尝胆由最初的一个故事升级为了故事模型,进入集体潜意识,人们开始默认其必然性,即无论面临多么巨大的挫败与阻碍,只要意志坚定,就可以完成甜蜜的复仇。问题是,谁赋予了这种必然性,除了刻意的修改、阐释和重复之外?温格的实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卧薪尝胆的现实版本,不同的是,这个勾践在卧薪尝胆的岁月中耗尽了他的锐气和精力,他的知识也已落伍,时光荏苒,却已无力进攻吴国。越国人民不愿原谅勾践,开始呼吁 “Goujian out”。当老去的勾践黯然去国,人们又变得伤感起来,说起了“merci Goujian”。
卧薪尝胆与布罗迪小姐的故事体现了当事者一致的信念:相信时间会带来奇迹。可是时间会带来何种奇迹?
在财政不足的情况下,把年轻人培养成一支球队的主干,留住他们,作为一个团队去实现梦想——从一开始这就是不可能的。耶稣和他的 12 个门徒。努尔哈赤和他的 13 幅铠甲。温格和他的 11 个首发?克里斯玛式的领袖,年轻人,传奇事业。你知道这是什么:被塑造的神话。我回顾温格的实验计划时,不无吃惊地意识到它本是一个 BUG,一个田园诗或者空想社会主义那类的东西。但它也是任务。让骑士之所以为骑士的那种不可能的任务。
2007 年,俱乐部的强人大卫·邓恩,雇佣了温格的人,被排挤离去,权谋、创新和引入新资本的可能性随之东流。次贷危机阻滞了海布里公寓的销售,债务压力最重的 4 年恰好一同到来。前一个赛季末危机已现,温格拒绝了皇马留了下来——多年后屡遭质疑时他说,他曾拒绝了全世界——不可能的“实验”就成了俱乐部的救命稻草。为什么在泰坦尼克号要沉没的时候,船长一再拒绝逃生?也许温格本人也带有浪漫幻想,也许他只是坚守准则,无论如何,他继续了他的实验。这不过是牛犊顶橡树,摇撼不了什么。但是整个故事中令人莞尔又深具魅力的部分因此到来了。我们,温格先生、俱乐部、球员、全球的球迷们,每个人都“经历”了这个实验,为之倾注了情感,每个人知道它很难实现,却都不愿承认它必然失败。自然我也是其中之一。多半是因为我们拥有温格。因为拥有温格,俱乐部可以卖掉球员变现,球队实力下滑可以止损,当所有人都认为阿森纳已经沦落之时,我们仍旧抱着幻想,期待奇迹。阿森纳终于成为了一家如此独特的俱乐部,给你的快乐如此之少,烦恼如此之多,但是如果有谁爱这个俱乐部,他就会深爱。这一切都维系于一个自我催眠式的计划,而且发生在高度发达资本主义年代。这就是那个我将永远深藏于心的阿森纳故事。
有一次我在网上看到一位利兹联球迷的话,相信我,他更惨。他的球队已经掉到英甲了,他在网上找场球看都难。何苦依旧喜欢利兹联呢?也许我们都很难解释,为什么你一生中可以喜欢很多女孩,却只能喜欢一只球队?
也许是补偿?我不知道。也许这是对生活中无法实现的一生一世的梦想的补偿。大卫·邓恩则解释了温格为什么留在阿森纳。“阿尔塞纳,你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吗?”邓恩离去前曾问。温格问是什么。“你爱俱乐部太多了。”
如今,一切已经往事,“父亲般的”温格已经散发着过时难闻的老人味儿。如果说 2004 年 3 月 1 日 - 2013 年 9 月 3 日期间,足球世界发生了什么深刻的事,那么就是爸爸的死去。当初弗格森把贝克汉姆、范尼和海因策扫地出门的强悍已不可能重现。一位步履所及必起风波的肃反大师,如今也踉跄难行。主教练的父权时代结束了。足球变得娱乐化,事实上,世上的一切都在卷入娱乐漩涡。内马尔的转会标志着球星的权力直接来自于全球市场:人民所授。新一代的成功教练都是小权力的技术型教练。杀人诛心已落伍,况乎春风化雨。
不仅温格不会重现,伟大教练的概念也许也将凋零。终有一天人工智能会接管教席,带来令人瞠目结舌的足球,让今日之事化作烟尘。“现实”在飞速流逝,我们经历的这一切都轻如鸿毛,不足为道。但是对我来说,仍有两个问题值得一问。第一个问题是,温格是一个伟大的人吗?阿森纳球迷会认为称自己的主教练“风范长存”并不矫情,这就是答案。“我相信对待任何事物的目标是让它升华为艺术。”我记得他说。我们也知道他做了什么:22 年,每周 7 天。更重要的是他有着真正的愿望,我想。那是带有利他主义色彩的愿望,是布罗迪小姐那种愿望,那种你知道会让你备尝痛苦却愿意为之备尝痛苦,虔心期望成真却多半不会成真的愿望,那种真正浪漫的愿望。另一方面,在“几代人的温格”执教期间,在迷惘青年与迷路中年之间,我自己也开始警觉,人生不是别的,就是愿望旁边的那些东西。所以第二个问题是,我还有何愿望?
“尊敬的温格先生,如今你已不复当年,连我也不再年轻了。”在不会发出的邮件中,最终我想写,“我曾想了很久,你和阿森纳对我来说意义何在,毕竟我们远隔重洋。后来我想,对我来说唯一重要的是,世上有一个故事,是你我之间的故事。生活多半是一个英雄梦想被岁月销磨的故事,仅仅触摸它已是何其幸运。我只想告诉你这一点。”
(2018)
题图来自 Nelson Ndongala on Unsp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