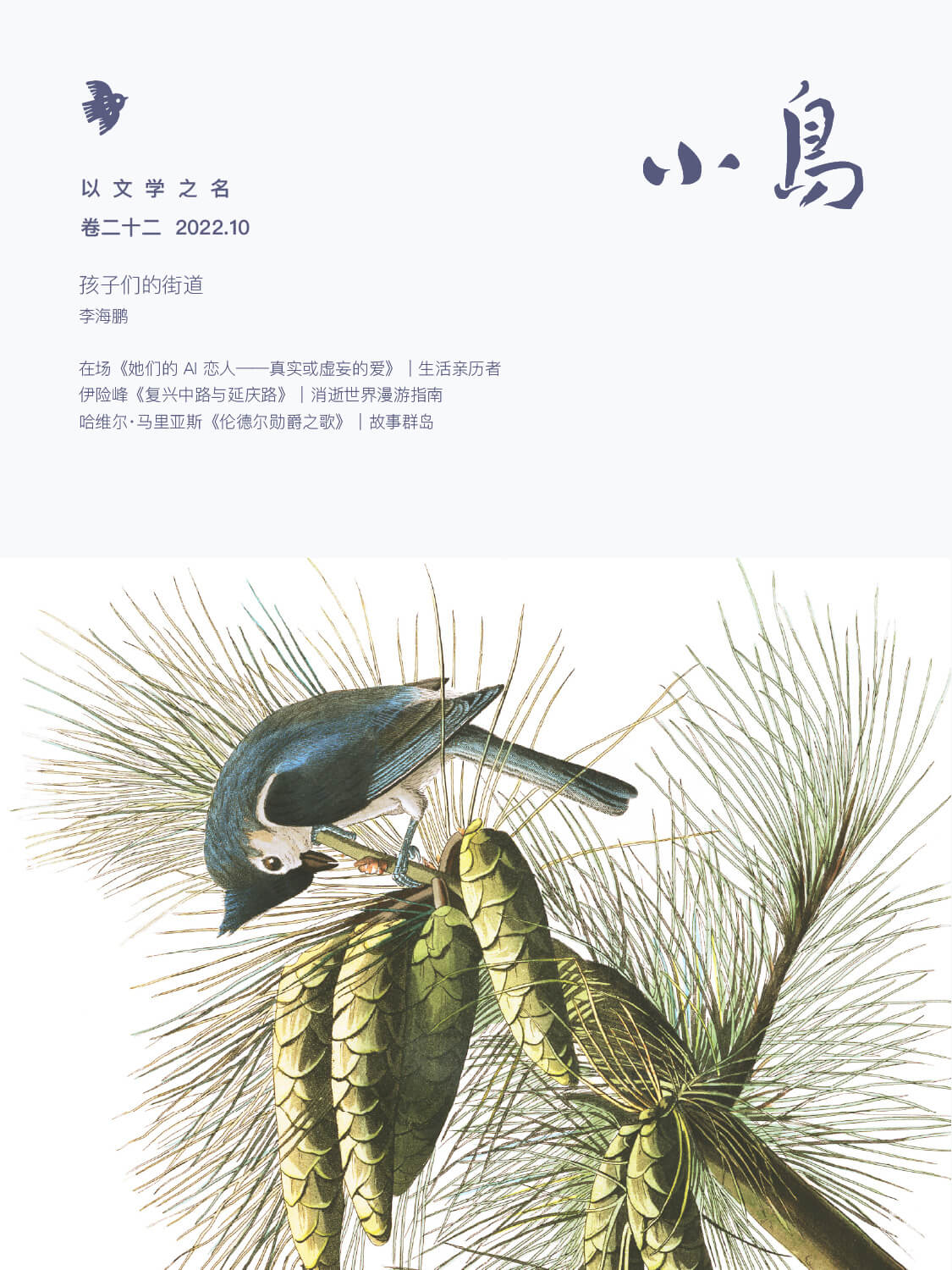2003 年,我住在吴兴路,有一天在街上乱走到复兴中路,看到路边大院子里竟然还藏着一个高高的跳水台,从街上望过去,有人摆出造型,跳下去,阳光灿烂的日子。在街上都能感觉到笑声。
有一些东西,当时看惊鸿一瞥,走过去就过去了,但相隔时久,却念念不忘起来。溢出到街面的笑声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值得挂念,挥之不去。办公室搬到复兴中路之后,每天都会在那条街上走来走去,看不到跳水台。那东西怕是一个梦吧?
它真的消失了,现在那里是交响音乐厅。或许它在未来也可以给某个惊鸿一瞥的人同样磨不掉的记忆……那个人,觉得这暖人颜色的音乐厅,藏着很多的音乐在里面,存下很多记忆在里面。现在看,它是一个地标性的存在,也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地方,不会成为下一个跳水馆,但谁知道呢?跳水馆刚出来的时候说不定也是一个笃信自己可以永远存在下去的建筑,有什么理由会拆掉它呢?哪怕没有人喜欢在户外跳水了。
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要一直存在下去。我们办公到与这个曾经的跳水馆的直线距离实际上不超过 100 米,出我们弄堂门向右拐,与我们平行的一个弄堂是新康花园,过了新康花园就是交响音乐厅,曾经的跳水馆就在这里。城市对文化保持着尊重,在城里的这好地方建了音乐厅,又因为要回避地铁振动干扰,音乐厅又让地铁改道,绕开音乐厅,这都是好事。
***
那是 2016 年?差不多就是这个时候,静谧成了大城市要追求的一个指标,政府在暗地里推动一些事。沿街的店铺,做些小生意或者生意做得很大的,接到了通知:房东不租了。到这个时候,大家对二房东的存在有了更多的了解,那些宣称不租了的,爱找谁找谁,打官司也不大在乎的二房东实际上并没有房屋的处置权,如果你们相处融洽和颜悦色,那么二房东也会跟你诉苦,说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真正房东也没有办法。
各种小道消息拼凑起来,大约会还原这个城市前改革开放年代里的本质。大部分门面房其来有自,都是政府机构或者是军方。军队不让做生意,那就不租了;政府要求城市静谧,那就不租了。所以那段时间里,我们弄堂出来左拐,一排门面房,一家书店,两家乐器行,一家我吵过架再也不去的小酒馆,只剩下一个有执照有房屋经营许可的乐器行留了下来,其它都用砖砌了起来。砌墙也简单,贴着门砌起来,音乐书店的老板和店员看着门外面的墙一点点高起来,我在那里拍照,并没有人管,大家都觉得这事与自己必然无关。那书店卖谱子为主,有自己客群,倒也不愁生计,进弄堂里穿过几个楼门洞,进单元门,还是可以买。外面沿街很快就成了一堵雕着图案的墙,有一段时间里墙上四个一组写着: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还有那个北方风格的长得像个红洋葱一样的女胖娃娃。
***
陕西南路上,原来借着鲜花市场,出了些花店、画廊之类的沿街铺面,那本来是市中心不错的一个特色小市场,甚至,那一段时间里我开始钻研士绅化,这些铺面本来都是士绅化的结果,任何一个城市想让自己的街面升级无非也就是这些 ABC——艺术画廊,精品店,咖啡馆……在经过一段时间的静谧革命之后,铺面砌上了砖,不像复兴中路这几家店用灰色涂料盖棺论定,不知道出于什么心理,主事者直接贴上了壁纸,壁纸显然是特制的,上面画了砖、窗,还好,没有画出门来。
在这一点上,早年引起轩然大波和话题的东八块步子迈得更大。那里现在最核心的地方是大名鼎鼎的上海自然博物馆和静安雕塑公园——跟我们门口的交响音乐厅一样,一个新的让人热爱的好地方。我说的步子迈得更大并非是这两个新建筑,而是周边另外几块,整个旧街区都被壁纸包围了起来,相应位置都画好了窗,门,还有定期更新的老字号,今天是酱园,明天可能就是一个别的东西,这些不过瘾,还画了一些人在墙面上,恢复了场景——有人正从楼上吊下来一个篮子,下面小囡正伸手去接……你从南北高架上呼啸而过的时候,可能恍惚间会觉得回到了民国——与马路对面的南货总汇共同构成了旧日传奇。这横亘了两个街区的旧房子,拆了一半扔在那里,旧住户早就已经离开了,东八块都快二十年了吧?
壁纸上画出来的窗户没有忘记画映出天空的蓝色。这是新闸路上最诡异的蓝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