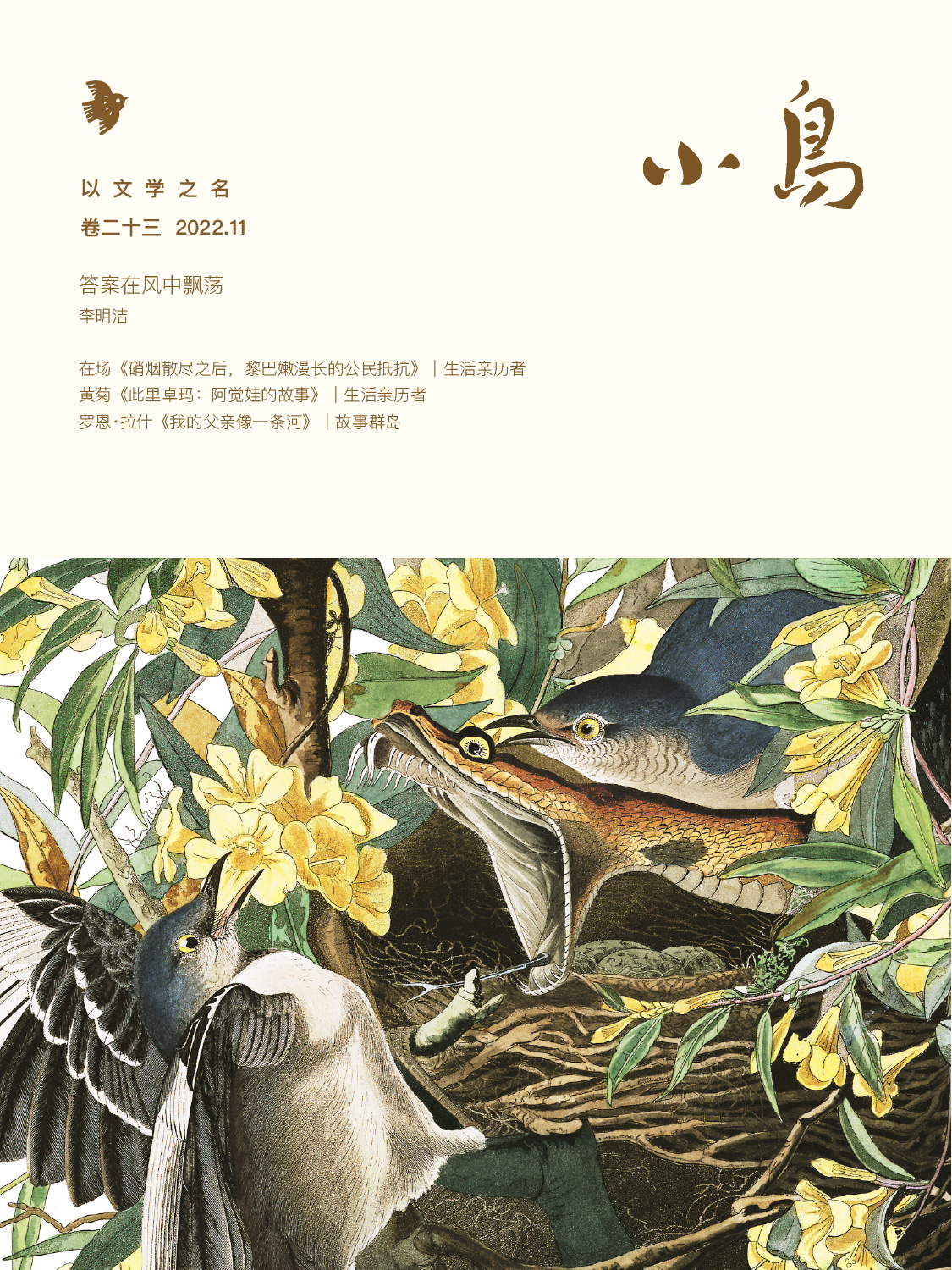圣彼得堡
还是从约瑟夫·布罗茨基《大理石像》的那句话开始。
天气不错啊,各位长官!台伯河蜿蜒流淌,群山一片青蓝。罗马城,这条母狗,近在眼前。
布罗茨基最爱的城市是圣彼得堡。这个在沼泽中诞生的城市,出身不凡。我们习惯于说它与彼得大帝之间的关系,好像一个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画了一个圈一样就在波罗的海之滨对接了启蒙时代,实际发生的当然就如同白海运河、西伯利亚大铁路一样,以无数生命为代价完成——“它是暴君狂妄设想的产物,是专制君主的疯狂梦想”。专制者“平地抠饼对面拿贼”的事做了不少,圣彼得堡更多是幸存者效应,而那些在缺水缺交通缺资源缺人缺所有要素的什么地方搞的废弃的乌托邦是专制者的本职工作——“这个腐烂的、可厌恶的城市会随雾而升起,像烟一般消失”,陀思妥耶夫斯基恨圣彼得堡入骨,诅咒它如烟般消失,那些乌托邦最终命运大抵也就这样。
但在布罗茨基眼中,这个城市何止是美丽,因为诗歌,因为散文,它们构成了第二个圣彼得堡,“散文被一读再读,诗歌被背诵,原因之一是苏联学童如果想毕业就得背诵它们。正是这种背诵,确保了这座城市在未来的地位和位置——只要俄语依然存在——并把苏联学童转变成俄罗斯人民”。
学年一般结束于五月底白夜抵达这座城市的时候,这些白夜将在整个六月份持续。白夜是指太阳只离开天空一两个小时的夜晚,这种现象在北纬(高纬度)地区是很常见的。那是这座城市最神奇的时刻,你可以在凌晨两点读书写作而不需要灯光,建筑物没有阴影,屋顶环绕着金光,看上去就像一套脆弱的瓷器。周围是如此的安静,你几乎可以听见一支汤匙在芬兰掉落的叮当声。天空染上了透明的粉红色,亮得河流那浅蓝色的水彩几乎无法反映它。那些桥则被吊起,仿佛三角洲中的诸岛屿松开它们的手,并开始慢慢漂流,拐入主流,朝着波罗的海游去。在这样的夜晚,很难睡得着觉,因为光太猛,也因为任何梦都比不上这种现实。人不会投下阴影,像水。
布罗茨基出生于 1941 年,被称作“日瓦戈一代”,他们成年之路,最严酷的清洗和战争时期已经过去,社会停滞,未来渺茫,一切看起来都要变成永恒的样子。
很久以前,有一个小男孩。他生活在世界上最不公正的国家。那国家被一群生物统治,这群生物用所有的人类来看,应被视为退化的生物。但没人作如是想。还有一个城市。地球表面上最美丽的城市。有一条巨大的灰河,悬挂在其遥远的底部之上,如同巨大的灰天悬挂在那条灰河之上。那条灰河沿岸耸立着宏伟的宫殿,其正面的装饰是如此美丽,如果那个小男孩站在右岸,那左岸看上去就像一个叫作文明的巨大软体动物的压印。那文明已不存在了。清早,当天空还闪耀着群星时,那小男孩起床,在喝了一杯茶和吃了一个蛋之后,便沿着那条白雪覆盖的花岗岩河岸奔向学校,一路上陪伴他的,是收音机宣布的炼钢新纪录,紧跟他的,是军队合唱团向领袖高唱的赞歌,那领袖的画像就挂在小男孩还温暖着的睡床边的墙上。那条宽阔的河呈白色,冻结着,如同一个大陆的舌头伸入寂静,那座大桥向暗色的蓝天弓起,如同一个钢铁上颚。如果小男孩有额外的两分钟,他会在冰上滑行,再走二三十步,来到河面中央。这时候他只想着鱼在厚冰下干什么。接着,他会停下来,转身一百八十度,跑回去,一口气奔向学校入口。他会冲入大堂,把帽子和外衣扔到一个挂钩上,然后飞也似的跑上楼梯,进入教室。那是一间大教室,有三排桌子,教师座椅背后的墙上挂着领袖的画像,一张有两个半球的地图,只有一个半球是合法的。小男孩坐下来,打开公文包,把钢笔和笔记本摆在桌面上,抬起头,准备听胡说八道。
这个聪明的男孩后来成为诗人,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最多看过的是他的散文和他的回忆文章,不是他的诗。他最著名的经历甚至都不是写诗,而是成为苏联统治后期最著名的段子:1964 年,他因为写诗而被捕,列宁格勒官员以“邪恶的寄生生活”这个罪名把他送上法庭,这事本来就已经够丢人的了,偏偏法官又是一个“高级黑”一样的颟顸角色,问他:“谁承认你是诗人,又是谁批准你成为诗人?”布罗茨基拣到这个问题就像东方不败拣到葵花宝典,“没有人。又是谁批准我成为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