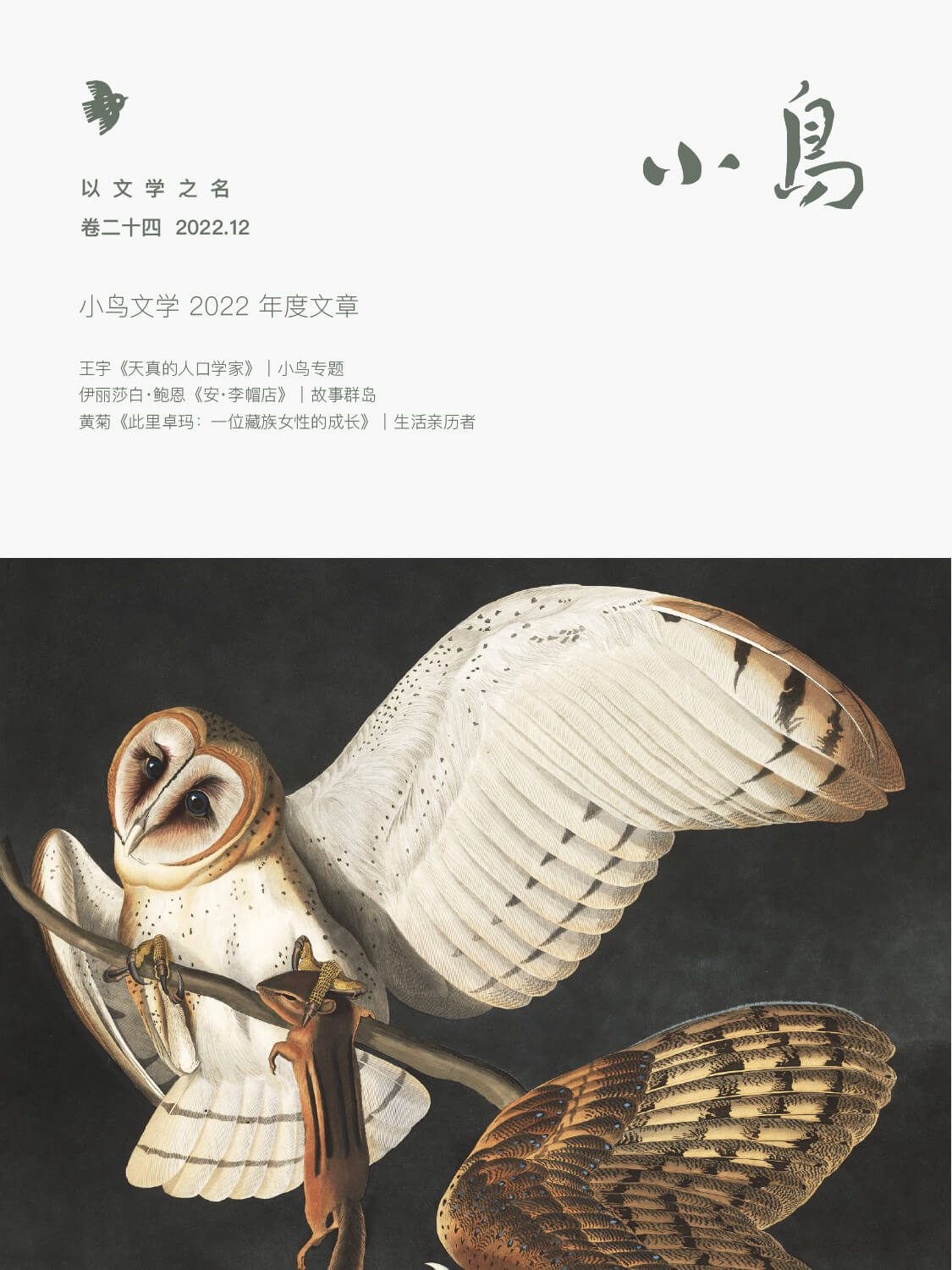01
远古的时候,我国有一座昆仑山。如果从那山上向上走,走到高一倍的高度,就到了凉风山。到了那凉风山上,人就会长生不死。如果从凉风山上再往上走,又走了一倍的高度,就到了悬圃。大概是悬空的花园吧。人就变为人灵了,能够呼风唤雨。要是再往上走,再登上高一倍的高度,就到了天上。天上是大帝的居所,能够登天的,就是神灵了。
我的父亲是一个读书人,书读多了,就喜欢讲故事给我听,讲的故事也不知真假。他讲完故事,倒会由得我发问。于是我就问:
那现在我们能不能上天呢?
不能。
为什么不能?因为有一个皇帝,叫他的臣子把天地之间的通道断绝了。真可惜,天上的悬空花园一定很好玩。我父亲没有告诉我为什么有一个皇帝要叫臣子把天地之间的通道断绝了;我也没有问用了什么方法才断绝的,更加没有问昆仑山现在怎样了,又在哪里。我好想说,我们要怎样才能知道天上的消息,明白天上又是怎样的呢?
只能靠通灵的人了。
谁是通灵的人呢?
神巫是通灵的人。女的叫巫,男的叫觋。
古古怪怪的吧。不是给你讲过有两个人,把天地之间的通道断绝了?那两个人,就是神巫,一个叫黎,一个叫重。他们住在大荒之中的一座山上。
又有一座山,不是昆仑山了?
这山不是昆仑山,是灵山,住着一群神巫。他们的右手操控了青蛇,左手操控了赤蛇,能在灵山上升降。最著名的神巫共有十四位,首领叫巫咸。另外一个神巫更有名,因为她是女巫,名叫羲和,曾经生下十个太阳。
十个太阳,是不是后来给后羿射了下来?
是的。喔,另一个故事,我也该讲一讲。你先背诵《诗经》里《大雅·灵台》的第一章给我听听,就是今天早上我教你的那一首。
好的。
经始灵台,经之营之。
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这是说,古代的一个诸侯,要建一座高台,用来观天。消息在当地悄悄传开后,引得大批庶民前来参加筑台。没多久,高台就建成了,称为“灵台”。
为什么要建一座灵台呢?因为在高高的台上面,天象会观看得更清楚。为什么要观看天象?因为观看天象,才明了天意。据说人世上的一切都由上天主宰,谁成为帝王,谁只是庶民,都由上天做主。明白了天意,也就明白了谁统治、谁受统治。上天会当这个统治的人是自己的儿子,这个人就叫天子。天子的文告,起首不是说“奉天承运”吗?但天象是要某些独特的人去解释的,这些人不是普通人,而是能够通灵的巫师。通灵的人就是上天和人间的中介,由他们解释天意才算合法。君王然后公布天下。庶民于是明白,于是相信。所以,通灵的巫师都受帝王礼待、重用,建立高台让他们观天,再传达上天的旨意。上天永远是公正严明的智者,把天下交托给有德的人。败德者即使获得了上天的眷顾,暂时拥有天下,最终仍会遭上天遗弃,把天下转交另外有德行的人。
可历来的帝王不全是好的,是上天也会犯错吗?我不敢问父亲,因为上天的意旨并不容许猜度。我自己就经常犯错,我错了改过,父亲就说善莫大焉。父亲说,诗中记述的是远古的商代,商纣王是个暴君,遭百姓唾骂诅咒,百姓要跟他同归于尽。那个时代,国家只是部落的组合,各有领主。纣王其实只是盟主,因为暴虐,不听劝告,不少部落的领主想推翻他,更有的想夺取王权。其中一个姬姓领主在周原这个地方筑建灵台,观看天象。一直以来,所有土地,都属于王土,天空也不例外,只有天子才能够筑建灵台,其他领主不可以观天象,不可以拥有灵台,更不要说庶民了。然而,姬姓领主竟在自己的地方筑起一座灵台,又让群众参加建造,建成了,又有通天的人上台观天文。这是僭建,真是司马昭之心,路人不用观天,都知道了。观天的结果,果然就是:上天指示,要驱除无德暴君,拥立有道的新君。有道的新君,就是他了。
啊,我于是想,上天原来也知错能改。
父亲教我读书的时候总告诉我许多故事。父亲和我都喜欢在夜晚观看天上的星斗。父亲要我注意灵台的“靈”字,顶头是云雨的雨,中间有三个口,下面呢,就是巫,是仰头看天的女巫。所以,灵台就是巫台。那年我九岁。
02
父亲一直喜欢观星。每当星空清朗,父亲就带我到户外院子纳凉,抬头望天,迟迟不睡。众星在头顶不远处闪耀,发出银光,忽暗忽明。有时,父亲和我还攀上屋顶,卧在瓦上,那时众星似乎又亲近了许多,仿佛可以伸手相握了。我父亲认识很多星,能够一一称呼它们的名字,辨认它们的位置,如同熟悉的朋友。而我,只见夜空上有一道银河,千百星星泳于河中,闪烁着眼睛,好像有许多话要说,但欲言又止。父亲能把星星或一颗,或一群,辨认得清清楚楚。父亲是古史中的神巫吗?他说不是,说神巫什么的,他才不屑哩,最多勉强列入最低级别的畴人。什么是畴人,我也没有追问,当时被一颗飞星吸引。有一奇星忽然横过夜空,非常明亮,倏忽隐没,煞是神异。
我父亲即说,那是一颗飞星,见首不见尾,若是见尾,则是便星;若是星尾如扫帚,即是长星。我随父亲看星多年,见过各种会飞的星,又见过特别明亮的星,因此也算是同龄中的知星人吧。星斗满天,我认得太白星、客星等。客星很有趣,在天空上忽然来了忽然又不见了,像自由行客。我家不时也有长辈来客,偶然问我星星的事,我也能略说一二。一二罢了。有一日,父亲嘱我画一星图,让他指正。这成为我除读四书、习字、绘画之外的日课。每日午后,我在小书房内的案桌上展开一幅宣纸,两侧以镇尺压实,就用小号毛笔绘画。画的都是我所知道的天上星辰,不是画出星光就算,而是要画出星名、含义。原来星空的世界如同人间世界,既有帝王将相,也有河船桥路。天上的星就是地上的人,一颗星是一人,或一物。一般人的星不为人所见,因为太卑微了,大家视而不见,只有帝王将相的星象,才特别光亮,例如皇帝,乃是紫微星,那星恒久发光发热,若是暗晦起来,必定大事不妙。
啊,我于是想,上天原来也知错能改。
父亲教我看星,说古人把天上的星宿划分为三大区,那是三垣:紫微垣、太微垣、天市垣。垣,就是城墙。再加上四象:东方苍龙、北方玄武、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四方又各领七星,合共二十八宿。我画的星图就从紫微开始,这是皇帝的居所。地上的皇帝住在紫禁城内,天上的皇帝住在紫微垣内。我先画垣。这垣是左右各一,左方一幅名紫微左垣,右方一幅则为紫微右垣。两垣并不相连。我所画的天垣,一左一右,犹如两片豆荚,微微弯曲,面对面,距离不太远,中空无物。两片豆荚,既不相连就有裂口,一南一北,犹如门口。南方门口有些星,父亲说那星名天床,我就在那处画了一张床,并在旁侧写下“天床”二字。至于北面的门口,父亲说有两组星,一是罗伞,一是杆。我即画了一把大伞、一杆伞柄,并写下“罗伞”和“杆”在旁。那日的星图就完成了。父亲说,我画的只是简单的图像,便于认识星象,正确的星图除了图像,还得把星的数目一颗一颗画出来,大小光暗,也得点明,可用朱砂点染。如今画得简单,只需我认星的名称、位置、象形。每日不需多绘,但必须辨识和牢记。
第一日,我虽只画了两垣和三件事物,但我记住了,两垣是两幅南北走向的墙,墙里是天上皇帝的紫微宫。
03
我的小书房其实算不得书房,而是大厅堂里的小角落。这地方,我觉得很有趣,大概是父亲特别建造的厅堂,和别的厅堂并不相连。它是一座两面厅,看来是房屋,有四面墙,可是有边门。也就是南面有一扇门,北面又有一扇门。如果从这扇门进去,可以从另外一扇门出来。如果从那一边的门进入,也可以从这边的门出来。就像父亲说的什么八阵图似的。也不知道父亲是怎么想出来的。娘亲说,有什么奇怪的,江南的园林,譬如拙政园里的远香堂,就有四面厅哩。
我家的两面厅,也在园子里。这个房子里面有一道隔扇,是一列板门合成的,板块的底下是木板,上层是纱绣,罩在棂格子的木架外面,虽是板槅,却有透孔,因为花绣和棂条很密,看不清楚隔邻有什么人,只听得见声响。父亲有很多朋友,常常有书友到家来喝茶,看书看画,都坐在朝南那面的厅堂里,而我则在另一边的后房写字,或者,到娘亲的堂屋里嬉耍。平日,我也在两面厅的后厅读书,那里有许多书架,摆满了书。我也可以自己拿书看。我六岁时读过《三字经》《小学集解》《幼学琼林》,八岁开始读四书、《孝经》,尽管许多地方并不明白。我不明白的地方还有许多哩。此外,每天都要习字,爷爷收集了许多字帖,父亲要我同时留神那些名家的字帖,像看书那样,不过像看图画。我最喜欢张旭龙飞凤舞的草书,老实说,我其实也看不明白,我看着那些线条游走,就像天上翻卷的浮云。但父亲要我临楷书,是褚遂良的,或者欧阳询的,一笔一画,要整齐中正,还得心平气和。父亲说,欧阳询的样子很丑,他的书法却很美;我们再也看不到他的样子了,却仍然可以看到他的书法。
我的父母本来住在江宁的鸡鸣山,鸡鸣山又叫鸡笼山。父亲在鸡鸣山的观星台做事,他说都是闲工夫,好处是可以多读喜欢的书。当年他还是个小伙子。我想,那地方的清晨,一定听得到鸡啼,此起彼落,催父亲上班。父亲告诉我,元代在大都建立司天台,大都城址就位于今天的北京。司天台由王恂和郭守敬带领,这个郭守敬可是大大有名,他制作了浑仪、简仪、圭表、浑象等观测天象的仪器。那他就是通灵的神巫吗?父亲大力地摇头,只是说神巫不用观测的仪器。
明初,司天台被战火破坏了,观测仪器全部运往江宁的鸡鸣山观星台。明成祖迁都北京,但天文仪器仍然留在南京,继续观测天文。在北京另外设立“行在钦天监”,只能依靠肉眼观测。这,父亲忽然说,就是神巫的做法了。当年的南京现在叫江宁。后来北京终于仿制了南京的观测仪器。南京的观星台作用于是大不如前,在那里供职的人差不多就像旧仪器,可说投闲弃置。钦天监本来是官名,以前叫司天监,掌管观察天文、推算历书、授时等工作,也泛称政府掌管天文、研究历法的部门。
父亲说了一件他牢牢记着的事,原来元代时郭守敬建造的观测仪器,到了明代,由于没有留下好好的说明,加上明太祖下旨不许民间私自学习天文,于是逐渐再没有人懂得运用,后来甚至有些仪器倒置了也不知晓,直到有一位西洋传教士到来,重新调教好,才可以使用。那个西洋人,名叫汤若望。
父亲觉得这方面要学的还有许多许多,改朝换代了,南京改称江宁,于是和几位朋友从山上下来,迁来北京,北京的天象台听说来了一些西洋人。那时他们还是小伙子,满以为可以到天象台找到工作,但没有。父亲索性不再出外工作,之前变卖了爷爷留下的一些瘦田,家族的书坊解散后也分得微薄的股份,还有外祖父曾留给母亲很体面的嫁妆,将就一点,也就不需怎样工作了。他说反正没有门路,又不愿意考科举,因为从明到清,考的是八股文。八股文想来不会是好东西,它的内容和形式都有严格的限制,还规定字数。他不考,也不要我考。
我在北京出生,在家说的是南京话。当年明成祖迁都,大批汉人随着从南京移居到北京来,也带来了南京话。清朝初期因大量使用汉员,许多事物满人又前所未闻,所以南京话仍然通行。到了今上康熙皇帝时代,北京官话才逐渐流行起来。我自小父亲也教我北京话。所以北京话我也会说,不过和家人、朋友一起时,我们仍然说南京话。
我曾问父亲,会回到鸡鸣山,看看故居吗?我知道鸡鸣山,早年是很有名的,那里有一座鸡鸣古寺,山南有国子监。国子监的建筑宏伟,学员众多,一度收生接近一万人。特别的地方是,也接收外国的留学生,例如来自日本、高丽、暹罗的。父亲曾在国子监读书,但想到官场黑暗,说不宜漏夜赶科场,而兴趣又在天文,所以后来转到观星台去。
鸡鸣山的山麓曾经有许多文人雅士聚居。祖父的一位胡姓好友,在前朝最后一年,刊刻了有名的《十竹斋笺谱》,很受欢迎,采用了前所未有的饾版、拱花等技术。我问父亲什么是饾版、拱花。他解释:饾版是印刻时把一幅彩色的画,每一种颜色,分别逐一雕刻版子,然后套合起来刻印;每种颜色,丝毫不能套偏,图画复杂的话,可能会用到几十块版子。这种分色刻版,真是杂凑“饾饤”的工夫,所以称为“饾版”。拱花是把凹凸的硬板嵌合,令纸面局部拱起,产生浮雕的效果。父亲还留下了一套爷爷的《十竹斋笺谱》,他欣赏那种用心、准确的技术,技术到了这地步,就是艺术。胡氏两代跟容儿一家也是好友,两家人同样是医大夫。
我想鸡鸣山一定很好看,是一座灵山。
有什么好看的,都没有了。
不是可以看星吗?
哪里看星不是一样的?反而是星看人,到底不同。
当我问他以前的事,他瞪着我,忽然严肃起来,也没答话,变成了另一个父亲了。因此我知道,有些东西是不能问的,又或者问得不对时候。他的几个老友也没有在钦天监找到工作,一位叔叔转做茶商,接浙江来的茶叶做小买卖;另一位,他最要好的,容儿的父亲,做了老本行,开了间药店。
好好读书,父亲想了好一会儿说。
哪里看星不是一样的?反而是星看人,到底不同。
我读书的书桌就是后厅中其中一张,另一张则是我画画用,桌上摊开我正在画的星图,每天画几个星象在纸上。我已经画了天床和华盖,后来画了五帝和五帝内座。内座就是座椅,五帝可不是五个皇帝,而是五颗星。原来,五帝内座这个星象,或叫星官,是由五颗星合成的,每一颗星是一个座位。皇帝一年五季要轮番坐遍每一个座位,春季坐春位,夏季坐夏位,之后是季夏、秋、冬等。
什么是季夏?为什么一年变了五季?容儿问。
我怎么知道呀?
04
我画另外两颗星时最高兴,因为我对北斗星最熟悉,纳凉的时候,我很快就看到它们,一共是七颗星,像个斗的模样,还有一个手柄。斗是四颗星,柄是三颗。斗的口面对皇帝星,原来,北斗星是皇帝的车子,难怪它停在紫微右垣的外面,天床下面的位置,皇帝从天床那里出来就可以坐北斗车出巡了。至于那天画的另一个星叫勾陈,我又不明白是什么事物了,也画不出来,只好画了一圈大黑墨。父亲看着笑了,却说,记着这颗全天空最亮的星,名叫勾陈一,不会走到别的地方去,也永远那么亮。
轮到交通工具了,因为皇帝天天要出巡,又要到皇宫去办事。皇帝的车子,共有三辆,一辆是位于垣南的北斗,另有两辆,位于垣北,都由四匹千里马驾驰,而且御夫是最能干的王良和造父,马车疾驰时,如同飞行。有时,皇帝出外不乘车,乘船,因为天上有天河。船都泊在北方,一艘名天船,位于紫微右垣的北门外。另一船远些,在紫微左垣外,泊在渡口,那泊船的岸边叫天津。马车附近,有一座马棚,名叫天厩,是皇帝的马厩。
我总是一面画,一面听父亲和他的书友说话,平日谈的都是些诗文。说说笑笑,喝喝茶。不过,有时声音压得很低,有时又说得很大声,把我吓一跳。不过,近日说的竟是什么西洋人、教堂和监牢。娘亲来看过我画的图,说我画得不错。她告诉我,图中还应该有不少事物,但我年纪还小,将来再画上去好了。我问还有什么呀。她说,譬如那两垣,右垣内躲着七个人呢,左垣内则有八人,就像打开豆荚见到荚内的豆颗。当然,垣内的每一个人就是每一颗星,他们都是皇帝四周的官员。那我明白了,天床、华盖、天柱也是一些星合起来的模样,不过,我要把星和星之间的线连起来才行。母亲说,是嘛,并不是人人都能想得出那些线哩。
画北斗星的时候,我以为已经把紫微垣画好了,因为北斗已是在紫微左垣和紫微垣的城墙外。不过,墙外除了北斗,还有很多星。一连几天,我就画那些围着紫微垣内的一些星。先是画厨房。皇帝、皇后和太子都要吃饭,厨房应该在垣墙内才是。可是紫垣内实在太挤了,厨房不得不搬到城外。厨房一共有两个,一个是内厨,就在北斗的斗口上面,这是为后宫而设的厨房;另外一个叫天厨,专供食物给皇帝,并且宴会文武百官。
我的紫微垣画完,父亲看过后说,不要忘记还有两处,就是天上的监狱;于是画了座天牢,它位于北斗的底下,父亲说,这一座是关困贵族高官的大牢。另一座囚困的是一般平民,位于紫微左垣之下西方的地方。几颗星图织成一个罗网的样子,名叫贯索。我终于把紫微垣画好了。娘亲说,天上三垣,我不过只画了一垣,还有两个呢。
难不难画?容儿问。
容儿比我小一岁,随他父亲到来,大人聊天,他就走到我的书房,看我的绘画。我说一半一半。画床、座位、船都不难,画车和马难些,画人很难。画北斗最容易,最难画的是勾陈和贯索,只能写字算数。在小弟面前,我好像很有学问似的。
05
每天下午,我都在双面厅的后厅画星宿,画完了紫微垣,还有两个垣,一个叫太微垣,同样是由两道墙包围起来。左边的是太微左垣,右边的是太微右垣,里面有很多人,都是皇帝的官员。皇帝每天要到这里来听政,所以这里也有一张五帝座。人很难画,因为样貌和衣服都不一样,我只好写下他们的官名,即三公、九卿和五诸侯。有三件事物我觉得很特别,它们都在墙外,一个叫灵台,是座高台,灵台我知道是看星宿的台,在太微右垣外。它的旁边是一座明堂,恰在左、右两垣南面的门口。明堂是祭祀、庆典用的。太微左垣北面的门外,有一个周代的鼎,这鼎也够神奇,是历代皇帝都要抢夺的宝贝,好像抢得了,就抢得了天下。整个太微垣位于北斗星底下。
第三个垣叫天市垣,这是老百姓住的地方了。不过,皇帝又有一张帝座在垣里,他来看看百姓过得怎样,听听百姓的想法,最重要的是不能有百姓生事。天市垣又是由左垣和右垣包围起来,特别的事物不多,我画了几层楼高的市楼和一辆叫车肆的木头车,都画在两垣的南门口。整个天市垣就在贯索底下的位置。我站起来看看三个垣,像什么呢?
一个“品”字,容儿说了。
画天市垣的时候,说实话,我不很专心,因为前厅有很多人交谈,说话的声音时大时小。他们说,京城里的确多了很多西洋人,高大,头发都剪得很短,不梳辫子,却卷起来。他们又长胡子,眼睛有的黄色,有的蓝色,像猫子。有人见过他们跳到河里游泳,半身赤条条上岸,全身都是毛,像猴子。又有一个说,西洋人在朝廷里当官啦,从外国带来不少珍奇玩意儿,讨得皇太后、皇帝和许多官员的欢心。又有一个说,西洋人并不简单,他们有许多本领,会做数学,会观星象,会计算日食月食,懂历法,都是有用的知识。又有人说,西洋人来我国传教,教我们信耶稣,不要拜邪魔,不要娶妾。他们不是在王府街那边建了西洋教堂,花园里有大幅的图画?我们都该去看看,听说观众人山人海。
一次我正独个儿在双面厅里画星图,忽然整个厅堂都摇动起来,我坐也坐不稳,不知为何好像被人一推,推到墙上,再跌倒在地上,四周哗啦哗啦响个不停。我坐在墙脚,看见厅内的花瓶都掉在地上,裂开,遍地碎片。这时,娘亲和福伯赶来,把我扶起,带我离开。我见到我画的星图还在案上,就拍掉纸上的沙石,匆匆卷起带走。不久,父亲也回家了,说外面有很多房子倒塌,很多人受伤,甚至死亡。原来那是地震。我们都吓坏了,我只想着容儿一家可好。福伯说,上天发怒,不久就有大灾难啰。父亲听了,摇摇头,沉吟说:应该有预兆,为什么没有?
我家幸好损失不大,打破了不少瓷器花瓶,书架上的书只是散落地上,封面花斑斑,内页仍完好。地震后好一阵子,我没有再画星图。双面厅要修理整顿,也没有书友来访。那段时日,我们也没有看星。我也没有做特别的事,仍学《论语》、《大学》和《中庸》。但若干年前一次地震,连续三天,令许多人家破人亡,连王府街的天主堂也倒塌了,那次地震却挽救了一个人,一个特别的西洋人,是钦天监监正汤若望。
康熙七年六月十七日戌刻(约公元 1668 年 7 月 25 日 20 时),地大震。余适客稷下,方与表兄李笃之对烛饮。忽闻有声如雷,自东南来,向西北去。众骇异,不解其故。俄而几案摆簸,酒杯倾覆;屋梁椽柱,错折有声。相顾失色。久之,方知地震,各疾趋出。见楼阁房舍,仆而复起;墙倾屋塌之声,与儿啼女号,喧如鼎沸。
人眩晕不能立,坐地上,随地转侧。河水倾泼丈余,鸡鸣犬吠满城中。逾一时许,始稍定。视街上,则男女裸聚,竞相告语,并忘其未衣也。后闻某处井倾仄,不可汲;某家楼台南北易向;栖霞山裂;沂水陷穴,广数亩。此真非常之奇变也。
——蒲松龄(1640—1715)《聊斋志异·地震》
康熙十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巳时地震,京城倒房一万二千七百九十三间,坏房一万八千二十八间,死人民四百八十五名。
——刘献廷(1648—1695)《广阳杂记·卷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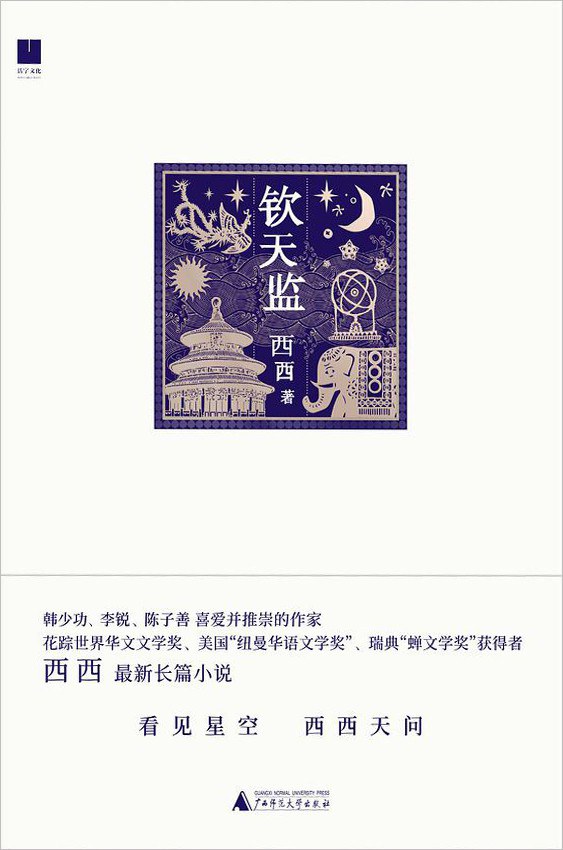
本文为节选,摘自《钦天监》
西西 著
活字文化|世界·观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1 年 1 月
题图来自 zhang kaiyv on Unsp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