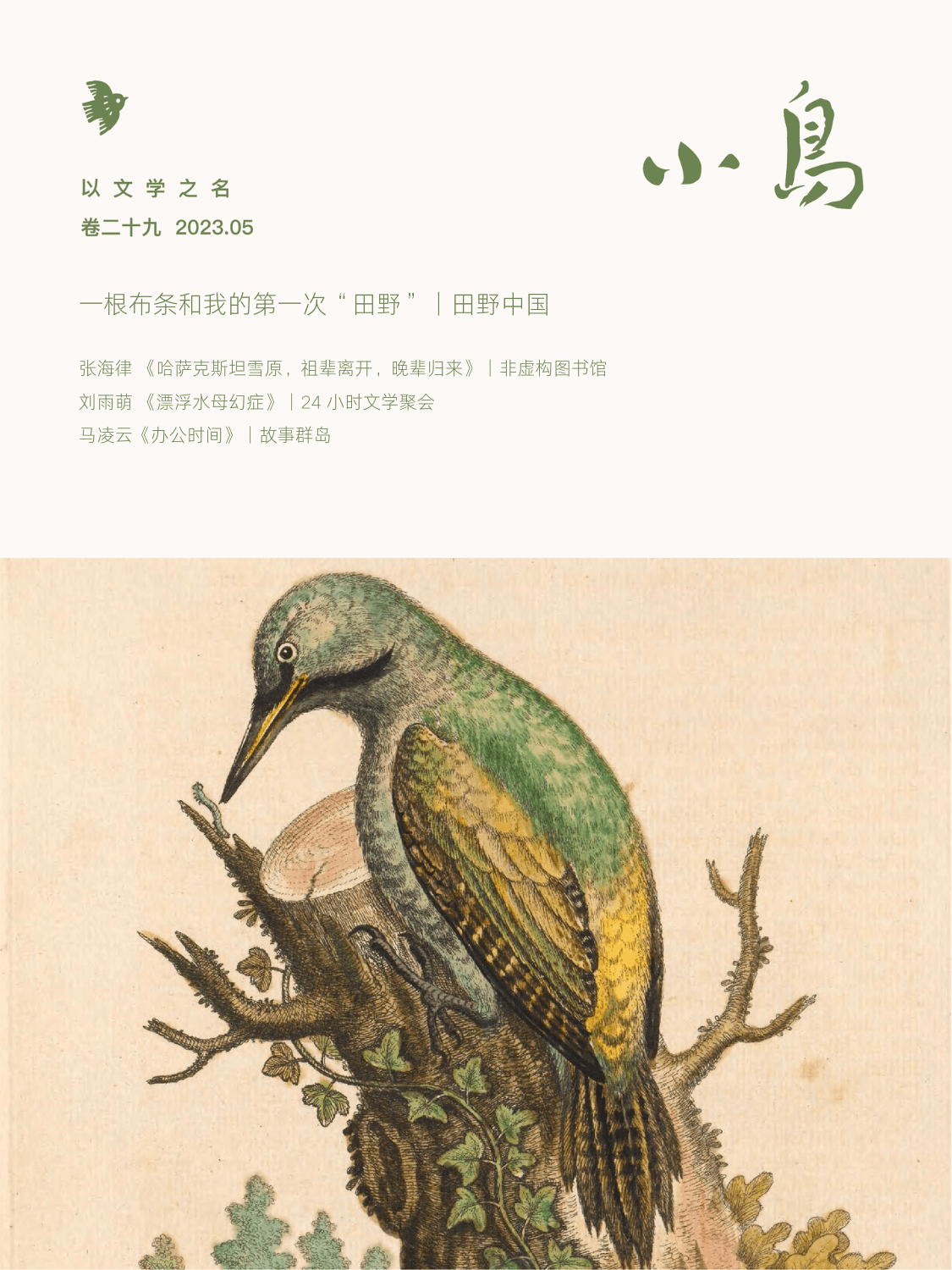李汉超家的墙上挂着两幅地图,一幅是世界地图,另一幅是中国地图。很多人家里都有这个摆设,对于墙上没有太多花样的时代来说,这东西在装饰意义上聊胜于无。李汉超对动画片没有太多热爱,跟大人一起看电视,听到什么新闻了,他会到地图上去找。利比亚,卡扎菲,战争,顺着地中海撒哈拉沙漠,踅摸一圈,找到利比亚,似懂非懂。他的家人反正看出来了,他在关心卡扎菲。十三四岁,作为一个小粉红,他说他得站卡扎菲。偶尔会琢磨一下,这个大方脸汉子关我什么事。没想通透。现在也一样,他偶尔会在自己的公众号上写美国政治,拜登关你什么事?他说现在也想不大清。
但这是李汉超生活日常。
听人聊天,说《货币战争》可有名了,拿过来看看。一看,“我操,罗斯菲尔德家族这么牛逼。”连看了三本,不怎么跟人讨论,自己看自己消化。没人讨论的原因是中学典型理科班,小粉红也好,自由派也好,没有人在意。同学们也不看书,李汉超说。《货币战争》让他觉得看懂了世界格局。墙上的地图也活了。现在,他说那时看的都是“黑历史”类型的书。后来才开始看正常书。
他说的正常书,指的是经典。经济学,看曼昆的,政治学看基辛格的。“《大外交》,on China 这种。”那时,李汉超已经上高中。早上六点多到校,晚上九点钟放学,回家没时间看书,就只能在学校看。他同学也发现这个人好奇怪啊,看些奇怪的书——“就是没用的书,就这个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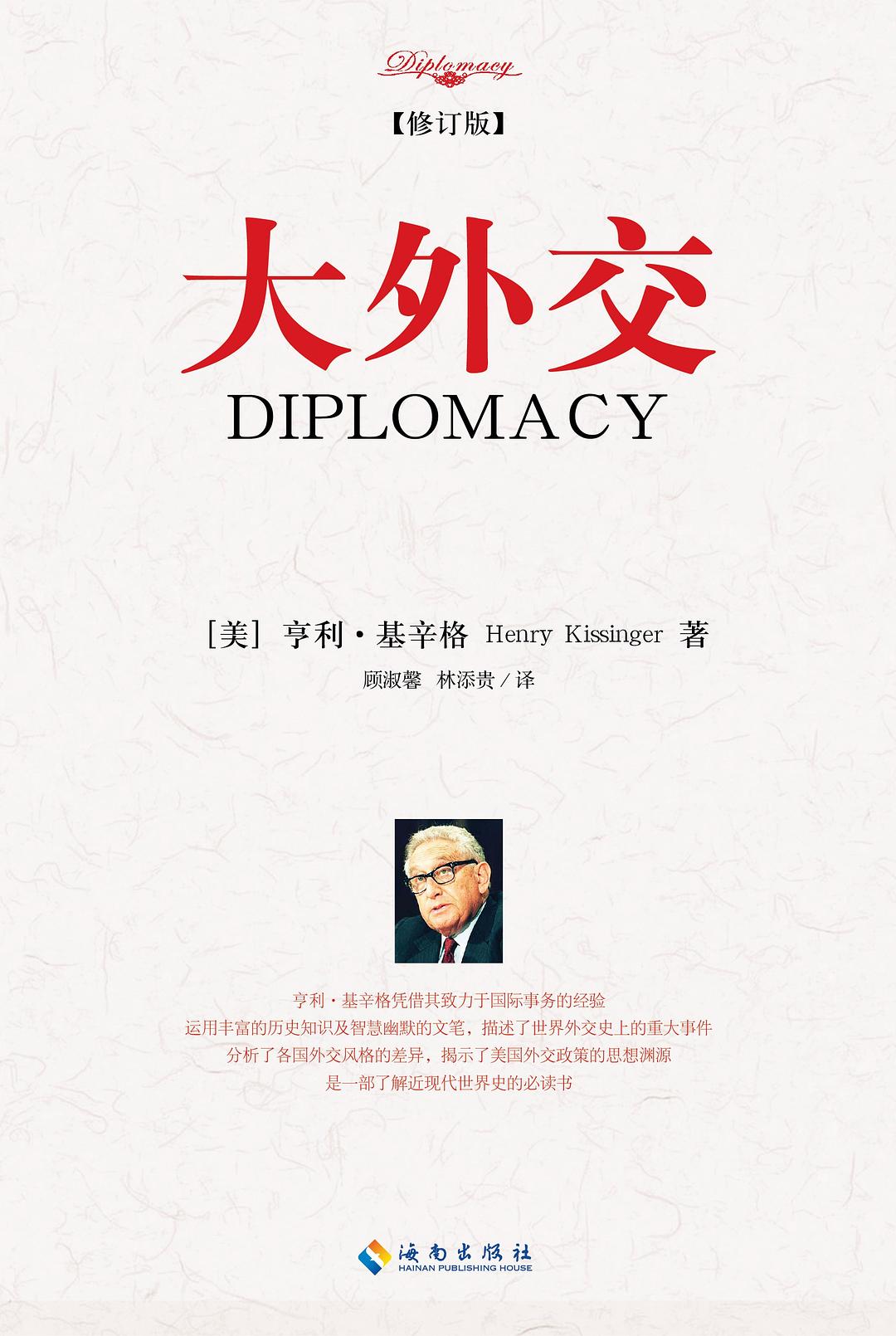
- 《大外交》
他学习好,年级大排名总能排十来名的样子,所以老师也不怎么管他的兴趣。“我们老师也有想交流的,当时我可能太小,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看出来的。英语老师比较喜欢我。这是肯定的。看我在看书,平时聊天也比较多。我们班主任,某一任班主任,数学老师,somehow 也挺喜欢跟我聊天的。会有这样的反应。数学老师在你具体读什么上帮不了你太多。”所以,也没有什么人在读什么书或者建立一个知识结构上有什么特别的帮助。“现实接触到的人,基本上是不存在的。”
所以现在他会说,小时候知识结构有欠缺。喜欢国际关系,看基辛格如同看爽文,一提国际关系,马约,嚯,世界这个大棋盘就摆在那儿了。如果非要说谁给了他一点支持,那只能是他爸爸,而他爸爸所做的支持实际上就是墙上那幅本来可有可无的世界地图。
“一切都来源于那个世界地图?”
“你要这么说也对,倒是能对上。那是 2000 年啊,很多人家里都这样。这边挂个世界地图,那边挂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
2000 年,李汉超两岁,他应该还没记事,确切地说,从他出生,家里就奠定了他未来对世界认识的格局。
2012 年 9 月,具体是哪天李汉超不记得了。那天下午,街上人群逐渐增多,喊口号,“钓鱼岛是中国的!”
他兴奋啊。《中国青年报》当年的报道说,中国有二十几个城市发生了游行示威。“日方近来在钓鱼岛问题上一系列错误的态度和行为,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报道称抵制日货虽然情绪化,但是一种“鲜明的表态”,“以表明中国人不容侵犯的尊严”。
14 岁的李汉超,走出家门,看大世界。他只是看。队伍对他来说有点过于隆重。他很兴奋。游行只是听说过的事,没想到会在身边发生,参与游行的人也都克制而礼貌,没有人砸车,也没有什么很直接的目标让游行者可以投掷鸡蛋或者砖头,有惊无险,李汉超跟着走了一路。
在相隔八年之后,我们在北京一家星巴克聊天。他捻着他有点油的头发,头发掉下来,他从桌上把这些散落的头发归置到一块,继续捻。事后总结:四分看热闹,六分表达支持。回忆中最大的感受:开心。
他说这时他政治意识清晰。钓鱼岛就是我们的啊。
李汉超已经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毕业,聊天的那会儿,他应该在伦敦政经念 PPE,就是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新冠疫情打乱了他的节奏。他在北京上网课。现在,他可以从容不迫地回头观照自己的政治光谱。
“小粉红?你说具体什么东西影响了你?这个没办法讲影响。一开始,人生长在这儿,天然就是小粉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