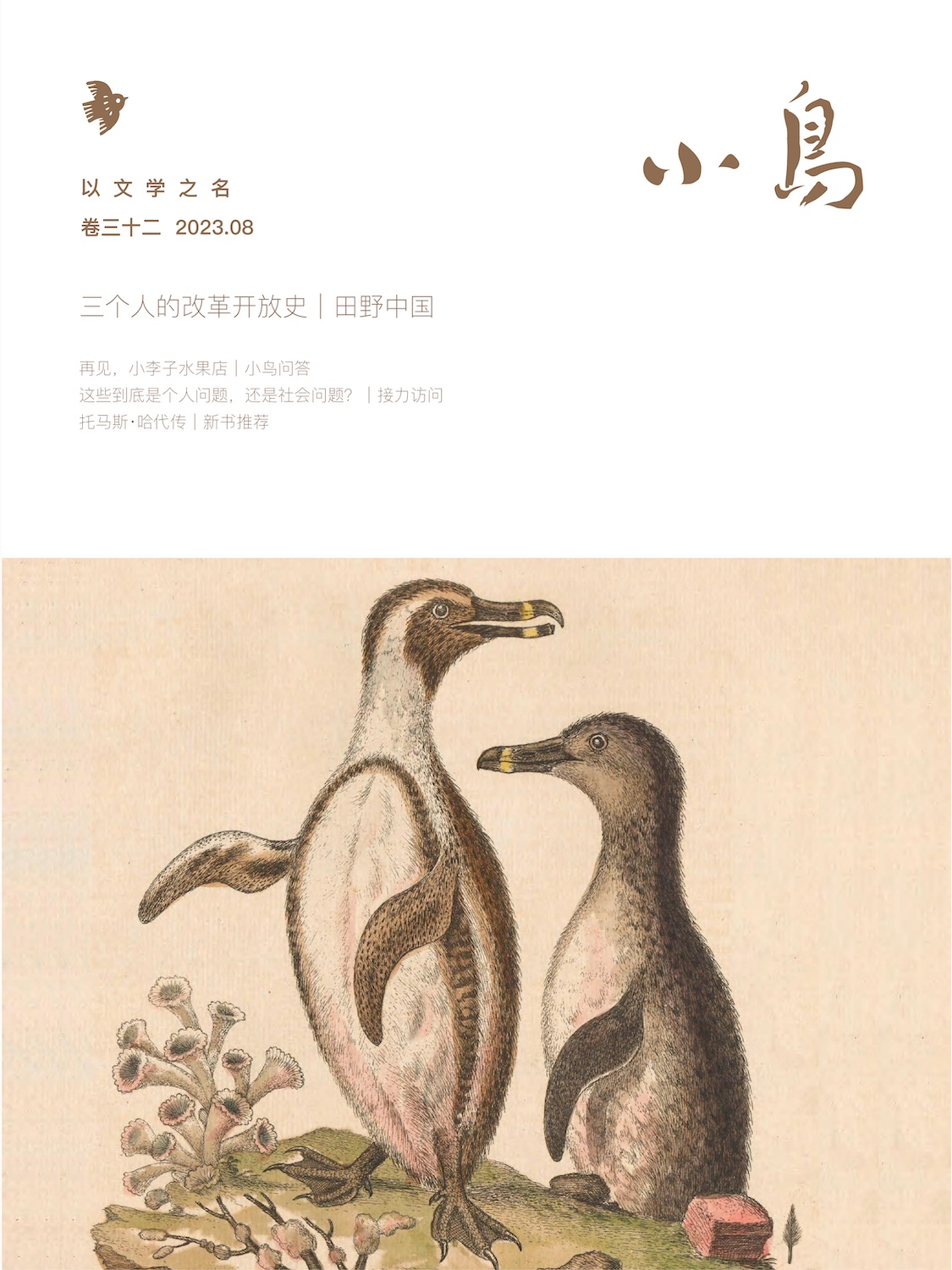2000 年,温女士花 15 万接手上海浦东一家酒吧。酒吧原来的主人是一位美容师,温女士是她的客户,同时也是酒吧的客人。美容师不会喝酒,也不喜欢应酬,就跟温女士商量,要不酒吧兑给你?温女士想了想,觉得也不错,就成了酒吧的老板娘。
那时浦东荒凉,除了陆家嘴,没什么人,下班之后街上是空的。酒吧那一带不太一样,那里有一片涉外公寓,涉外公寓里住着不少磁悬浮的德国专家,上海当时正在修一条从龙阳路地铁站到浦东机场的磁悬浮试验线,用的是德国人的技术,德国人爱喝啤酒,支撑了温女士的生意。
德国人有一位中国同事,酒喝得好,会说话逗人开心,举止得体,年少多金,前店主还在位的时候,曾经指点给温女士,如今温女士接手酒吧,长袖善舞,与重点老客人互动增加,更加熟络,时间久了,走在一起,结婚了。温女士漂泊多年,没想到这个看来不是太上道的生意居然让她找到了一个优质男人,父母也特别喜欢,他们是知识分子,总担心女儿的江湖气不知道找回来一个什么样的男人,看到这留学背景的知识精英,正是天上掉下来的喜悦。
那个酒吧,见证了爱情,见证了儿子出生,一直到六岁,儿子要上学了,温女士忙活不过来了,最终把酒吧关掉。开了九年。
在另一个同样来自温女士的自嘲版本中,温女士会说酒吧是被老板娘喝垮的。她江湖气,豪爽,一喝多就不让人家埋单,她喝多了看着跟正常人一样,客人也没有太多心理负担。她爱喝酒,年轻时喝多少都不会断片,现在岁数大了,会断片,断得越来越多,但她似乎也没有想节制一下的愿望。“开心了就喝呗,没有量,也不会特别控制,高兴了想咋来就咋来。”
我们与温女士约在杨浦五角场一间茶餐厅。温女士送儿子补课,“他自己来也行,但晃晃悠悠坐公交车得一个半点,我开车半个小时就到了,”可能她总借这接送的机会多点和青春期的儿子共处时间,但她的说法是:“我没什么事,正好跟你们聊天。”很无缝连接的样子。
温女士,简单点说是这样的传奇:1980 年代她是一个洛阳问题少女,1990 年代的时候她已经成为香港人,2000 年代,她在上海经营一个酒吧,2010 年代之后,她做投资,一级市场二级市场都会做一点,大多数时候是个母亲,在儿子的学校做家委会义工委员会的主管。
她自己最喜欢的那部分传奇还是开酒吧的几年。茶餐厅里讲她喜欢坐在那里看乐队演出,讲她与陌生的或者相熟的客人聊天,讲初见她先生时他们风华正茂,讲浦东到处乱糟糟,讲房价,前一年周围还是荒草,转眼房价就涨了一百万,讲每一个人都有一点心事,“越是陌生人可能越容易说,安全吧。每个人都有一点心事。”她说她可以跟人随便聊上几句,“我就是居委会大妈。”然后哈哈大笑,她会制造点文艺的气氛,然后再用江湖风打乱。
我们起初认识她的儿子,儿子正准备上高三,我们觉得不应该破坏他的专注、影响他的学业,他就推荐了他的妈妈与我们聊天,由此我们认识了温女士,然后我们发现她的家族故事,特别是跟财富有关的那一部分,我们或者可以视为某种类型家庭的一个标本。
这种家庭一般是这样的:家中有一位强势的成员,掌握一定资源,这资源可能是权力也可能是钱,他会成为这个家庭中一言九鼎的人物,强势和中心地位是自然而然完成的,如果他的财富或者可控的资源更强大,有能力和足够的宽度和深度容纳更多的生意,那么家中的其它成员会组成一个松散我们姑且称之为家庭经济组织。它跟互助型的或互补型的那些家庭共同体不一样,它就是一种生意集合。
比如,我们在郭星的故事里看到的,他的祖辈中,四爷爷率先做房地产,并获得成功,建立起人脉关系,煤老板、同档次的富人、政府官员、其他掌握一些稀缺资源的人等等,四爷爷渐渐在家中成为中心,他的三哥、也就是郭星的爷爷会成为他的合伙人,也能获得丰厚回报,而利用四爷爷建立的资源,他们家会分到煤老板的车队保险业务。郭星的爸爸在因为赌博入狱之后这个生意随之丢掉,说明它是一个稀缺资源。
还有一种成为家中核心是因为得天独厚的视野,比如海外背景——特别是在海外资源稀缺的时候,它可能意味着:致富机会的捕捉能力更超前,不同市场的套利空间,更不要说信息处理能力。前面提到的林先生说温州人早年间走南闯北肯创业吃苦背后的优势,大体上也算得视野上的优势:信息不对称本身产生的优势。当他们家族中某一位赚钱能力超出普通人数倍时,他们会吸引更多的钱,这一般可以视为温州民间金融的力量;如果他的生意更大,这个人的生意就会成为资源中心——权力或者钱的支配者所建立的这种中心,类似于郭星,或者我们马上要说到温女士家中的局面。
在温女士家中扮演这个角色的是她的父亲。关于温女士的财富人生,某种程度上要从她的父辈的人生开始讲起,由此我们才能看到一条相对还算清晰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