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一周周地过去,象群也开始渐渐平静。这样,我们在喂食的时候就能靠近围栏,大象不再愤怒地冲过来了。当然,我们还能多补充些急需的睡眠。
荒野中艰苦的生活对灵魂来说不失为一种拯救。古老的本能被唤醒了,遗忘的技能回归了,意识变得更加敏锐,生活的节奏也慢慢变得更加丰富。
在荒野里生活,往往今天在这里,明天便去他处。我和戴维不想这样做丛林中的过客,我们必须努力调整自己,适应这里的一切,这样才能被这个原始大地的永住民接受。我们要像鱼儿漫游在水里一样,实现和周围环境的无缝对接。
最初,众多野生动物把我们视为不受欢迎的殖民入侵者。它们想知道我们是谁,到它们的地盘来干什么。无论走到哪儿,总有几百双眼睛盯着我们。我敏感地觉得自己时刻处于监控之下。无论何时,只要一抬头,总能看见不远处有猫鼬、疣猪,或者草原雕窥视着我。我们做过的事情一丝一毫都逃不过它们的眼睛。
很快,我们也成了原野中的生灵。大型动物渐渐习惯了我们的存在,也知道我们不会给它们造成什么伤害,开始在我们周围自由自在地漫步了。当地的公黑斑羚和它的母黑斑羚们,通常都像小马群一样活泼可爱。它们在三十步开外的地方吃草,把我们看成是自然景观的一部分。斑马和羚羊经常在我们身边经过,捻角羚和白斑羚在附近啃食,完全是一幅轻松自在的景象。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非常受欢迎。一群狒狒在一头装腔作势的公狒狒的带领下,每天悠闲地溜达到河边,顺便再洗个澡。见我们不小心闯入了它们的领地,而且还在那里扎营驻寨,那头可怕的公狒狒简直怒不可遏。它端坐在一棵纳塔尔桃花芯木树的树顶上,龇着匕首形的黄色大牙,“呼呼哈哈”地怒吼着,声音响彻山谷,它用来宣告土地所有权的“啵啵”声也回荡在河床两岸。在它眼里,我们一直以来都是入侵者。
时间已到春末,各种形状、各种大小的鸟儿已经换上了各种非洲色彩的羽毛。它们叽喳啁鸣,自顾自地吟唱着生命的故事。包括黑曼巴蛇在内的各种蛇类忙着找阴凉地儿,好躲避太阳的炙烤。我最喜欢的是一条漂亮的岩蟒,它住在附近溪谷旁的一堆岩石中。它还是一条小蟒,不足 5 英尺长。但是,看到它橄榄色与褐色相间的身子在地上像潺潺流水般滑过,你一定会惊叹不已的。
每当这条肌肉弹性惊人的蟒蛇从身边爬过,我都要紧紧地抓住马克斯脖子上的项圈。尽管它早就知道不能追逐大部分野生动物,但对蛇,它还是很有想法的。稍一疏忽,它就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向这条蟒蛇。
附近还有一只 1 英寸大小的达尔文树皮蛛,它把路虎车的双向无线电天线当成了巨大的脚手架。尽管身材娇小,可它绝对精力充沛。每天晚上,它都把接收天线当成支撑杆,然后织出一张大大的网。到了早晨,它就开始狼吞虎咽地享用昨晚的战利品了,而且不浪费粘在轻飘飘蛛丝上的每一毫克的蛋白质。当夜色降临的时候,它再次登台开始自己的纺织表演。我们给它起名“威尔玛”,它的 3 码见宽的网就是一个工程奇观。这样一张令人生畏的超黏性大网能够用“丝钢”捕住任何飞虫,比如 4 英寸长的长角甲虫。随后,威尔玛有条不紊地把虫子体内的汁液吸得一干二净。
有时,我们需要到博马的另一端去巡视。每当车辆一打火,发动机的震颤就把威尔玛吓坏了,它只能悬在刚刚织好的网上了。最终,我们不忍伤它的心,只好步行过去。
夜幕降临,活跃在阳光下的动物们都找安全的场所睡觉去了。大地看起来也空旷了许多,可是这样的情形持续不了多久。很快,在非洲闪耀的群星下,夜行动物重新占领了这片土地。疣猪给牙齿又细又小的丛林野猪让出位置。茶色战雕也休息去了,取而代之,巨鹰鸮粉墨登场。巨鹰鸮静悄悄地展开翅膀,在夜色中搜寻猎物。一看到圆滚滚、胖乎乎的丛林鼠,它马上俯冲下来。这种丛林鼠行动迟缓,易受攻击,要不是有着出色的繁殖能力,估计早就灭绝了。红脖子夜莺长着开合式的嘴巴,这完全像是为了在飞行中捕捉昆虫而量身定制的。它们汲取着大地渐渐退去的蒸腾热气,然后翱翔到空中。成千上万的蝙蝠在空中急速飞行。而夜猴是最可爱的动物,小身材,大眼睛,让人想把它抱在怀里好好爱抚一番。有时,会听到它们从树顶那里传来的交配时发出的尖叫声。
土狼,作为声名狼藉的野蛮食腐动物,在非洲经常被污蔑、被误解,但我还是很喜欢土狼。它们潜伏在黑暗的小路上寻找晚餐,喋喋不休的“嗷嗷”叫声是土狼在界定自己的领地。有时,第二天醒来,我们会发现和狗脚印类似的巨大足迹,这说明它们来瞧过我们了。我们有时会间歇地使用聚光灯追踪这个沸腾的剧院,可如果长时间打开聚光灯就会引来一群群的虫子。在丛林中,亮灯是很不明智的做法,因为这样会引来昆虫,昆虫引来青蛙,青蛙再引来蛇。我们唯一的连续照明手段只有营火。
一天早晨醒来,我在路虎车旁发现了猎豹的粪便。这只当地的公豹把我们睡觉的地方划成了它的领地,它的粪便传递出一种强硬的猫科动物信息——这是它的地盘儿。
住在这样接地气的地方,可以这么讲,我有充足的时间去研究这个象群。另外,它们独特的小怪癖也让我着迷不已。娜娜,个头巨大,有绝对权威,认真履行母头象的职责。它就像一个瞎操心的家庭主妇一样,最大化地利用了博马里的每一寸土地。它划分出来最佳的乘凉地点,最佳的遮风地点。更为神奇的是,它还精确到分钟,掌握了进餐的时间。它还准确地知道我们什么时候给水坑和泥塘添水。
弗朗姬,把自己封为象群的保护人。它最开心的事情是抛下其他大象,全速从我们身边冲过,高高地扬起头,凶狠地瞪着眼睛。而所做的这些,无非就是闹着玩。
曼德拉,娜娜的小儿子,是个天生的小丑,它滑稽的动作总是让我们忍俊不禁。它生命中考虑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让它橡胶般有弹性的鼻子听话,就好像这条鼻子是有生命的独立个体一样。它经常虚张声势,假装冲向我们,当然这只是它妈妈在身边的时候才发生的事情。
马布拉和马如拉,分别是弗朗姬 13 岁的儿子和 11 岁的女儿。它们总是既安静又听话,很少离开妈妈的身边。
南迪,娜娜的女儿,已经十多岁了,完全是它妈妈的翻版。它个性更加独立,经常独自漫步、探索。
还有努姆赞这头年轻的公象,它是前任母头象的儿子。在妈妈死后,它就从王子贬成了贱民,也不再是象群的核心成员。绝大多数时候,它都是独来独往,或者待在象群的边儿上。这就是亿万年来象群的行事之道。象群是非常女权的社会,一旦公象进入青春期,它就会被赶走。这是大自然的一种散播基因的方式,否则,所有的象群只能内部交配了。当然,公象被驱逐后,会感到心灵受到极大的创伤,这就好比一个小男孩被送到遥远的寄宿学校后,开始深深地想念自己的家园。一般情况下,它们在荒野上会遇到其他被驱逐的公象。然后它们会在一头充满智慧的老公象的指导下,形成一个关系松散的“单身汉”公象群。
糟糕的是,我们的象群里面没有一头公象可以扮演努姆赞父亲的角色。这样,它不仅仅要经历失去母亲和妹妹的痛苦,同时还要忍受被家人驱逐的痛苦,而这又是它熟悉并热爱的唯一的家。
喂食时间到了。每当这时,弗朗姬和娜娜就粗暴地用肩膀把努姆赞推到一旁。这样,它只能在其他大象饱餐后捡拾它们的残羹剩饭了。见它越来越瘦,戴维决定单独喂它。努姆赞表现出来的感激之情让人不忍目睹,这让原本就很热爱野生动物的戴维更加关注它了。每天,戴维都额外给它扔过去苜蓿草和新鲜的金合欢树枝。
我们做过的事情一丝一毫都逃不过它们的眼睛。
一件事情更加证实了努姆赞地位的卑微。一天晚上,我们听到了一连串长时间的高声尖叫。随后,我们不得不剥夺了威尔玛利用路虎车进行结网工程的权利,驱车赶到了博马的另一端。到那儿后,我们看见娜娜和弗朗姬已经把这头年轻的公象挤到了角落那里,还把它顶到了电围栏上。
我们一边往那里跑,戴维一边气喘吁吁地说:“快看啊,象群把它当成冲击夯了,想把它推出去,好打开一个缺口。”
它们就是这样打算的。努姆赞被带电电线困住,电流穿透它年轻的躯体,这头巨大的血肉之躯发出了声嘶力竭的尖叫。它越叫,它们越使劲推它。终于,在我们出手干预之前,尽管我也不确定怎样干预,它们放了它。这个可怜的家伙猛冲过来,沿着博马围栏全速地跑了一圈又一圈,大声叫喊着它的愤慨。
它终于平静下来,找到了一块远离其余大象的安静地方,站在那里,生着闷气。看起来,它的内心极度痛苦。
这件事更确凿地显示娜娜和弗朗姬完全明白电围栏的工作原理。它们知道如果把努姆赞推过火线,它们就不用害怕被电击中了。然后,象群可以冲破围栏,重获自由。
不管怎样,让我长舒一口气的是,每天让人心惊肉跳的黎明巡逻结束了。娜娜不再带领着家人排着队站在北部边界,吓唬我们它们要集体出逃了。在这几周里,我们克服了极大的困难,也看到了些许进展。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我们谁都没有料想到的。
第二天早晨,太阳刚刚升起,我一抬头,就看见娜娜和小曼德拉站在营地的正前方。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我一站起来,娜娜就抬起大鼻子,垂下耳朵,直视着我,一副平静的样子。我本能地走向它。
在与大象打交道的艰难经历中,我知道大象喜欢从容缓慢的动作,因此我慢慢地走过去,还时不时地故意停下来拽一根草叶,再查看一下树桩,这也是我平常消磨时间的方式。我需要让它习惯我接近它们的方式。最后,我停在了距离围栏 3 码的地方,盯着面前的这个庞然大物。我慢慢地向前迈了一步,又迈一步,离围栏只有两步了。
它没有动,我心头突然掠过一丝满足感。现在距离这个坏脾气的野生动物只有一步了,它完全可以轻而易举地杀死我。可不知为什么,我现在感到从未有过的安全。
我心里充满了幸福的幻想。当这头壮观的生物高高耸立在我的面前时,我已经完全出神了。我第一次注意到它长着浓密尖细的睫毛,皮肤上遍布着成千上万条十字形皱纹,甚至它的断牙都让我觉得新奇。它温柔的眼神吸引着我走过去。然后,就像慢动作一样,它轻轻地伸出鼻子来碰我。我如同被催眠了一般,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仿佛这是世界上最自然不过的事情。
戴维的声音从虚幻的背景传来:“老板!”
随后声音越来越大:“老板,老板!该死,你在干什么?”
他急切的喊叫声打破了魔咒。突然,我意识到,如果娜娜抓住我,那一切就都结束了。它能把我像玩具娃娃一样拽进围栏,然后踩扁。
我想后退,但是脚被牢牢地钉在地上。那种奇怪的感觉又来了,我感到好像被催眠了似的,内心无比平静。
娜娜再一次伸出了鼻子。这时,我懂了,它想让我再靠近些。没有多想,我又向围栏迈去。
娜娜的鼻子像蛇一样从围栏里探出来,小心翼翼地避开电立桩,轻轻地触碰我的身体,并且温柔地抚摸着我。时间仿佛静止了!我很惊讶,娜娜的鼻尖竟然是湿漉漉的,而且身上还散发着好闻的麝香味儿。过了片刻,我抬起手,抚摸了一下它的鼻子尖儿,上面长着又粗又硬的毛发。
这个瞬间马上就过去了。它慢慢地收回长鼻子,站在那里看了我一会儿,然后慢慢地转过身,朝象群走去。象群站在大约 20 码开外的地方,默默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有趣的是,当它折返回去的时候,弗朗姬向前迈了几步去迎接它,就好像欢迎它重返家园一样。如果我想得没错,我认为弗朗姬是对娜娜说——“你做得真棒!”随后,我也回到了营地。
我已惊讶得完全说不出话了,过了好一会儿,才颠三倒四地说:“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该把它们放出去了。”
“究竟是怎么回事?”戴维问道,“把它们放出去吗?从博马里放出去?”
“是的。我们先休息一下,顺便好好谈一谈。”
我们开车回到保护区的小旅店,一边喝着现磨咖啡,一边热烈地谈论着刚刚发生的事情。
“现在,娜娜和它刚来时比,已经完全不一样了,这是事实。”戴维说着,“实际上,整个象群都改变了,它们的暴力倾向没了。也许我们应该给 KZN 野生动物协会打个电话,听听他们怎么说。”
“别打电话。我们自己做主,先把大象放出去再说。野生动物协会已经说过了,我们必须把大象关三个月。他们现在不可能改变主意的。”
戴维点点头:“你说的对。还记得大象从乌姆福洛济运回来之后,有天晚上我们谈什么了吗?我们必须让母头象至少相信一个人。现在我们做到了,它信赖你。”
“好吧,马上呼叫库斯,让他确保外围护栏全部通上电。明天一早,我们就把大象放到保护区里面。”
我们开车回到博马。一想到自己将要做出的重大决定,我内心就非常痛苦。如果我判断错误,象群闯出了保护区,那等待它们的就是死亡。我开始动摇了。不过,在最后一次夜间巡逻时,我注意到大象们表现得更加放松和平静了。这是以前没有过的情形,它们好像正在期待,并等着一件重要事情的发生。感觉到这一点,我心里好受多了。
五点钟的时候,保护区保安从电围栏供电处那里呼叫我,说博马的供电已经切断。戴维把横在博马大门上的巨大栏杆从铰链上抬了下来。
我冲着站在 50 码外的娜娜大喊,并且故意在大门口进出两次,向它显示门已经打开了。然后,戴维和我走开,站到安全距离外的一个蚁丘上,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博马大门口发生的一切。
二十分钟过去了,一点儿动静都没有。终于,娜娜慢悠悠地向大门走去,还用鼻子探测着四周,以确认没有无形的障碍。结果令它很满意,娜娜继续往前走,象群跟在后面。可是,走到大门口的时候,它们莫名其妙地站住不动了,娜娜也不往前走了。
十分钟过去了,它仍然一动不动地站着。我问戴维:“怎么了?它怎么不出来呢?”
“一定是因为门口的水。”他说,“当初,为了从卡车上把大象卸下来,我们在那里挖了坑。现在里面全是雨水,娜娜可不喜欢踏进去。我想它不会从那里走的,因为对曼德拉来说,水太深了。”
接下来,我们第一次目睹了娜娜是如何生动展示它大力神般的力量的。
在门口两侧,立着两根 8 英尺高、8 英寸宽的桉树干,而且树干底部 30 英寸还被灌浇到了混凝土里。娜娜用鼻子检查一番这两根树干,然后低头猛地一推,树干马上就被撞弯了,然后像软木瓶塞一样从混凝土里弹了出来。
戴维和我面面相觑,完全惊呆了。“我的天啊,”我赞叹着,“我们就是开着拖拉机也做不到这一点啊。想想昨天,我居然还让它碰我了呢!”
水沟周围的障碍清除了。娜娜已经等不及了,它带着象群沿着保护区里的一条小路直奔河流而去。我们眼看着夏天浓密的丛林吞噬了它们。
“我希望我们做得对。”我说。
“我们做得没错。它已经准备好了。”
我希望戴维的判断是正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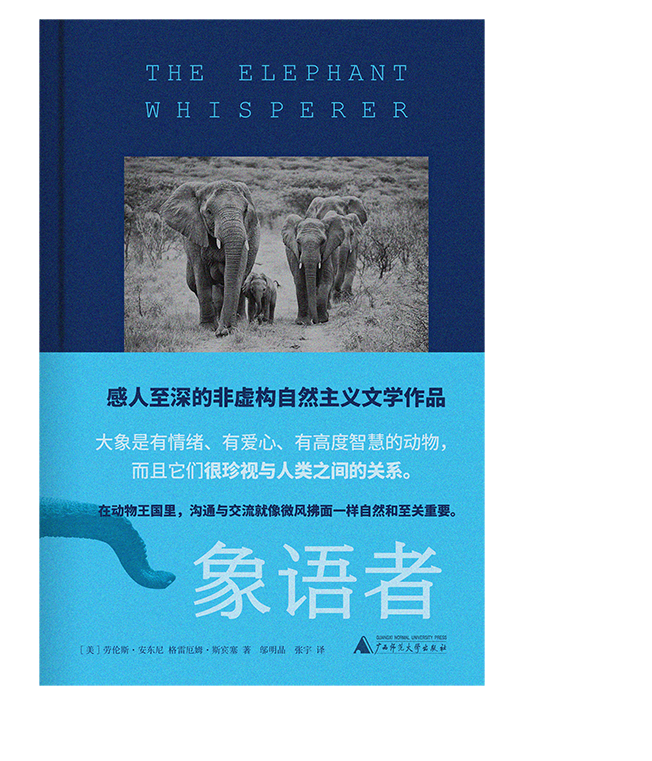
本文摘自《象语者》
[南非]劳伦斯·安东尼 / [英]格雷厄姆·斯彭斯
邬明晶 / 张宇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 年 7 月
题图来自 Florian van Duyn on Unsplas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