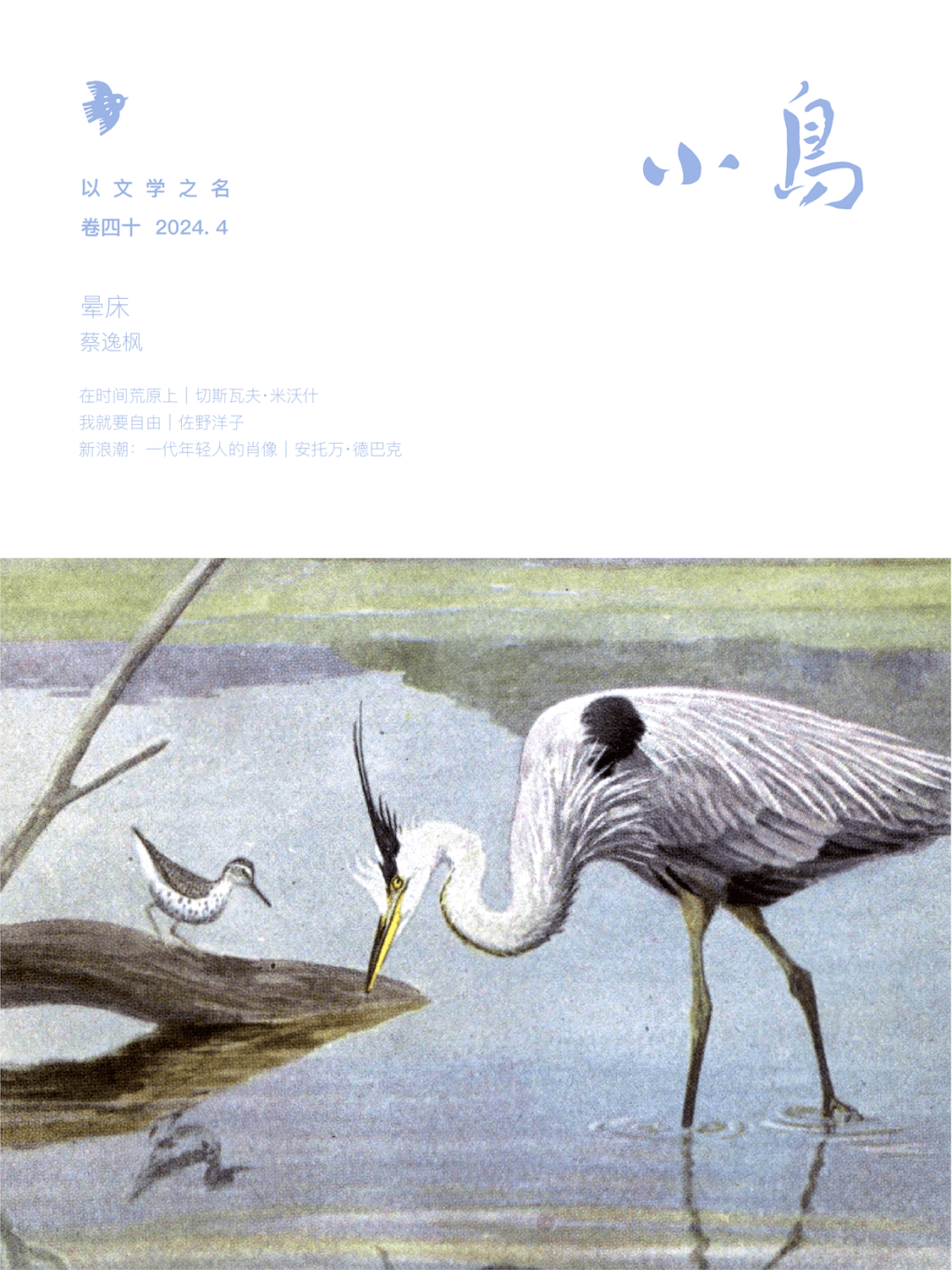《红唇》是拉美文学偶像普伊格,浪子文学代表作。1969 年,小说于杂志上连载,共十六期。以书信、日记、剪报……甚至警局档案、家庭相簿、塔罗占卜,拼贴出一场错综复杂的多角恋。
男主角胡安·卡洛斯是个迷人的浪子,但本书一开篇,他就已经死了。这场死亡如同一个线头,牵出情人们彼此纠缠的乱麻。书中没有传统的小说文本,有的只是:付之一炬的情书、尘封多年的档案,卑微的忏悔、痛苦的吊唁、心碎的独白。读者必得亲自解谜,成为故事中的一环,在迷宫中找寻出口,一如那些受困的男女。
经“野望”授权,我们摘选了本书译后记,分享给读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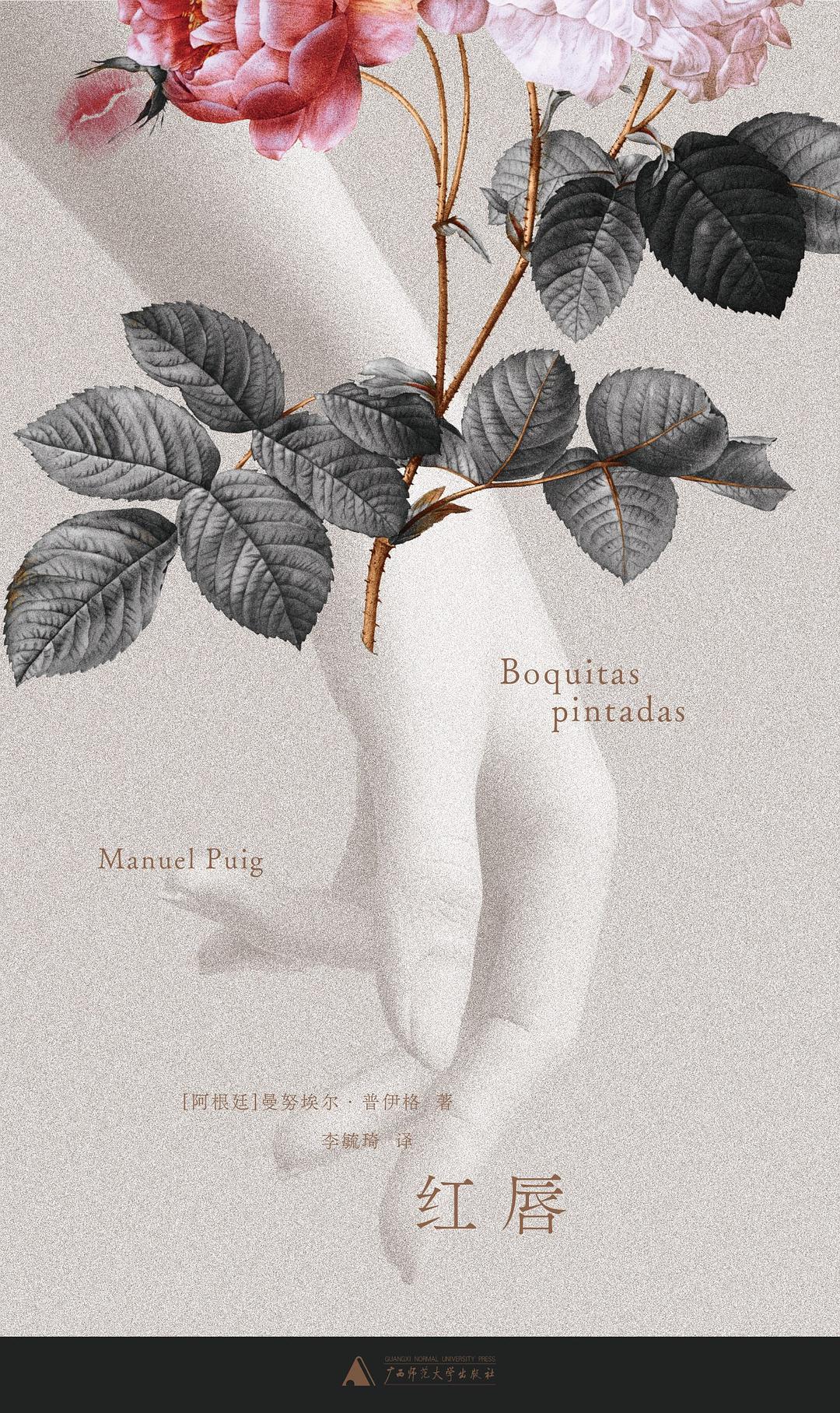
你是音乐、苍穹、宫殿、河流、天使,是上帝终将显现在我死去的双眼前那朵永恒的玫瑰,隐秘,而没有尽头。
- 博尔赫斯《永恒的玫瑰》
迷影 | Película
必须承认,以突如其来的讣告打头的《红唇》,远不算一本可以轻易看进去的小说。拼贴,或者说蒙太奇,是其中不可或缺的关键词。当然,也绕不开普伊格的迷影情结——普伊格本人学电影出身,后来进行文学创造时总是不自觉带上蒙太奇的结构方式,或许,也只有声、光、影、画俱全的电影,才足以栩栩如生地描绘出那些各各相异的,心碎的波莱罗之夜。
——在那些冬雨淋漓的夜晚、终有一别的波莱罗舞曲中,究竟发生了什么?
时间回溯到 1932 年 12 月 28 日,曼努埃尔·普伊格出生于潘帕斯大草原上的比耶加斯将军镇。他将自己的家乡形容为“一个远离海、群山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无所有之地”。1951 年,普伊格前往意大利罗马学习电影。他曾立志成为导演或编剧,但始终未能如愿,于是转向文学创作。
1968 年,普伊格的小说首作《丽塔·海华丝的背叛》出版。在这部半自传体小说中,普伊格借用通俗浪漫小说和电影杂志的语言,辅以现代主义的技巧,创造出一种汪洋恣肆的美学,描绘了自己泡在电影院里的童年。这部作品影响深远,风靡拉美,成了又一部被世界读者广泛接受的拉美文学经典。
次年,他的第二部小说《红唇》于杂志上连载,其中的人物几乎个个都是狂热影迷。千金小姐玛贝尔认为,在令人窒息的炎热中,“最理想的安排是跟她那个同为影迷的姨妈一起,走进一家开放冷气的电影院”,并对布宜诺斯艾利斯每家影院所放映电影如数家珍;女佣拉瓦因为雇主突如其来的要求,懊恼于“恐怕没法去电影院看她常看的星期五特价场了”;内妮在婚后去了玛贝尔提过的“歌剧”电影院,感慨“豪华得远远超出我的想象”。小说详细描述了一部电影和一部广播小说,达到了“戏中戏”的效果,同时又与玛贝尔和内妮两位人物的性格、命运与当时的经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今天放映的是一部喜剧大片,场景令她心驰神往:宽敞的大厅、黑色大理石楼梯和镀铬的扶手、白色缎面椅子、白色缎面窗帘、蓬松的白色羊毛地毯、镀铬的桌腿和椅腿。大厅里坐着一名打字员,是个美丽的纽约金发女郎……夜复一夜,当激情涌上心头时,他们的身躯在黑暗中如同镀铬一样熠熠生辉,镀铬的心脏绽开了,鲜红的热血向外喷涌而出,染红了白色的缎面、白色的皮毛:当镀铬的外壳已无法抑制灼热的血液时,两对嘴唇每夜凑在一起,赠给彼此禁忌之吻。
由此,普伊格用复述电影情节来纾解和表达情绪、预示和推动剧情的手法初见端倪。这一手法延续到了 1976 年问世的代表作《蜘蛛女之吻》中——小说中串联的六部电影向来为人称道。这部迷影作品的改编颇为成功,除了由美国演员威廉·赫特出演的同名影片,歌舞剧《蜘蛛女之吻》亦是一炮而红,多年来久演不衰,成为百老汇的经典剧目。
普伊格的创作方式给后来的许多作家以启迪,村上春树、大卫·福斯特·华莱士等都是其忠实拥趸。王家卫的电影以非线性叙事风格而闻名,而他坦言,以标志性的剪接手法打乱角色关系和剧情发展的灵感,正是来自曼努埃尔·普伊格的作品。当年王家卫选择张国荣和梁朝伟远赴阿根廷拍摄《春光乍泄》,据说正是向普伊格致敬。在王家卫眼中,普伊格“最好的作品”便是《红唇》,这部小说也成了《阿飞正传》的灵感源头。
波莱罗 | Bolero
可以说,曼努埃尔·普伊格的叙事能力和语言功底都相当惊人,这和他从小接受阿根廷传统故事演绎的熏陶,以及一生长期四处流亡有关。多年的文字磨练,对影视戏剧文化的良性吸收,对拼贴技法的熟练应用,使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写作风格。而在《红唇》这部爱情小说中,他的语言仿佛带有波莱罗舞曲的韵味,每一章皆以一段流行歌词开头,而主人公的彷徨情绪则展现得淋漓尽致。
波莱罗(Bolero)是拉丁美洲抒情歌曲中的一种。它的歌词取材于日常生活,糅合欧洲诗歌中使用的语言、非裔民族传唱的旋律和美洲原住民的情感,常在家庭、节日和大型音乐厅等各种场合中表演,与探戈一同成为阿根廷社会鲜明的文化象征。
《红唇》中,曾出现名为《探戈对决波莱罗》的电台节目,而小说本身的情节,又何尝不是一场活色生香的纸上探戈。这种据说是情人之间的秘密舞蹈,舞蹈者必须表情严肃,表现出东张西望,提防被人发现的模样。从马德罗港口的表演,到街头巷角成对蹁跹的男男女女,无一不是抿紧了嘴角,跳舞如暗流涌动的华丽搏斗,热烈狂放、变化无穷,似心悦又似决裂。
关于波莱罗最动人的段落之一,出现在多年后,当内妮与玛贝尔在家中喝着马黛茶促膝谈心,既是闺蜜又曾是情敌的两人一番交锋,回忆起当外面刮起尘埃滚滚的草原之风的少女时期,她们是如何相信爱情,又几乎同时隐秘地领略到,命运如何让她们变得言不由衷和身不由己:
内妮说她喜欢波莱罗舞曲和将它们介绍过来的中美洲歌手。玛贝尔连连附和。内妮继续说,这些舞曲总能扣动她的心弦,歌词好像是为全天下的女人而写的,又像是写给每一个特别的女人的。玛贝尔觉得,这是因为波莱罗舞曲唱的都是肺腑之言。
事实上,每章开头循环往复出现的舞曲,几乎伴随着每一个人物的、不可避免的宿命——随着与死亡的距离愈来愈近,爱却在痛楚中被打磨得愈发闪光。读者必须以足够的时间展辐去理解、观看,才得以百感交集地体会到,那些要求烧毁的情书与心碎的独白,塔罗牌反复切牌却测算不出的“命运”“灵魂”“玷污”“背叛”……于是故事中人人都在青春岁月消逝后心绪翻涌,面对虚空中永恒停在二十九岁的英俊容颜,进行凄艳的忏情自白。
拼贴 | Collage
《红唇》中,普伊格的看家绝活之一,便是“不好好讲故事”。为了营造一种原汁原味的粗粝感,他几乎穷尽了所有读者能想到的叙事方式。出生证明、犯罪记录、庭审报告、广播小说,多种不寻常的叙述语言与现实命运交织,在多声部讲述中,人物的虚荣和自私被赤裸剖析。
于是读者会看到,无花果树下心怀鬼胎的男女、忏悔室中吐露惊天秘密的新娘、吉普赛占卜摊前老妪与美男子的对峙……一段痴男怨女、阴阳永隔的故事,在他的笔下跌宕起伏,充斥着斑斓的光晕。他喜欢并列同一时间段不同人物的所作所为,动用更精微的显影术、更高曝光的冲洗方式、更敏感的感知触须,如此专注却又徒劳地探勘着事实与人心、欲望与卑微、忏悔与心碎。
这些画面,孤立地看如同一幅幅立体主义拼贴画,但都与阿根廷社会的全景图发生着联系。普伊格把现实生活中司空见惯的日常文件拼贴起来,放置在同一文本之中,使读者眼前一亮,达到“陌生化”的效果,也极大地增加了文本的容量。各种意象的叠加手法,在第一部的尾声、长达四页的罗列中登峰造极:
……提审,诈骗,破产,耻辱,贫穷,土豆泥,烤苹果,糖浆,我母亲,我妹妹,咖啡,晚上 9 点 15 分,寒冷,彭丘,人行道,风,土路,街角,大门,女贞,金发姑娘,内妮,我的女朋友,她母亲,她父亲,厨房,桌子,油布,科斯金,治疗,痊愈,镇政府,我的工作,计划,动机,当花匠的父亲,人行道,大门,内妮,她父亲,苗床,女贞,人行道土路,未粉刷的房屋,打包工的职位,白皙的肌肤,嘴唇,寒冷,风,大门,厨房里的灯光,厨房里的母亲,女人的诺言,“你还没痊愈吗?不过要不了多久,我相信到年底你肯定就痊愈了,坐大巴累吗?”,十四号房间,老人,你敢跟一个病人结婚吗?……
就这样,一张张微缩显影胶片飞快地闪回——读者只能在缺失应有动词的前提下拼凑出所谓的真相,就像看电影时忘了拿一副改变折光的眼镜,让人如雾里看花。
至于占据小说大量篇幅的信件,又何尝不是曝光后停格的一张张青春画像,在焚化炉中被烈焰短暂点亮,直至彻底烧毁;而读者则在时光的长河中,观察当年山盟海誓之爱如何腐蚀,如何持续衰老,甚而为了一瞬的爱情光焰,不得不长久地忏悔:
“……你看,金发姑娘,只是跟你聊了一会儿,我就觉得好些了,要是能见到你,我会高兴成什么样啊……”“……我爱你胜过爱任何人……” “……科斯金还有一家医院……” “一有更多消息,我就给你回信……” “……科斯金河的水暖洋洋的……”“……你也太遥远了……” “……现在我每读一遍你的信,就又增添了几分信心……”
正如略萨所言:“普伊格作品的创新之处在于,其所描绘的人工、漫画式的生活,会将生活的其他面向排除在外,并取而代之,成为唯一的真相。这就让他的小说有一种独特的氛围感。虽然普伊格的文学视野基于人类最普通的一种经验——通过各种形式的想象,从现实世界遁入梦想世界——但他所描绘的世界却显得那样遥远、华丽且不真实。”
阿根廷 | Argentina
普伊格成年后很少住在阿根廷,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流亡他乡,但他所有的小说几乎都关于阿根廷或流放中的阿根廷人。
一般中国人了解遥远的阿根廷,除足球外,总逃不开高乔、探戈、马黛茶一类充满异国情调的名词,也许,还要加上博尔赫斯笔下辗转如中国屏风的《小径分岔处的花园》,以及《春光乍泄》中惆怅的南方酒吧、气势滂沱的伊瓜苏瀑布。有人会想起那首堪比国歌的《阿根廷,请别为我哭泣》,以及那首举世闻名的探戈舞曲《一步之遥》,暗暗诧异为何关于它的种种腔调虽然浪荡不羁,却总有挥之不去的忧伤。
《红唇》中很少直接描述阿根廷,但又处处飘荡着马黛茶的芬芳。阿根廷人嗜马黛,分享一杯滚烫的马黛茶,是增进情谊的绝好机会,许多家庭都珍藏着祖传的马黛茶杯。那苦而回甘、滋味悠长的马黛茶,就跟小说中错综复杂的关系一般耐人品味。传闻中的阿根廷四宝:足球、探戈、马黛、烤肉,既构成了阿根廷人生活的一部分,也是其达观潇洒的精神寄托。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夜晚,到处是熙熙攘攘的餐馆、剧院、探戈俱乐部,酒吧中人人都有自己心仪的球队。这里的银行可以理直气壮地十一点开门、三点关门,市中心的抗议与游行也成家常便饭。人们习惯啜饮马黛茶,向烤肉上撒粗盐,下午三点用午餐,夜间九点用晚餐,约会时使用“拉美时间”迟到半小时,不论见到谁都先紧紧拥抱、亲吻脸颊;口中所说的西班牙语经过独特的阿根廷口音渲染,变得抑扬顿挫、跌宕起伏,令初来乍到者迷惑不已——这亦是阿根廷的一大特色。
然而,正如探戈舞者总是眉头深蹙、拒不对视,马黛茶初饮时苦涩如中药、细细品味才有回甘——阿根廷的气质决不是一派天真欢快。这个国家奔放而浪漫,高傲且敏感,以狭长之形居于南美版图末端,恰似世界尽头的曲折仙境。它的移民大多来自西班牙和意大利,这两个欧洲最自由不羁的国度,将浪漫与热情带到了这片南美末端的土地,也让它原封不动地继承了南欧的懒散与动荡。这个民族的历史有着苦难的底色,经过多年跌宕与炮火的洗礼,故而在放荡中不乏挣扎不屈的美。
在那些晴朗的日子里,漫步在阿根廷街头,你会看到它的天空湛蓝无比,像被一把锋利刀子深深切开那样深邃,如国旗一般蓝白分明。而云少的时候,天空就显得无限高远,楼宇之上的蓝似乎能到达宇宙。这个国家靠近南极,就连大气也要稀薄几分,仅仅看一眼就会让人忘怀——你会明白,阿根廷人天生的忧郁与世界尽头的孤独,全都有理可循。而这也许正是《红唇》的魅力最深处所源来。
题图为舞台剧版《红唇》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