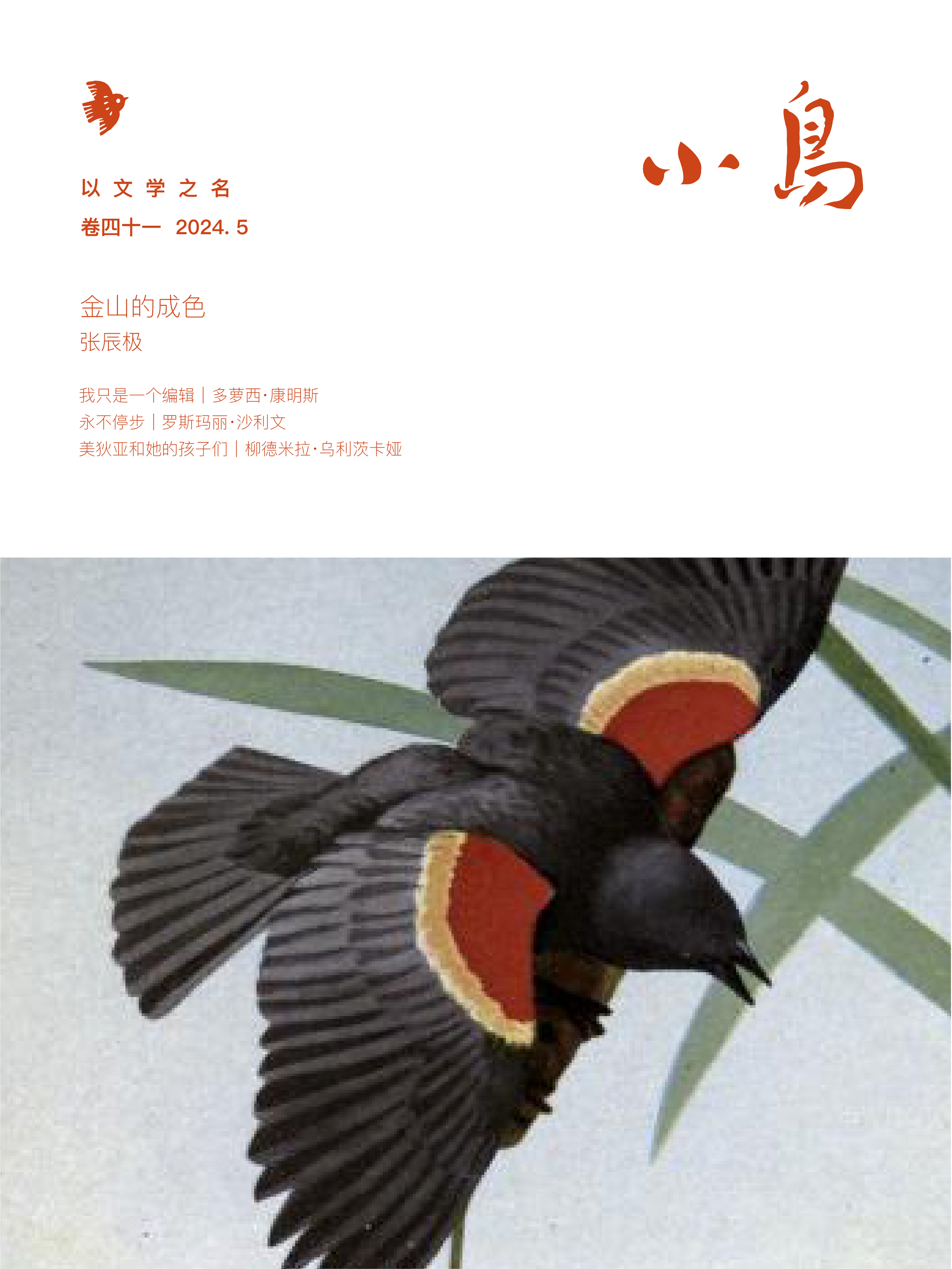作为一名日裔美籍学者,吉原真里面对亚洲(裔)古典音乐家在西方世界日益增加的关注度和影响力的现实,从自身古典音乐训练的经历、自己的亚裔身份出发,展开了这项“把自己作为方法”的民族志研究。
《古典音乐界的亚洲人》一书以 70 多位亚洲(裔)音乐家的访谈为基础,探讨了古典音乐在亚洲传播的历史、文化及其艺术形式的本质,并考察了亚洲(裔)音乐家在白人主导的古典音乐世界中所扮演的角色,他们的种族身份、性别身份和阶级地位如何影响他们的职业经历、发展和成就。
经“拜德雅”授权,我们节选了《性别扮演》一章,分享给读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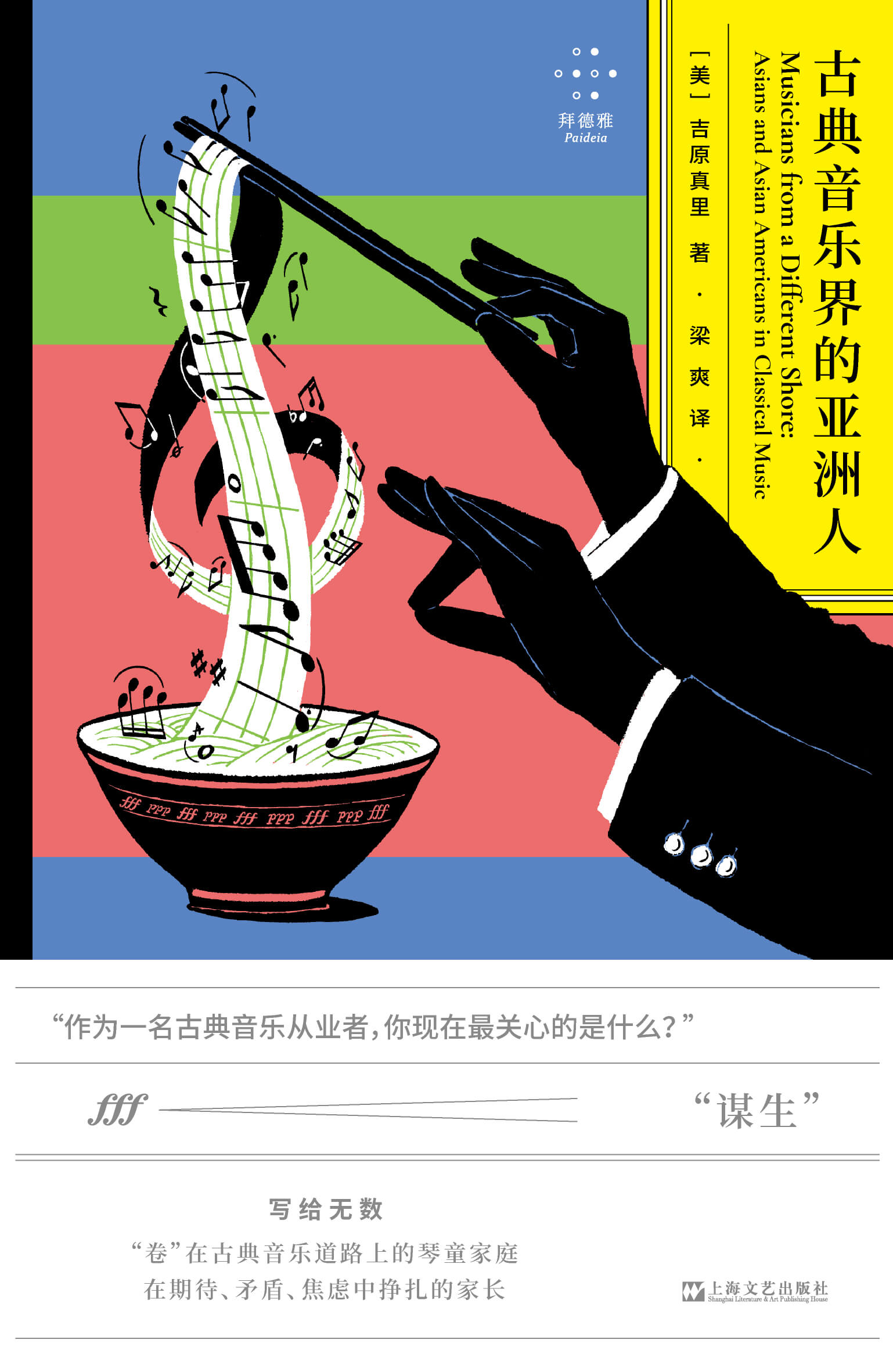
女性音乐家在处理来自音乐职业和社会整体的性别化期望时,面临的是另外一种挑战。对很多亚洲(裔)女性音乐家来说,追求古典音乐是遵循性别常规期望所走的一条道路。不论是东亚还是美国,在中产阶级的背景下,做一名勤勉的音乐学生符合成为一名好女孩和一名品德高尚的年轻女人的要求。然而,当她们开始更严肃对待音乐,决定从事该领域的工作时,她们的性别和种族组合则带上了全然不同的含义。亚洲(裔)女性音乐家常常发现,要想成为一名成功的职业音乐家,她们必须违背自己身上背负的性别期望。尽管对全体女性音乐家而言,不论是什么种族,都得在既定的女性常规和女性气质典范与艺术表达和职业生涯的要求之间周旋,亚洲(裔)音乐家还必须面对亚洲文化中特有的性别常规。除此之外,由于主流美国文化对亚洲(裔)女性赋予性别化(gendered)和性化(sexualized)的含义,亚洲(裔)女性音乐家需要以一种既能让自己受益,又不会使自己的艺术和个人名誉受损的方式来把控自己的形象和身份。
就像许多亚洲(裔)音乐家并不认为种族或种族歧视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是特别重要的影响因素,我的一些女性受访者告诉我她们也不认为古典音乐职业中存在特别严重的性别歧视。尤其是交响乐团的音乐家,她们试演的时候在屏幕后方,并不认为性别(或种族)在应聘过程或日常工作中有多重要。除此之外,就像很多亚洲和亚裔美国音乐家不太参与种族或族裔议题一样,许多亚洲(裔)女性音乐家在谈及性别议题时并不具有一套特别政治化的语言。在我的采访中,极少有明确自己是女性主义者的受访者。
当然,少有人明确指认女性主义身份这件事,也许更多反映的是社会历史背景,而不光是她们个人的政治取向。在我进行采访的时候,我的很多女性受访者的年龄在 20~30 岁出头。她们是“后女性主义”的一代,在她们的成长过程中,她们的女性主义前辈据说赢得了许多以性别平等为目标的战役。很多人认为能够同时追求事业和家庭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还有很多人将女性主义跟愤怒的、厌男的、烧掉胸罩的、无性的女人联系在一起。除此之外,即便现在很多年轻女性都有在上大学时接触到女性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础的政治语言,但那些青年时期在音乐学院度过的人则缺乏这样的经历。
然而,缺乏讨论女性主义的政治语言,并不意味着她们对性别议题缺少意识,或者看不到性别如何影响自己作为音乐家的生活。在采访时,即便在我没有明确问她们相关议题的时候,许多女性音乐家都会提及音乐职业领域中男性占主导的特征,以及女人在音乐职业生涯中遇到的重重困难。许多人还在谈论职业路径时讨论到性别议题。实际上,亚洲(裔)女性音乐家在分享故事时对自己人生路径的描述,就表露了性别和种族在她们作为音乐家的生活中所承担的核心角色。
我采访钢琴家海伦·黄的时候,她正在茱莉亚音乐学院读最后一年。她说在她 18 岁开始自己巡演的时候,她意识到巡演音乐家的生活是多么孤独,也开始思考要平衡事业和让人充实的家庭生活是多么困难:“身为女人,你怎么去处理这些?对男人来说这要容易多了……容易太多了。”小提琴家詹妮弗·高说,虽然她在作为音乐家的工作中很少担心自己的亚裔身份,但“我觉得在音乐世界中更难的其实是身为女人……不过,我觉得现在也有了变化。但我认为在过去做女人是很艰难的,对于那些年轻时 [表演了] 很长一段时间、现在年长一点的女人,那样的转变对她们来说是非常困难的。你知道的,没有人会为舞台上长得丑的男人喝倒彩,但要是女人就完全不同了”。
即便在音乐家们进入职业生涯之前,性别就已经在音乐学院对他们的日常经历产生过影响。亚洲(裔)女性音乐家很清楚亚洲(裔)学生被性别化的形象和刻板印象,以及她们身上背负的期望。当我的受访者,尤其是学生和刚从音乐学院毕业的人,讨论起对亚洲(裔)音乐家的种族刻板印象时,他们很多人会特别谈及对亚洲(裔)女性的刻板印象。他们提到了一个十分流行的对亚洲人,尤其是韩国(裔)人的刻板印象,说的是到茱莉亚音乐学院上学的女性学生并不是在严肃追求音乐,她们来这里上学只是因为她们的父母希望她们在音乐学院历练后,能回家找个合适的丈夫。不论这是否站得住脚,这样的说法肯定还是会影响全身心投入音乐的亚洲(裔)学生。
你知道的,没有人会为舞台上长得丑的男人喝倒彩,但要是女人就完全不同了
钢琴家米拉·黄回忆起当她在茱莉亚音乐学院和曼哈顿音乐学院学习时,哪些学生比较认真是一目了然的:“因为我们有很多演奏课,[学生会在其他人面前演奏,] 你会注意到哪些人总是做好了准备,愿意表演……有的人则总是坐在角落,跟朋友聊天玩笑……其中有的是亚洲(裔)女性……当然存在一看就对职业不太严肃的亚洲(裔)女性,她们来上学只是出于一些别的什么原因。” 她说,尽管她从未在职场上经历过明显的种族歧视,但她的确感受到对亚洲(裔)女性的刻板印象是真实存在的,亚洲(裔)女性必须加倍努力才能出人头地。
钢琴家杉山美织(Miori Sugiyama)所说的也回应了黄的说法:
在像茱莉亚音乐学院这样的地方,我们这些亚洲(裔)女孩占了钢琴系的大多数……有个刻板印象是说社会上有太多亚洲(裔)女性钢琴家,在某种程度上我感觉在你被介绍给经纪人时,就带有先入为主的劣势了。如果你是亚洲人、女性钢琴家,那么你就自动……你得非常努力,才能显得跟别人不同,我觉得我们已经很努力了,但这份工作太沉重了,太让人受挫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以形象为主导的文化,他们想要有代表性的钢琴明日之星是一个能够真正代表这个国家的人。很显然,在很多情况下这不会是一个亚洲人,一个亚洲(裔)女性。[有可能] 更会是一个棕发或金发碧眼的男人……典型的美国形象。
然而,性别议题不仅跟形象和刻板印象有关。亚洲(裔)女性音乐家还需要在塑造了这个行业的性别经济中小心行进,其中最常见的现象是年长的白人男性老师与年轻的亚洲(裔)女性学生之间发生性关系。白人男性与亚洲(裔)女性之间的浪漫关系在美国-亚洲的历史上是普遍发生的事情,在古典音乐的世界中同样如此。的确,许多 1960 年代首批到美国学习音乐的女性学生与她们的白人同事或老师结婚了。当然,许多亚洲(裔)男性音乐家也有同白人或其他非亚洲(裔)背景的女性结婚或发展浪漫关系。在这个有着相对多男同性恋者和女同性恋者的领域中,在亚洲人与白人之间发生的同性浪漫关系也相当普遍。然而,我与音乐家们的对话——有亚洲人和白人、男性和女性——无疑表明了,他人对亚洲(裔)音乐家性别和性关系最典型的设想是年长的白人男性与年轻的亚洲(裔)女性在一起。考虑到音乐学院的教职员工中大多数仍是白人男性,这并不是什么出人意料的事情。许多音乐家很容易就能够指出几个曾跟他们的亚洲(裔)学生发展浪漫关系或者结婚的白人男性老师,这些学生通常比他们自己要年轻得多。当我在纽约进行田野调查时,我在几个场合里见到一位知名的白人男性钢琴家兼评论家,身边总有一位明显看着是他照顾对象的年轻亚洲(裔)女性(并不总是同一位),这个男人因其女友一个接一个都是年轻的亚洲(裔)学生而臭名昭著。
当然,亚洲(裔)女性在这类关系中并不总是受害者。部分亚洲(裔)女性学生自愿与她们的老师进入浪漫关系。然而,在这样的性别关系和性权力关系中隐藏着各种问题和危险,亚洲(裔)女性音乐家常常要学习如何去应对。单独授课是极其亲密和私人的,而且充满高涨的情感和大量的身体接触——在单独授课时,学生将自己全身心地交付给老师进行评判和指导,很多时候跨越了音乐知识和技巧的界限——置学生于脆弱的境地中。尽管近年来明目张胆的性挑逗和性骚扰越来越少发生,但是我的部分女性受访者仍跟我讲述了她们或者朋友被老师施加此类压力的一些事件。
这种性张力同样存在于女性音乐家与其他对她们职业生涯有重要影响的男性的关系中,比如指挥、音乐总监、经纪人和资助人。小提琴家安·亚纪子·梅耶斯描述古典音乐“仍是一个男性行业”。她说,当她发现美国主要交响乐团在 2005 年才首次任命女性指挥家 [马林·阿尔索普(Marine Alsop)从 2007—2008 乐季开始担任巴尔的摩交响乐团音乐总监] 时,她感到非常惊讶。当我让她分享自己在这个男性主导的行业中的经历时,她给出了以下回应:
我会跟一个对我大献殷勤的指挥一起工作。然后我会想,如果我是俄罗斯汉子,他还会这么殷勤吗?只因为我是女孩、单身,在这里进行专业工作,他就感觉自己能 [挑逗我]……这真的让我感到匪夷所思。那样的行为对我来说很恶心。我不感兴趣,我们之间是不会发生什么的,我来这里不是为了那个。我来这里不是为了跟指挥上床。我来这里是为了工作,为了演奏音乐。行业中的这方面有时候让人痛苦不堪……这类事情发生了很多很多次。许多指挥拥有很大的权力,他们能决定找哪些艺术家合作,所以你必须如履薄冰。
正如梅耶斯解释的,尤其是对那些追求独奏事业或歌剧演员事业的音乐家来说,男性指挥的支持常常是决定他们成败的因素。在音乐家们之间流传着的许多故事和谣言,都是在说某些知名女性音乐家与帮助自己事业启程的、掌握权力的指挥或经纪人发生性关系这样的事情。
然后我会想,如果我是俄罗斯汉子,他还会这么殷勤吗?
当然,这类关系并不只发生在女性音乐家与男性指挥 / 音乐总监 / 经纪人 / 资助人之间,而且有这类关系的女性音乐家也不全是亚洲人。指导和支持的关系也不一定包含性。在我的研究过程中,我遇到了一些受资助的女性,她们的资助人为她们提供了慷慨的金钱资助和 / 或帮助她们获得演奏的机会,有的完全不要求任何附加条件,有的则只要求她们提供文秘或其他与性无关的服务。这些资助人中有的是亚洲(裔)男性或者白人女性。因此,手握钱权的资助人提供的资助不能单单以性别、性和种族的角度来解释。然而,需要承认的是,亚洲(裔)音乐家是在一个更广阔的种族和性别环境中工作的,在这个环境里,古典音乐界中大部分持有决定权的人是年长的白人男性。亚洲(裔)女性音乐家,不管她们是否与这些男人发生性关系,都很清楚这其中的权力关系,小心翼翼地规划自己的职业和个人生活。
如今的亚洲(裔)女性音乐家,同样要与性别角色的社会常规和跟追求音乐事业不符的女性气质典范进行搏斗。钢琴家李素妍是采访中少数几个明确称自己为“女性主义者”的音乐家之一。李素妍是一名非常有魅力、光彩夺目且友善的女人,在我们进行访谈的那段时间,她正在茱莉亚音乐学院考艺术家文凭,是一位明星钢琴家。她的兴趣爱好在古典音乐家之间并不寻常:当我问起她最喜爱的音乐家是谁时,她毫不犹豫地回答“披头士”。她对我的问题——“你认为你的韩裔或亚裔身份在哪些方面影响了你作为音乐家的生活?”——作出的回答就很能说明她的想法。这是一个跟种族身份重要性相关的问题,并不是专门在问性别身份,但她给了我一个十分敏锐而深刻的回答,这个回答与性别歧视、性别刻板印象、对亚洲(裔)女性音乐家生活造成影响的女性气质典范相关。对李而言,种族问题与性别问题是紧密相联的:
对一个亚洲人,尤其是女人来说,要在古典 [音乐] 世界成功是很难的。我最近对此的感受越来越深刻。因为我们的文化教导我们要礼貌,太礼貌了,几乎变成了一种温驯。我们眼中的粗鲁行为有时恰恰是获得工作机会,在这个领域成功的必要条件。
李继续说她曾认为女性能够获得与男性相当的成就,女性个人的努力能够使她们突破屏障,取得认可。然而,她反思了这种对任人唯贤原则的信奉如何使她对音乐世界中各种形式的结构性性别歧视,以及对音乐职业中女性在实践和心理上的困难视而不见。她还讲述了自己如何通过练习各种武术和瑜伽来争取克服自己身形比男性钢琴家要小的劣势。
李素妍对那些投射于亚洲(裔)女性音乐家身上的种族化和性别化期望的想法是最敏锐的:
我认为美国人或全世界都认为亚洲(裔)女性是温驯的。那样的观点让我觉得很困扰……有那么多亚洲(裔)女性是弹钢琴的。我们扎着小马尾辫,穿着蓬蓬裙,尤其是上大学前的那些小孩,我不知道人们还会不会把我们放在眼里,真的。因为对亚洲(裔)女性的期待大部分就是希望她们嫁给一个有钱男人,做居家贤母。对,近年来是有很多变化,但是变化又没有那么大……我在首尔的父母会说:“你知道的,[你的钢琴] 是很重要,但你身边没有 [可嫁的] 律师或医生吗?” 我觉得就因为那 [种在亚洲人之间流通的性别典范],即便是 [茱莉亚音乐学院] 这里的教职员工或许也会自然而然地想:“这个女孩很有才华,很棒,但她终有一天可能要嫁人,不再从事这个职业。”很多人的确是这样想的。所以出于那样的理由,经纪人和整个社会就已经不把我们当回事了……有的老师,尤其是比较传统的老师,真的会把关注主要放在男性 [学生] 身上……做女人,一个女性化的人,还要非常坚强,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人们不想承认这点。我认为亚洲(裔)女性要非常非常努力才能摆脱迟早一天要结婚组建家庭这个被规划好的情景。我认为像内田 [光子],还有谁,[小提琴家] 郑京和这样的人是真正逃出来了。但这太罕见了,才两个人,总数又有多少?我刚到 [茱莉亚音乐学院] 上大一的时候,这里有 16 个女孩,1 个男孩。我们班是这样的。我们班的情况很奇怪,大部分情况下多少是平均的。但是来茱莉亚音乐学院的女生总是更多。当她们离开时,最终升上博士的全都是男生。这些全部通过委员会评判的女孩,她们不知怎地就消失了……我不知道她们去哪里了,杳无音讯。只有那个男的还在。真是个谜啊,我还没解开这个谜,除了说或许是因为社会已经有先入为主的看法,认为我们反正都不会继续下去,所以他们也不会努力为此创造机会。我不知道。
跟李一样,许多女性音乐家会长时间挣扎于性别常规和音乐追求之间的张力。钢琴家平田真希子在回顾自己生活各阶段经历的心理动荡,以及她在这些年演奏水平发生的变化时,告诉我她感觉自己在演奏中经历过的问题很大程度上跟自己与性别角色的挣扎有关:
一方面,我对音乐一直都是非常严肃的,也想作为一名音乐家获得成功。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会把自己锁在练习室里,跟外界断绝,不关心别人怎么看我,也不关注自己的外表。但另一方面,我内心的一部分想要找个好男人,结婚,过上普通女人的生活。我内心的那部分一直在对我说,将自我全然投入音乐中,毫无保留而激进地表达情绪,是不符合女性气质的。我觉得对吸引力和女性气质的渴望让我在演奏时有所保留。
平田对自己如何内化性别的社会常规深有感触。她真挚的评论表明了,即便音乐家们人生中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在与世隔绝的环境下只身进行训练,但他们仍植根于宽广社会里的各种常规和规范,也深受它们的影响。

- 加藤幸子
钢琴家加藤幸子(Sachiko Kato)曾同样陷入艺术追求与性别常规之间的两难选择的境地。尽管她没有直接以性别的角度叙述自己的人生故事,但她对人生不同阶段的反思很大程度上被组织成一种关于性别身份的叙事。当加藤和家人在她青少年时期从日本迁居洛杉矶后,她获得了在一所当地大学学习钢琴的全额奖学金。
然而,她感觉自己无法融入洛杉矶的环境中,因为周围的女性学生都是“典型的女生”。尽管她没有解释“典型的女生”是什么意思,但她余下的故事表明了,她对自己偏离常态的感觉来自她对音乐的态度、她的日本身份和性别这三者的结合。她说在加州圣巴巴拉西方音乐学院(Music Academy of the West)学习的那个夏天对她的人生起到了催化作用。她见识了其他学生出色的才能,被此深深震撼,但她也感觉这是自己有生以来第一次找到一群她能够融入并自在相处的朋友。后来她移居纽约,在茱莉亚音乐学院进行硕士学习,毕业后移居波士顿。
跟其他很多音乐家一样,加藤真正的挣扎始于毕业之后。她同时忙碌于参加比赛和谋生,感到筋疲力尽。她失去了方向感,觉得做钢琴家是很大的负担,因此搬回纽约,进入她自称的“漫长假期”。在这些年,她在纽约的一家日本书店工作,与不是音乐家的日本朋友社交。她回顾了那段时光:
因为我没有在日本长大,有一段时间我单单是因为讲日语或被日本人社群接纳,就已经觉得很开心了。在此之前我没有任何日本朋友。当我在茱莉亚音乐学院的时候,我觉得日本来的学生是一群跟自己差异很大的人,除了某个我现在仍很亲近的小提琴手之外,我没有跟那里的日本学生交往过。[我在多年的“假期”中沉浸于日本人社群,算是从那段时期反弹回来了。] 我既不觉得自己是彻底的日本人,也不觉得自己是彻底的美国人,年轻的时候我会有意识地把自己推往其中一个方向来应对那样的感觉。但我现在意识到,让自己更多成为两者中的某一个,是在否认我自身的一部分。
加藤在她的“漫长假期”寻找着自己作为钢琴家、日裔和女人的身份。当她解释自己如何重新开启职业生涯时,她很明确地说,这个过程与自己对性别典范的观念改变相关。在多年的自我探索,尤其是在 2001 年 9 月 11 日发生的恐怖袭击后,她重新考量了生活的重心,同时也通过翻译工作取得了经济上的稳定。两者都帮助她重新发掘出自己作为一名钢琴家的身份和自信,但她还说,“[我的突破] 还与自己过了‘正常女孩’的年纪有关。我开始觉得自己并不需要结婚,我感觉自己无牵无挂”。在故事的结尾,她坚定地说:“我从来没有过过正常人生。”值得注意的是,她所说的“正常人生”是暗指女性的“正常人生”,她通过摆脱婚姻和家庭这种传统的性别期望而获得了自我。
在我们的访谈中,加藤直接对那些将性别常规和刻板印象看作很严肃的问题,并将它们变成个人问题的亚洲(裔)女性音乐家表达了不屑。当我问起与亚洲(裔)音乐家刻板印象相关的问题时,她说:
我不觉得职业世界中存在这类刻板印象。在学生的世界里,的确有与“典型的亚洲(裔)女孩”挂钩的形象,但我已经没再遇到过让我感觉 [刻板印象会对我产生影响] 的情形了。说实话,我觉得自己跟那些担心这类问题的人不是同一个水平的。我觉得,如果你担心观众会怎么看你,那么你对音乐还是不够重视,真的……至于我自己,反正我都不符合一个典型的亚裔女人形象了,所以我也不觉得其他人会对我有这样的期待。
除了有意识地跟美国的性别化和种族化刻板印象撇清关系之外,加藤还对日本的性别典范大加批判,在她看来,那样的性别典范指定女性音乐家为性对象,而不是艺术家。当我在对话结尾问她有何需要补充的想法时,她是这样回应的:
你知道,日本音乐家,尤其是女性,看起来都十分正式整洁。女人都会带有某种特定的魅力……几年前,我在纪伊国屋 [曼哈顿的一家日本书店] 看到了一本由某位日本音乐评论家所写的日文书。那是一本日本音乐家的传略合辑。我在翻书的时候看到某个部分讲到了 [知名日本钢琴家] 中村绂子,全是赞美的话。但讲的是她的样貌!比如,她的眼睛圆圆的,十分可爱,像这样的东西!这跟她的作品有什么狗屁关系呢?在描述这个与我年纪相当的女人时——她当然很可爱——还有一点,书里说她戴粉色围巾很好看,行为举止纯真动人,诸如此类……然后,我看到内田光子的部分,这本书完全是在贬损她,说她为了显得聪明,抛出一些高高在上的想法,让听众困惑之类的……我看了头两个介绍后就完全不想再看了……我认为,在日本,人们会期望演奏者长得……美,演奏者得是一个常人高攀不起的美人……我觉得这些期望一直延伸到钢琴老师身上。即便你不表演,即便你只是钢琴老师,人们仍指望你长得漂亮。
因此,即便加藤很明显地远离了那些她不相信其存在的女性气质典范,但她的评论表明了围绕性别的形象和常规的确会影响音乐家的生活,不管他们是否接受这些常规的存在。
题图为钢琴家王羽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