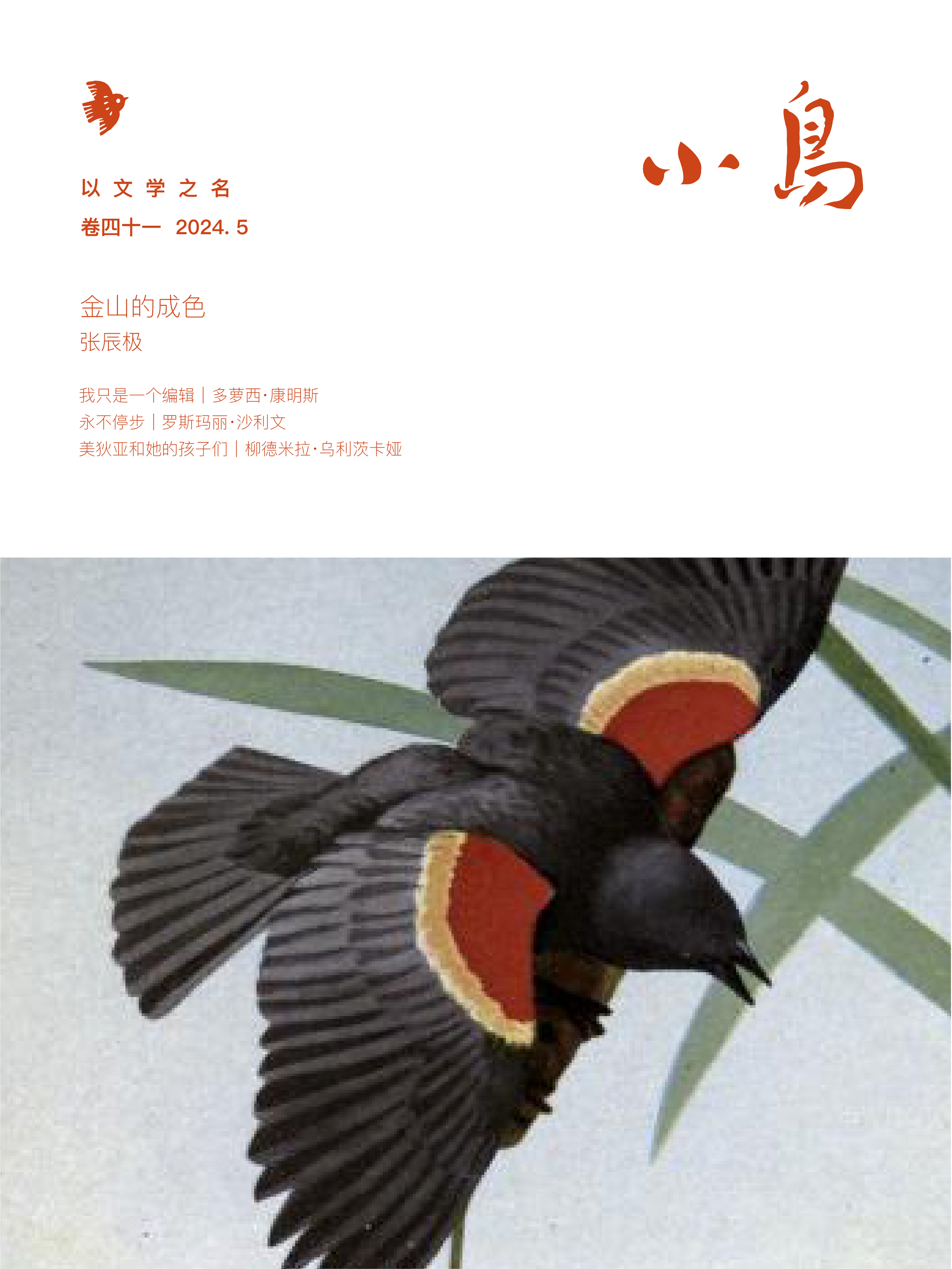这本书不仅是一个儿子向他杰出的父母表达敬意,更揭示了迷人生活中隐藏的角落。它并不感伤,慷慨又充满智慧。
- 胡安·加夫列尔·巴斯克斯
2014 年 3 月,与阿尔茨海默病斗争多年的加西亚·马尔克斯感冒了,妻子梅塞德斯·巴尔恰却预感最终结局将到来:“我们过不去这一关了。”死亡如约而至,作家于 4 月 17 日去世。2020 年 8 月 15 日,梅塞德斯·巴尔恰去世。
长子罗德里戈·加西亚决定写点什么纪念父母,当作最后的告别。当父母如行星般消逝,他会哀伤,却更加理解父母面对生活与死亡时的姿态:晚年时父亲就算失忆也不忘偶尔跟身边人逗趣;母亲温柔坚强一如从前,妥帖地处理丈夫的后事,但绝不承认自己是“遗孀”;即使身份再特殊,他们一家也从未要求过特权。
以下经“新经典”授权发布,节选自《一次告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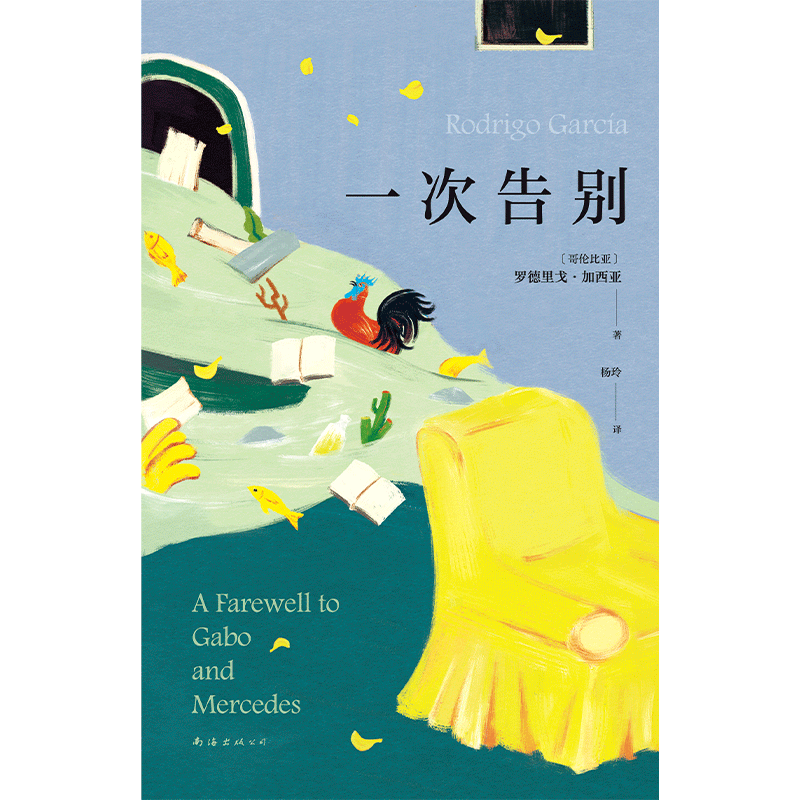
陆续有朋友从或远或近的地方赶来。家中的场景就像一场鸡尾酒会,一场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地提供饮品和茶点的守灵活动。母亲成了大家关注的中心,她同大家谈笑,嘘寒问暖,谈天说地,不知疲倦。有一些我以前听说过但从未见过的人,都是最近这些年我搬到洛杉矶后父亲结交的朋友。这样一群人充分反映出父亲的志趣所在:各种年龄、职业、社会阶层。母亲会私下里分批接待一些来访的客人,这其中还包含两位前总统。尽管她沉浸在悲痛之中,而且或许已经精疲力竭,但依然殷勤周到,颇有耐心。只有一两位客人走后,她疾言厉色,语气略带苦涩和讽刺。她无法原谅那些在父亲失去创作能力后就断了联系,甚至对她连声问候都不再有的人。她那份黑名单很短,但如果谁被列在上面,只能自求多福了。
还有一次,弟弟听说一所知名大学的校长在门外等候。门开后,一位男士走上前来,发表了一通流畅却有些生硬的赞扬之辞——有点像政治演说,之后给了弟弟一个正式的拥抱,没有再多说一句话,便一去不回头了。
父亲的一个弟弟带着夫人来了,同来的还有父亲那边我的一位堂姐,而我有近三十年都没有见过这位堂姐了。她在卡塔赫纳长大,现住在缅因州的一个小镇上,嫁给了一个当地人。她讲起了如何成功地使当地文化适应了自己的生活,而不是自己去适应文化,有趣极了。她的故事让我不由得想起父亲的家族对奇闻逸事的迷恋,对美化周围事物的热衷,还有对夸张的青睐。要知道,你得吸引听众,不能放他们走开。一个好故事永远能超越真理。一个好故事就是真理。
前往美术宫的途中,我拜托一位朋友在我们下车后穿过大厅时帮我拿着骨灰盒。我不愿被记者拍到捧着骨灰盒的样子,因为我觉得那样的情景太过私密,不该出现在新闻上。
我们下车后重新聚在一起,跟随着美术宫的负责人走上一级级台阶,穿过长廊,来到一扇门前。走过这扇门,主大厅有些意外地映入眼帘。我也说不清自己期待的是什么,但眼前的情景确实让我浑身一凛。宽敞的高台上摆放着父亲的骨灰盒,四周摆满了黄玫瑰。大厅的两侧都有很大一片区域摆放着一排排座椅,是为来宾准备的。骨灰盒正对的看台上则聚集了百余位摄影师、摄像师和记者。我们在左侧第一排坐下来,周围是早早赶来这里的各界要人和朋友。显然,大家期待我们先站在骨灰盒旁边守护片刻。于是,我和弟弟陪伴母亲走上前去,停在了他们为我们指定的位置。闪光灯一顿狂轰滥炸,使得这个时刻匪夷所思,超越了现实。我不禁想到,此刻我们认识的人可能正在世界各地看着我们。站在那里的似乎已经不是我了,只是某个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的家伙,一个从三岁到五十三岁都尽可能低调的家伙。我们身后,弟弟的家人默默守候,再后面是我的妻子和女儿们。其中一个女儿有社交恐惧,她后来告诉我,当时的经历痛苦极了,几乎让她无法承受。我很心痛。对于正值青春期的她来说,在那样私密的时刻、那样悲痛的氛围之中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这样的经历无疑是一种折磨。
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我们一直坐在那里,静静地看成千上万的人前来吊唁,他们中大部分人在雨中一直站了几个小时,只为走进来向父亲表达哀思。他们在陈放骨灰盒的台子前放上鲜花、纪念的物件、圣像又或是圣牌。很多人留下了他们自己的书,写下了表达悼念或爱意的纸条,一些人称呼父亲为大师,但大部分人则称他为加博,或者加比托。这一切清楚地提醒着我们,父亲不只属于我们,也属于很多人。
我飞回了洛杉矶,准备在那里待上几日。不久前,即使父亲已经认不出我是谁,每次我要离开,他都会抱怨:“不,别走啊,伙计,为什么要走呢?留下来。别丢下我。”每当这时,我都如鲠在喉,就像把一个满脸泪水的孩子留在幼儿园里,只不过没说“这一切都是为你好”这句不知是否真心的借口。
到家后我发现有几百封吊唁的信件正等着我。在眼前这个现实中,这些信仿佛在谈论一件久远的事情。我把它们留待以后处理,到那时它们或许会(事实上也确实如此)成为我莫大的慰藉。在一次来电中,母亲告诉我,一位男士出现在我家门前,自称为波鲁阿先生。母亲以为他是波鲁阿家族的某个人,墨西哥最早的出版社便是这个家族的产业。尽管并没有认出他是谁,她还是在客厅接待了他。而他表现得十分友善、热情,问起父亲的秘书,又问起了我和弟弟,他都能叫得上我们的名字,接着还分享了他对我父亲的记忆。父亲的秘书走了进来,他立刻从座椅上弹起来,热情地拥抱她。她则不好意思承认自己并不记得他。波鲁阿先生又坐下来,继而解释说他是从另一个城市开车来的,车子抛锚了,因为坚持想来表达哀思,所以请求一个朋友把他带到了这里,朋友就在外面等候。他问母亲是否能借给他大概二百美元去修车。母亲拿了现金给他,这个人便走了,从此再无音信。后来,我们才知道他原来是个远近闻名的骗子。得知此事,母亲哈哈大笑。
除了吊唁的信件,朋友们给我寄来了父亲去世当天世界各地报纸的头版。我因此陷入网络的无底洞之中,一口气查阅了各国、各地方的当天头版新闻,发现都有相关的报道。我尽可能多地阅读各种版本,每份报纸都有所侧重,强调了父亲生平或成就的不同方面。我再一次努力将报纸上报道的这个人同自己最后几个星期陪伴的那个人联系起来,那个病魔缠身、垂死挣扎、最终变成盒子里的一抔骨灰的人,又同我童年时代的父亲联系在一起,还有最终简直成了我的孩子或是弟弟的孩子的父亲联系在一起。我仔细读了自己对最后时日的记录,不知道是否应该汇总起来写成故事。父亲和母亲一样,始终坚信我们的家庭生活属于绝对的隐私。从我们还是孩子起,他们便一次又一次要求我们服从这条规定。但如今我们已经不是孩子了。或许是老小孩,但不是孩子了。
父亲曾抱怨说,死亡有一点让他最不喜欢,即这是人生中唯一他没有机会书写的一面。所有他经历的、见证的以及思考的,都被他写进了书里,成了被他虚构或是加密的内容。“如果你不写作也能活着,就别写作。”他常常这样说。我恰恰就属于不写点什么就活不下去的那类人,所以我相信他能原谅我。他的另外一句表达也定会被我带进坟墓:“没有什么比写得好的东西更珍贵了。”这一句尤其让我觉得振聋发聩,因为我清楚地知道,我写的关于他最后岁月的任何东西一定都能轻而易举地被发表,不管写得怎么样。在内心深处,我知道自己一定会写下这段回忆,通过某种方式将它呈现出来。如果我这样做了,我会援引父亲对我们说的另一句话作为依据:“等我死了,你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吧。”
我再次回到墨西哥,陪母亲一段日子,也见见几位之前没能赶来的巴塞罗那朋友。我和这些朋友自一九六八年起就亲密无间,而且追思仪式已经结束,整座房子里只有我们几人,我们得以相对安静惬意地聚一聚,不过此时父亲的离去也愈发明显。这两位朋友都是心理学家,属于父亲最信任的朋友之列。父亲从来不做心理治疗,他的理由很充分,声称打字机就是自己的心理医生。很可能他是怕心理治疗会盗取他的创造力,哪怕只那么一丁点,又或者那种赤裸裸地暴露在别人面前的感觉让他不舒服,谁也无法得知究竟为什么。有时,他确实鼓励我们跟亲近的朋友或家人聊一聊自己的焦虑,因为如果不这样做,最后我们很可能还得付钱去找专业人士来倾听。
这次回墨西哥,我最想做的就是跟父亲聊一聊他的死亡和身后之事。我久久地站在他那位于花园深处的书房中,他的骨灰就锁在这儿的一个小柜子里,这里和家中的其他地方一样,一切已经缓慢却无情地渐渐恢复正常。母亲再也没有来过书房,她或许永远也不会来了。父亲去世时所在的那个房间又恢复了往日的样子,但在我女儿、侄女和侄子们的口中,它是一间要避开的房间。我决定睡在那里,以便让它恢复作为客房的正常功能。不管怎样,我度过了一个平常的夜晚。
我乘上清晨的航班飞回洛杉矶,精疲力竭。这已经是三个星期内我第八次飞回或者飞离墨西哥城了。当飞机缓缓地驶入跑道时,一种清澈的顿悟感向我袭来,我意识到父亲在这个世界上的精彩一生已经结束了。起飞时,悲伤涌上心头,但与此同时,飞机引擎强有力的推力突然消失,意想不到的空虚感却神奇地让我为之一振。随着起落架被收起,机身微微向左倾斜,逆着朝阳,东方的两座火山隐约可见:一座是波波卡特佩特火山,它的形成比文字的诞生还要早上几十万年;另一座是伊斯塔西瓦特尔火山,一座活火山。我们上升到一万英尺的高度时,耳边响起了犹如微弱闹铃般的声音。我将座椅向后倾斜,向周围看了看。坐在我旁边的女士正在手机上读《百年孤独》。
题图为作者父母的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