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一下,这是 1936 年的夏天,你在德国度蜜月。天空阳光灿烂,周围的人们十分友善——感觉生活是美好的。你沿莱茵兰驱车南下,欣赏沿途的城堡和葡萄园,望着满载货物的庞大驳船逆莱茵河水而上,不由为眼前的景象着迷。你来到法兰克福,停下有显著英国标志的汽车,准备饱览这座城市里那些欧洲中世纪建筑瑰宝。
忽然,一个犹太人模样的女人不知打哪儿冒出,朝你走来。只见她满脸焦虑神色,手拉一个脚穿厚底鞋的十几岁跛足女孩。你听到的有关纳粹的种种令人不安的传言,都集中表现在这位绝望母亲的脸上——对犹太人的迫害、滥用安乐死、酷刑、未经审判的监禁。她看到了你汽车上的英国标志,恳求你把她女儿带去英国。你该怎么办?你会惊慌失措地转身走开吗?你会表示同情后告诉她,你真的无能为力吗?抑或你会把她的女儿带走,为她提供安全庇护?
这是个真实的故事,是我从一对英国夫妇的一个女儿那里首次听到的。那是一个炎热的夏日午后,我们坐在她位于剑桥的宁静花园里啜饮柠檬水。爱丽丝·弗利特(Alice Fleet)让我看了一张照片,照片中,格蕾塔(Greta)满脸笑容,怀抱着还是婴儿的爱丽丝。这是那个非凡旅行故事的快乐结局。我试着设身处地替她父母考虑,假如我处在相同情况下,会做出什么反应。仅仅用了几秒钟,我便得出结论:不论那个女人面临的严酷处境多么让人揪心,也不论纳粹多么令人深恶痛绝,我几乎肯定会选择第二种解决方式。单凭想象,要判断自己在这种情境下的反应并不难,但是,在真实情境下,我们真的确定自己会作出何种反应吗?对于眼前活生生的事实,我们该如何解释?这本书描述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发生在德国的事情。本书基于外国人的第一手记叙,从身心两方面,都营造出亲临希特勒(Adolf Hitler)时代的德国旅行的感受。作者查找到大量以前未发表过的日记和信件,生动地展示出纳粹德国的全新形象,希望能优化甚至挑战读者现有的看法。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生的人们来说,要想超然地看待这段时期是不可能的。纳粹暴行的阴影实在太浓重,绝对不可能淡化或置之脑后。但是,如果没有受到战后回顾的影响,当时在第三帝国旅行会是什么感觉呢?假如不了解当时的真实情况,要把握纳粹主义的本质,想不受宣传或大屠杀预言的影响,还会容易吗?这种旅行经历是改变了还是仅仅强化了固有的偏见?
对这些问题以及许多其他方面问题的讨论,都参考了诸多到访者的个人证词。这些人中包括:查尔斯·林白(Charles Lindbergh)、戴维·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帕蒂亚拉的王公(Maharaja of Patiala)、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保加利亚国王,以及塞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等名流。还有普通的旅行者,从遵行和平主义的贵格会信徒到犹太童子军,从非洲裔美国学者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伍老兵。也不乏学生、政治家、音乐家、外交官、小学生、共产主义者、诗人、新闻记者、法西斯主义者、艺术家,当然还有游客——他们中的许多人年复一年到纳粹德国度假。这些人都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到访者中还有中国学者、奥林匹克运动会选手和挪威一位支持纳粹的诺贝尔奖得主。五花八门的旅行者得到的印象和给出的反应自然有很大差异,而且往往相互矛盾,但综合在一起,却构成了一幅非同寻常的希特勒时代德国的三维图像。
许多人访问第三帝国是出于职业原因,另一些人只是去享受一个愉快的假期。然而,更多人的动机是长久以来对德国文化的热爱、家庭渊源或往往只是好奇心。在其他地方民主遭遇失败、失业泛滥成灾的背景下,右翼支持者希望从“成功的”独裁统治中吸取经验,回国复制,而追随卡莱尔式英雄崇拜的人则渴望看到真正的超人行动。但是无论旅行者的政治态度或背景的差异有多大,有一个主题几乎是一致的——享受德国自然美景的乐趣。人们不必是亲纳粹者,也会赞叹这里乡村的绿茵、岸边满是葡萄园的河流和一望无际的果园。另外,这里原汁原味的中世纪城镇、整洁的村庄、干净的酒店、友好的人民和有益健康的廉价食品都十分诱人,更不用说还有瓦格纳(Wilhelm Richard Wagner)的音乐、窗槛花箱、泡沫丰富的杯装啤酒。这些因素年复一年地吸引度假者来此休闲,尽管该国政权在许多方面令人毛骨悚然,致使出行者的国家施加了越来越严格的审查。当然,那些年发生的人类悲剧仍然是头等重要的大事,但是在诸多日记和信件中,汉堡、德累斯顿、法兰克福、慕尼黑等城市在战前的非凡魅力仍然十分突出,这愈发显出德国因希特勒而遭受了多大的损失——整个世界也因此蒙受了多大的损失。
在游客人数方面,美英两国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国家。尽管爆发了大规模战争,但英国公众大部分在感情上仍比较亲近德国人——认为后者在各种方面都比法国人更令人满意。美国驻德国大使的女儿玛莎·多德(Martha Dodd)曾表示:“与法国人不同的是,德国人不是小偷,他们并不自私,也不急躁、冷酷或强硬。”在英国,越来越多的人对《凡尔赛条约》(Treaty of Versailles)感到不安,与如今许多人认可的一样,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对德国人特别不利的不公平协议。他们此时当然应该向这个前敌国表示支持和友好。此外,许多英国人认为,他们自己的国家有很多方面该向新德国学习。因此,尽管人们意识到纳粹是野蛮的,而且这一意识日益扩展深化,但英国人继续前往德国做生意、享受乐趣。美国记者韦斯特布鲁克·佩格勒(Westbrook Pegler)在 1936 年的一篇报道中坦言,英国“有一种乐观的错觉,认为纳粹就像个巨人。他们目前的容忍并非接受其野蛮倾向,而是希望通过鼓励而激发出他较好的本性,让他未来有可能变得彬彬有礼”。这个看法很有道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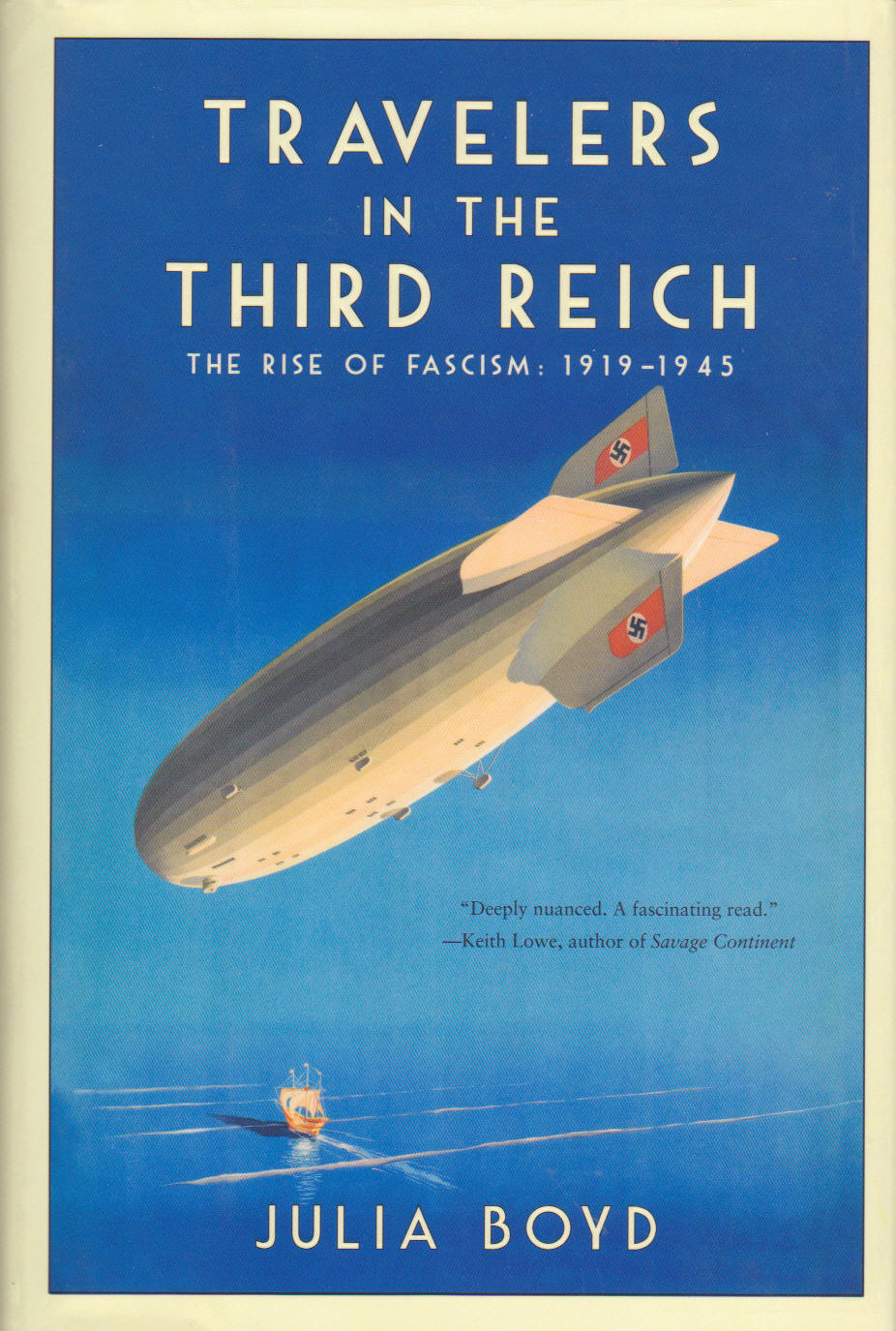
截至 1937 年,美国每年到第三帝国旅游的人数达到五十万。绝大多数人的意图是充分享受在欧洲的旅行,把政治看成烦人的干扰因素,索性不管不顾。做到这一点十分容易,因为德国人在尽最大努力吸引外国游客——特别是英美两国游客。在种族问题上,美国游客尤其不愿过分追究纳粹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在迫害犹太人问题上作出贬损评论,会引发人们对该问题与美国对待黑人群体的手段进行对比。普通美国人很少有人情愿探索这一话题。大多数游客回想到战前在德国度假的经历,真心认为他们无法预知纳粹的真实意图。诚然,在前往莱茵兰或巴伐利亚等热门度假景点的普通游客看来,纳粹罪行的明显证据十分有限。当然,外国人注意到大批身穿制服的士兵,他们高举旗帜,呼喊口号,正步游行,但那只不过是德国人在表现对自己国家的忠诚,不是吗?旅行者往往对到处充斥的反犹太主义告示感到不满。但是,不管犹太人的待遇多么令人不快,许多外国人认为这属于别国的内部事务,不该由自己操心。此外,他们自己往往也反对犹太人——在许多人看来,犹太人有必要为自己辩解。对于报纸上对德意志帝国的攻击,他们认为这种情况言过其实,毕竟人人都知道,记者从来嗜好小题大做,为的是引起轰动。人们还记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初几周,报纸上报道的德国暴行后来被证明是虚假的。正如路易斯·麦克尼斯(Louis MacNeice)所言:但是,我们心里认为,这不关我们的事,游客们想看到的无非是,经过加工后呈现在浏览者面前的现状。
我们认为报纸就像一只云雀,为其政党政治唱高调,还搞无端谩骂。虽然以上大部分情况对一般游客来说都是真实的,但那些出于职业原因或是专门为了探知新德国而去第三帝国旅行的人们是怎么想的呢?在纳粹统治的最初几个月中,许多外国人发现很难确定该相信什么。希特勒是个怪物还是个奇迹?虽然一些访客仍然心怀疑虑,但证据表明,随着岁月的流逝,多数人甚至在踏上这个国家之前就已经得出了结论。他们去德国的意图是确认自己原先的预期,而不是挑战自己的预想(与他们对待苏联的态度相同)。令人惊讶的是,似乎很少有人因旅行的直接结果而改变初衷。右翼人士发现那里的人民勤劳而自信,承受着《凡尔赛条约》的不公平对待,与此同时还保护了欧洲其他国家免受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影响。在他们看来,希特勒不仅是一位鼓舞人心的领袖,还是个谦虚而绝对真诚的人,他致力于和平,有无数爱国的狂热追随者。相反,左翼人士却认为那是一个执行种族主义罪恶政策的政权,残酷而具有压迫性,通过使用酷刑和迫害来恐吓公民。但是,在某个方面,双方的看法一致:受到千百万人崇拜的希特勒完全掌控了这个国家。
学生构成了一个尤为奇特的团体。即使在如此令人不快的政权背景下,德国的文化成分似乎仍被视为青少年成长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是,很难解释为何直到战争爆发前,众多英美青少年仍被送往纳粹德国求学。鄙视纳粹的父母嘲笑德国“文化”粗野,但为孩子收拾行装送他们去德国长住时,却不感到丝毫内疚。去德国的年轻人则认为,尽管与最初的想象并非完全相同,但这是一次非凡的经历。众多学生和其他许多从德国归来的人曾努力警告自己的家人和朋友,那里有潜在的危险。但是公众对此表现冷漠,或者对纳粹的“成就”表示赞同,还心怀对啤酒园和紧身连衣裙的愉快回忆。最重要的是,人们对再打一场战争有着深切的恐惧,于是,他们对种种警告往往充耳不闻。
对战争的恐惧,是影响许多外国人看清德意志帝国真实面目至关重要的因素,这一点在退伍军人身上尤为明显。他们渴望相信希特勒确实是个和平主义者,相信纳粹革命会很快平息,最终德国会成为文明国家,相信德国公民不断作出的承诺:德国的确是善意的。结果导致他们中许多人经常去新德国提供自己的支持。考虑到他们的儿子到头来仍有可能不得不承受与他们相同的梦魇,他们的这种态度不难理解。但也可能是纳粹强调的规则、纪律和效率,对军人有天然的诱惑力。
作为第三帝国的一个突出特征,壮观的火炬游行和异教形式的庆典自然会经常被外国人提到。有些人对此表示反感,但另外一些人认为,它们恰恰表现出德国重新找回了自信。在许多人看来,纳粹主义似乎取代基督教而成了国教。雅利安人至上观加强了血与土的种族意识形态,如今成了人民的福音,元首就是他们的救世主。其实,就连不太支持纳粹的许多外国人,在诸如纽伦堡集会或大规模火炬游行的盛大活动中,都会不由自主地被此类活动的强烈情绪感染。谁也不及纳粹更了解如何操纵大批人群的情绪,许多外国人常常吃惊地发觉,自己并不能免疫。
所有前往德意志帝国的旅行者,无论他们是什么人,也不论他们的目的是什么,都不断地接触到各种形式的宣传:《凡尔赛条约》是邪恶的,纳粹革命成就惊人,希特勒为和平作出了贡献,德国需要保卫自己、需要夺回其殖民地、需要向东方扩张,等等。从纳粹最持久的宣传内容是“布尔什维克和犹太人的威胁”,他们最初确信这种宣传会说服美国和英国与之联手。他们不停向外国人宣讲,红色部落欲横扫整个欧洲大陆、摧毁文明,只有德国挡在它们面前。许多人听腻了,便不再倾听。试图清晰地界定纳粹主义与布尔什维克主义之间的差别,的确让比较有思想的旅行者感到困惑。他们当然知道纳粹是共产党的死敌,但两者各自的目标和手段究竟有何不同呢?在非专业研究人士看来,希特勒剥夺所有人的个人自由,控制国家和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使用酷刑和象征性的审判,部署强大的秘密警察部队,推行无耻的宣传,这至少从表面上看与斯大林(Joseph Stalin)非常类似。南希·米特福德(Nancy Mitford)曾轻描淡写地提道:“共产党跟纳粹之间从来插不进一根针。如果你不是工人,共产党会折磨死你。如果你不是德国人,纳粹会折磨你到死。贵族倾向于纳粹,而犹太人则偏爱布尔什维克。”
到了 1937 年,反纳粹大合唱的声音变得更加洪亮,除了一些明显的例外,记者和外交官成了主角。这些人在整个德国游历,努力描绘准确的画面,试图提请人们关注纳粹的暴行。但是他们的报告遭到反复编辑或删改,或者被认为过于夸大。就记者而言,他们中的许多人常年在德国工作,工作环境让他们精神非常紧张,他们知道自己随时可能因捏造的指控而被开除或遭逮捕。记者们的旅行札记,与短期访问者在日记和信件中经常表现出的愉快描述大相径庭,后者倾向于相信事情完全不像新闻记者说的那么糟糕。消息灵通的居民与普通旅游者对一个国家的印象自然不同,但在纳粹德国,这两种观点的对比尤其显著。
从战后的角度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访德国的旅行者面对的问题,很容易被认为非黑即白。希特勒和纳粹是邪恶的,那些无法理解的人不是愚蠢,就是法西斯。这本书并未对外国人在纳粹德国的游历进行全面研究,但通过许多旅客当时对所见所闻的记叙,本书试图展示,要想恰当理解纳粹德国,并不像很多人认为的那么简单。这些旅行者的故事让人感到不安、荒唐、动人,从家长里短到国族悲欢,为人们洞察第三帝国的复杂属性、内在悖论及其最终毁灭提供了新的角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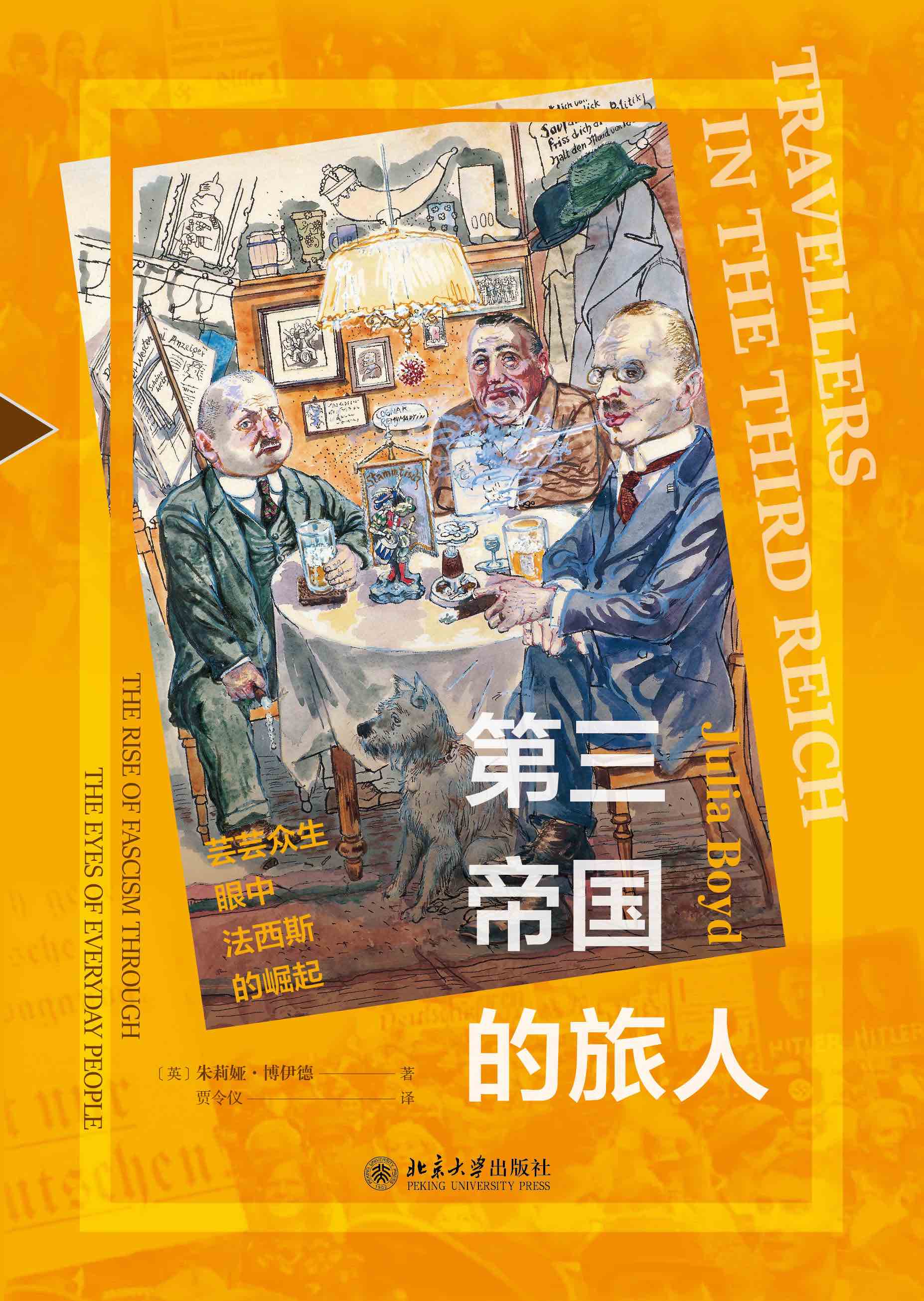
本文摘自《第三帝国的旅人》,注释从略
[英]朱莉娅·博伊德
贾令仪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0 年 2 月
题图来自 SeM/UIG via Getty Imag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