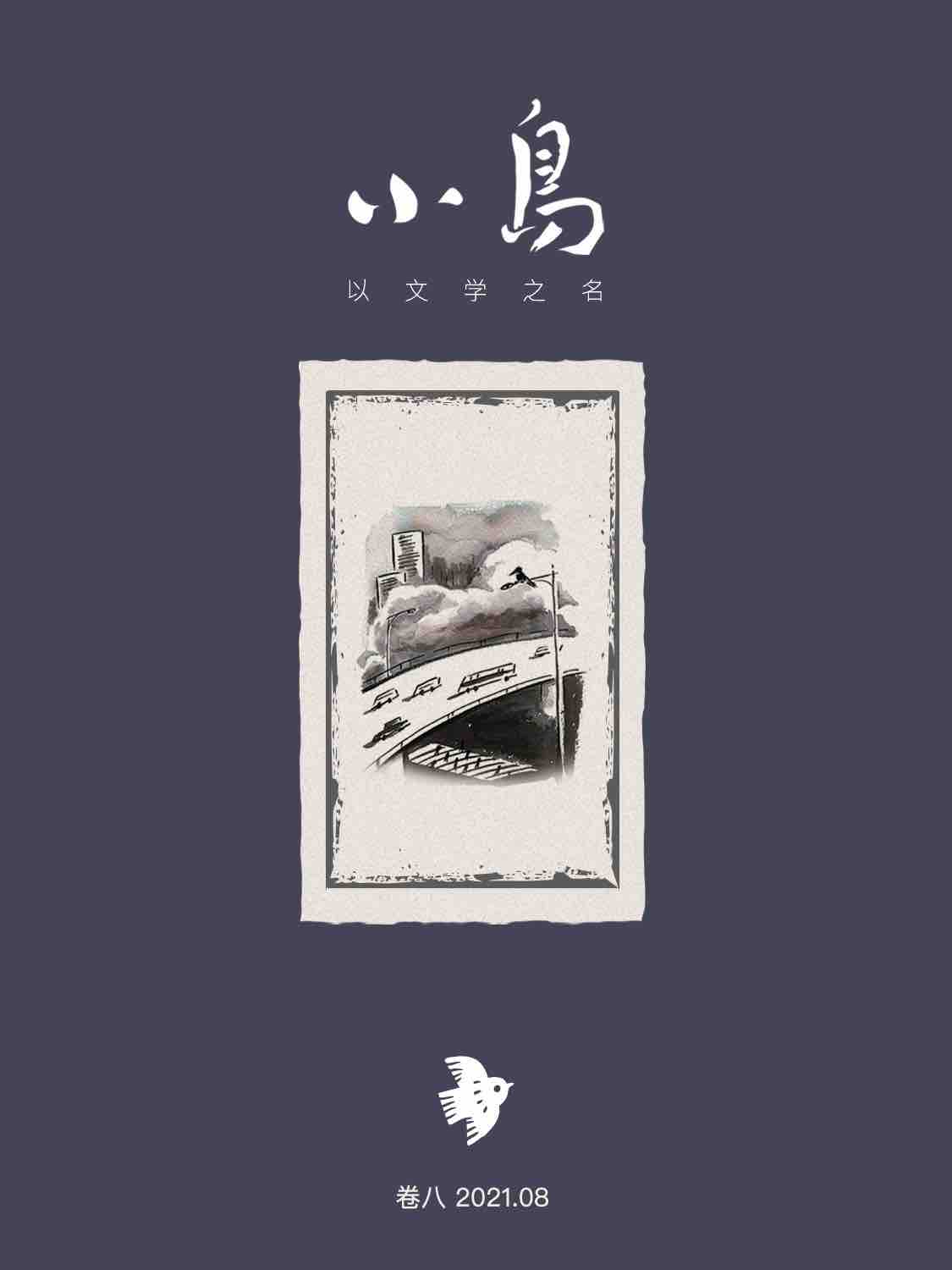在北京的一个普通居民小区里,一场由市政府出资,国家公共服务机构主办的相亲活动正在举行。在 80 平米的长方形会议厅里,40 位女生面对面站成两排,一些穿着志愿者红背心的工作人员将塑料红玫瑰一人一支,分发给站在周围的 40 位男生。另外两位工作人员,将大门关起,上锁。他们守在门口,防止男生在最后的环节临阵脱逃。
背景音乐循环着“今天你要嫁给我。”这是游戏和交谈环节过后的表白时间。身穿三件套灰色西装的主持人站在台上俯视全场,鼓励男生们勇敢表白:“各位男嘉宾,勇敢一点!请用你们手中的玫瑰表达对心仪女嘉宾的爱意!把玫瑰递到她手中,然后,站在她身后。”
我看到岩末已经站在一位之前相谈甚欢的女生身后,女生手里握着玫瑰。一些男嘉宾表白的努力失败了,女生拒绝接受玫瑰,他们继续手持玫瑰,在两排女生站成的围墙之外转圈。
俊峰靠在镜墙上,手中的玫瑰被捻来捻去。他并没有要加入的意思。我问他:“没有看到合适的女生吗?”他笑了一下:“这样的仪式有什么意义?”和俊峰一样的男生还有十几个,有胖有瘦,有高有矮,他们或站或坐,等在角落里。
这场活动的主办者是这家服务机构的主任,一位 40 岁的已婚男性。此时,他在场地里绕着圈催促男嘉宾上前表白:“主动点,男生要主动点呀!”他费力地把一个推到前边,又去拉另一个,这时,第一个已经又退回原地。他们不想表白,但身后紧闭的大门让他们无法逃脱这个选择的环节。
岩末和女生成功牵手,女生获得了一只一米高的玩具熊作为奖励。“牵手”是相亲现场配对成功的专用名词,和他们一样的还有其他 6 对男女。活动结束后,所有参与者都被推到台上合照,这标志着活动的圆满完成。
与商业性的相亲活动不同,在国家公共服务机构主办的相亲活动中,你看不到参与者华丽的着装,精心修饰的发型,填有个人经济和住房条件的表格;也看不到高档的会所,精致的下午茶。在这里,有人像岩末一样享受和异性互动的过程,有人像俊峰一样对程式化的亲密感到厌烦。但他们都是这个相亲场忠实的参与者。活动主办方告诉我,关门是为了挡住那些逃避合照的人,合照是举办活动,清点人数的证明,需要存档。
01
用风险和焦虑滋养的相亲机制
2016 年,我第一次作为研究者进入国家机构组织的相亲活动调研。自此之后,我在获得主办方允许的情况下,在不同时段,以旁观者、主办方志愿者、相亲者的身份在北京和上海参与了上百场市政府出资、国家公共服务机构——妇联、工会、共青团——筹办的相亲活动。市政府资金以购买公共服务的方式按年划拨给后者。
每进入一个新机构筹办的相亲活动,我都会凑到主办人员身边,问一句:“国家为什么要组织相亲呢?”对方的答案五花八门,且随着年代推移,经历了由“自发到自觉”的变化。与此同时,经年累积,我脑海中,对于国家机构组织相亲这件事,从起初的没有答案到如今时时徘徊着数个解释。
2016 年,“公园相亲”已经兴盛了好几年。在北京的中山公园、天坛公园,上海的人民公园、鲁迅公园,南京的玄武湖公园等等,相亲人群都呈现出如招聘市场般繁荣的景象。国际美妆品牌 SK-II 还以人民公园为场景制作了一部女性主义视频《她最后去了相亲角》,作为其全球营销活动“#改写命运”的一部分。就连我的许多美国同学都知道相亲角这种中国特色集会活动。
相亲角是家长的主场。单身男女的简历被挂在架子上,贴在雨伞上,印在扇子上。家长们走着,逛着,聊着,探听着对方的住房距离市中心的距离,标榜着自己孩子的身体健康。有时,在谈判失败后,你还能偶尔听到一句家长烦躁的咒骂,“独生子女害死人呀!还真把自己孩子当宝了。”或是,对自己教育失败的自责,“我就是从小对他管得太严了,博士毕业还没谈过恋爱。”
与此同时,政府出资,公共服务机构筹办的相亲活动还方兴未艾。不论在北京还是上海,想找到一场活动观摩尚属不易。
那年夏天,我在北京金融街附近参加一场相亲。那是我第一次问主办方为什么要做相亲活动。对方是一位 40 多岁的女性领导,听到问题迟疑了一下,“现在男女比例失调很严重,有 3000 万光棍,北京有这么多农民工,如果他们长期单身,会危害社会安全。”
当时,对于这个教科书般的标准回答,我不知道是喜是悲,喜的是我可以沿着人类学前辈的论述,轻松地论断这是对于农村男性、流动人口的异化,是国家通过建构家庭来促进社会和谐的行动;悲的是这种从国家《人口发展报告》中摘录的标准答案和那天的相亲参与者显得格格不入。
那场活动的男性参与者有不少是附近金融机构和政府机关的职员,他们通过所在单位的工会报名,获得入场券。没有看到符合农民工形象的男性出现,我多嘴问了一句,“参加活动的农民工一般从什么渠道报名呢?”那位领导又迟疑一下,“我们办的是针对高素质人群的相亲,还真没有见过农民工……”
那一年,“性别比例失调,光棍危险”是公共服务机构对于为何要组织相亲给出的主流答案。理念中的服务对象是蕴藏着危险可能性的农民工,而现实中的服务对象是穿着衬衫西裤或 Polo 衫牛仔裤的职员、市民。
那时,我直觉性的判断是这些公共机构的人员可能也不太清楚举办相亲活动的社会学依据是什么。一些主办方会更直白地告诉我,“我们经费少,相亲简单呀,不需要什么资源,有人就行了!”或者,“你看过《非诚勿扰》吧,现在相亲很流行呀。”
2017 年,我试探性地把相亲研究扩展到上海,也正是在这一年,我日后调研的那家婚介所获得了上海市政府每年 100 万元的活动经费,用来举办“公益类”的相亲交友活动。这些活动的服务对象,除了普通上海青年市民以外,还包括军人、残疾人、老年人。那时,这家婚介所属的事业单位还没有完成从自收自支到政府全额拨款的改制。因此,负责人还称“总经理”而不是日后的“主任”。
当我问到人民公园的相亲角前景如何时,总经理撇撇嘴,“你不知道,市政府每天在高处看着这些家长都头疼死了,想把他们赶走嘛也不好赶。”人民公园背后就是上海市政府、市发改委、市人大常委的所在地。如此想来,市政公务人员每天看着地面上,上百位中老年人的集会也的确头疼。与此同时,爸爸妈妈们向政府、妇联信访,要求政府帮助孩子找对象的也不在少数。
面对这些现象和诉求,这家婚介也真的为父母们开辟了专场。每月微信公众号上的活动通知都写着“不要再去人民公园啦,来 XX 聊天吧!”每个月,老父、老母们也真的会如约而至,把婚介所的活动区域挤得水泄不通。每次家长离场后,我和其他工作人员都要清理很久堆积如山的瓜子皮,散落各处的茶杯。
与此同时,人民公园的相亲角并没有被取缔,相反,它被管理者改造成一个旅游景点和城市地标。它作为一个旅游景点甚至出现在百度地图上和上海城市规划馆播出的城市宣传片里。时至今日,每日来到相亲角的中外游客络绎不绝,来调研的学生也络绎不绝。这个相亲角里每日来来往往的父母和他们对于政府的诉求成为国家公共服务机构论证“相亲难”和“相亲是市民需要”的有利证明。 每年申请政府资金时,“困难”和“需要”都成为相亲机构申请陈述中的关键词。
在她挂满锦旗的宽敞办公室里,总经理一边用手机给我展示以往的活动视频,一边很豪气地向我介绍了她设计并举办的“海陆空三位一体”相亲活动。“海陆空”指代相亲活动展开的场所。“海”是浦江游轮,“陆”是郊野公园或展览馆,“空”是“相亲航班”。总经理作为一位女企业家,与市里各个企业,例如东方明珠、浦江游轮、春秋航空,都有着良好联系。利用这些人脉资源,她成功地将相亲活动以一种相比于“相亲角”更“高大上”的模式重新带入城市的公共空间。
那一年,“性别比例失调,光棍危险”是公共服务机构对于为何要组织相亲给出的主流答案。
她让我看到,举办相亲不仅是为了创造婚姻,更是为城市创造“爱”的气氛。她所参办的一年一度,或一年两度的“上海万人相亲大会暨婚恋博览会”特别体现了这一理念。这一活动的历届主办方包括上海市民政局、市委宣传部、市妇联、共青团、总工会等等。它的主题“让爱见证,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改编自 2010 年上海世博会的主题“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自 2011 年起,每年为期两日的活动都有 8000-9000 名单身男女报名、参加。“海陆空”相亲套餐,市级相亲活动,政府拨款,公益转型都是相亲逐渐体制化的标志。
2019 年,我以工作人员的身份,来到北京和上海,进入隶属于国家公共服务组织的两家婚介机构, 开始正式的长期调研。此时,国家涉入相亲活动的必要性又有了新的解释 。
在北京的婚介所,主任谈到相亲时,“焦虑”是他的口头禅。这两个字用他的东北口音说出来,更有急迫感。当我和主任,两位红娘和一位情感咨询师坐在办公室的沙发上头脑风暴相亲活动时,他总是喜欢说:
“那些家长儿都非常焦虑,老来找我们,让帮着介绍,那些孩子,你别看他嘴上不说,其实也是非常焦虑,你看那个 XXX,在这儿相亲都快十年了,还找不到。他和父母因为这事儿也闹翻了,连家都不回。一个社会里有这么多焦虑,这么多代际冲突,肯定是有问题呀!家长也焦虑,孩子也焦虑,这两者还有冲突,咱们怎么能让这两种焦虑一致了,变成结婚的动力?”
相亲场上的种种情绪和关系,在这一年里被明确地命名为“焦虑”。这种心理状态本身成为诊断社会问题的症候,也成为合理化公共干预的证据。用主任更有使命感的话说是“必须拯救”。
在我调研的五年中,国家机构组织的公益类相亲活动在城市中迅猛增长。到 2019 年,就我所在的机构而言,活动的频率达到了每周一场,每场的参与人数在 50 人到 200 人不等。此外,各区的妇联、共青团、民主党派,还有国企、外企、事业单位的工会,都会按月或者按季度独立、或合作举办相亲交友活动。例如“七夕”这样的节日临近时,我的微信通常会被十多场相亲活动的消息轰炸,这还是把所有商业机构举办的相亲活动排除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