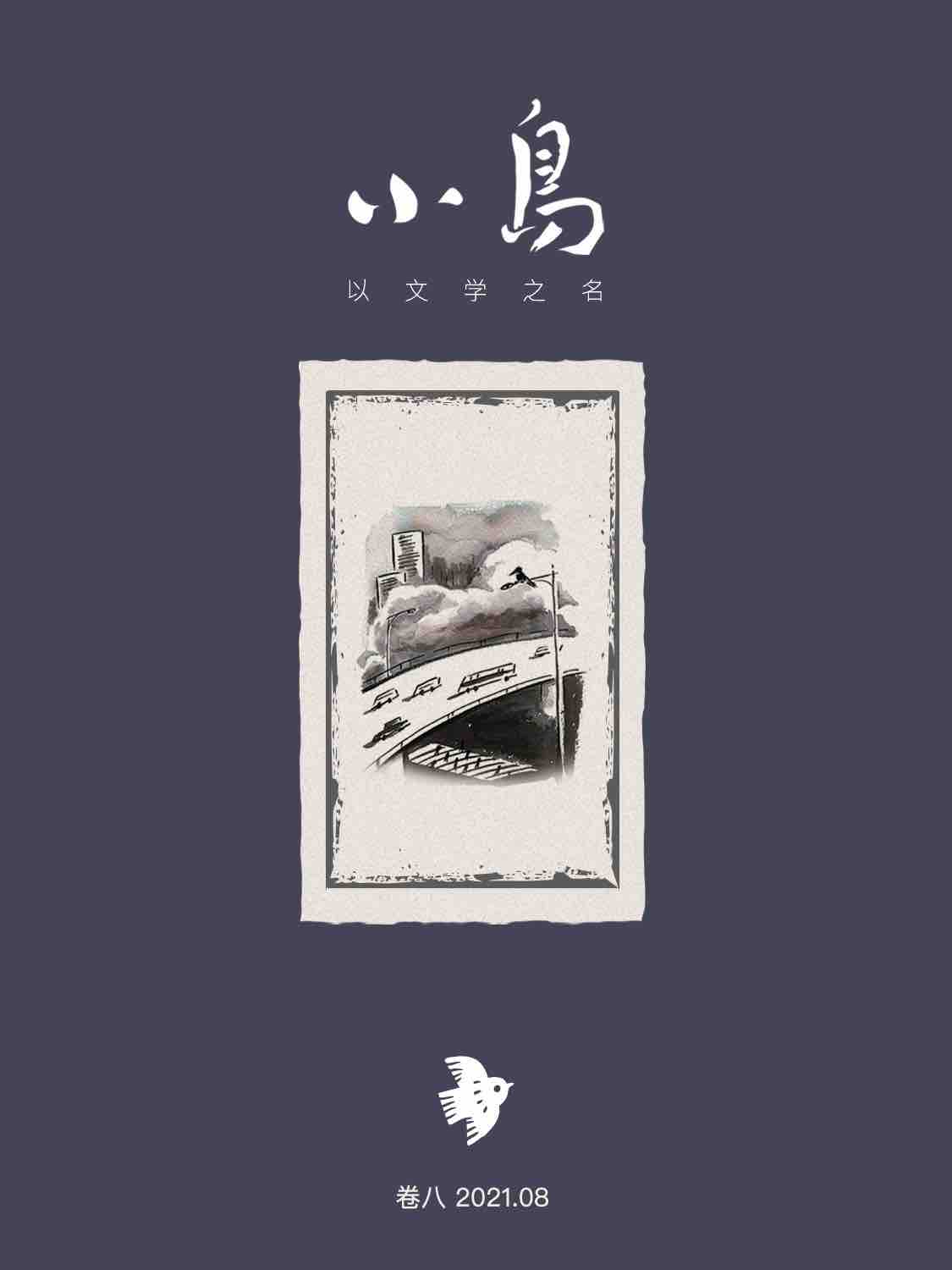01
前言
过去的 200 年间,阿富汗先后五次遭遇外敌干涉,好些世界强权与地区强国都曾试图侵略、占领、征服或控制这片土地。每次侵略,都让侵略者付出了沉重代价。奇怪的是,每一次干涉,仿佛都出自同样的原因;每一次外敌来犯,也都延续着一贯的套路——汹汹而来、悻悻而走,似乎都不知道前车之覆乃是后车之鉴。
1839 年,英国殖民者第一次侵入阿富汗。初次接触的回忆相当不堪。40 多年过后,同样的入侵者,犯下了几乎一模一样的错误。前辈的痛苦教训,后人却一点不曾汲取。又过了 40 年,英国人第三次踏进同一条河流。60 年后,苏联军队也在阿富汗栽了跟头。如今,阿富汗的土地上驻扎着美国及其盟友的军队。故事似乎一直在循环往复。
为什么大家都如此健忘呢?
由此,我想起了一段亲身经历。数年前,我有幸前往哈萨克斯坦宣传自己的作品。拙作内容关乎世界历史,我想通过伊斯兰的视角审视世事的变迁。所到之处,读者提出的问题无一例外都与阿富汗有关——这也难怪,我虽是美国公民,却在阿富汗出生和长大。我在哈萨克斯坦逗留期间,美国军队正在造访我幼时的家园,而且他们陷入了战争的攻坚阶段。此外,哈萨克斯坦的读者朋友对于阿富汗也怀有一份独特的记忆。他们的国家曾是苏联的一部分,20 世纪 80 年代的那场战争,也许我的读者之中不乏亲历者与见证人。
提到阿富汗,读者们总爱问个不停。他们想知道我如何看待美苏两国对阿富汗政局的干涉。这个问题,我曾在美国遭遇过无数次。每一次,我都会给出相同的答案:两次入侵都给阿富汗带去了沉重的灾难。苏联人无法自拔的深渊,如今又困住了美国人。开战之前,美国政府奉行实用主义,轻而易举就找到了干涉的理由;之后,却又受困于政治因素而无法迅速抽身离去。每蹉跎一点时间,美国政府就要付出更多的生命与金钱,而且他们并不知道原因何在。美国能够控制城市,却无法平息那些自以为在捍卫伊斯兰教的人发起的农村叛乱。
我的回答,读者们并不满意。有一位读者反复追问,还觉得我刚才那番话太过粗浅。我没能给出他想要的答案。最后,我不得不向他摊牌:“我觉得,这些问题的答案,您一定早已成竹在胸。您觉得我忽略了什么?”
“您一直在强调两场战争的相同点。”读者有些怨言,“对于差异却避而不谈。”
“哦,您觉得两者有何差异呢?不妨指教。”
“嗯,您不会不知道,我们当年出兵阿富汗,是受到了对方的邀请。阿富汗国内有难,所以才向邻居求援。那一次,我们不但出动了作战部队,还派遣专家顾问,帮扶阿富汗的进步势力。而贵国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则是彻头彻尾的侵略行径。对我来说,这似乎是一个很大的不同。”
当时,我只能摇头叹息。“您刚才的话是认真的吗?您当真觉苏联军队开进阿富汗是为了吊民伐罪?贵国军队当时的任务是要帮助进步力量打击反动派?其实,您的看法倒显示了苏、美之间的又一个共同点。很多美国人说起阿富汗战争,也会像您一样义正词严:阿富汗有难,美国军队千里驰援;美军来到这里不为攻城略地,只为消灭暴政。而且,我们美国人还在不遗余力地帮助阿富汗人生产和生活。”
问答之间,我产生了一点灵感。内外视角的差别,确实能让同一个故事生出不同的观感。从内部看,各支外国势力及其干涉意图实在大同小异。在战火纷飞的乡下,唯有那些反抗势力最能悟出美、苏、英之间的差异所在。
从外部看,阿富汗仿佛从未变迁,它面临的挑战一如从前,依旧崎岖的山脉、蒸腾的沙漠和无尽的草原。这里的人民向来悍勇不驯,还有着虔心宗教、仇视外族的名声。部落,是他们永恒的归宿。头巾、胡须、长袍、弯刀与马匹是部落习气的象征。每一个部落成员都必须拥有这些东西,否则,他就不属于这里。如此严格的会员准入制度,远远早于重金属音乐同好会,比起当代男士必须遵奉的着装守则也要悠久得多。
事实上,阿富汗人有他们自己的故事。历史上,这个国家总是朝着某一目标蜿蜒前行,尽管途中总被外来干预打断。那么,抛开路上的种种蹉跎,阿富汗人的故事还能剩下些什么呢?
“布兹卡谢”(Buzkash)这种马背叨羊游戏,似乎只见于阿富汗及中亚的草原上。游戏中,大家各自骑上马匹,瞄准地上的山羊尸体发起攻击。骑手一旦抓获猎物,就要朝场地两端狂奔;只要马儿跃过端线,他就能够获胜。不过,幸运儿的身旁总会你追我赶地聚起一众人马。大家不停扭打撕扯,只为夺取那件战利品。比赛没有队伍,参与其中的选手都是为了个人荣誉而战。参赛人数也从来没有具体规定。除了端线,场地内外并无明显区分,甚至没有负责掌控全局、研判形势的裁判。这种游戏并无犯规一说,自然也不需要有人维护规则。要想约束选手的行为,只能依靠传统习俗以及乡规民约,而且需要参赛者相互之间形成一种自觉。那些需要明文保护方才愿意上场参赛的人,根本就不会收到竞逐的邀请。
200 多年前的阿富汗社会,就好像一场轰轰烈烈的布兹卡谢。而后,阿富汗历史的主题一直围绕着两个问题:这种游戏需不需要一点规则?何种规则最为适合?当然,阿富汗这片土地不仅被用于布兹卡谢,这个地方还成了鲁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口中那场“大博弈”(The Great Game)的竞技场。为了各自的战略利益,世界强权纷纷加入。就像所有主权国家之间的博弈一样,这也是一场没有规则的游戏,它本身与阿富汗问题无关,其利益关系是全球性的。阿富汗不幸卷入其中,只是因为它正好位于混战的前沿而已。
两场不相干的游戏在一个场地举行,玩家难免磕磕碰碰,双方的命运也由此交织到了一起。自 19 世纪早期以来,太多类似的故事曾在这里上演。一场游戏会影响另一场游戏,并使其更为复杂。但是,大国间的博弈绝不能与阿富汗内部的竞逐混为一谈,那样一来,只会让历史的面目混淆不清。
200 多年前的阿富汗社会,就好像一场轰轰烈烈的布兹卡谢。
大国干预阿富汗的故事确实引人入胜,不过,阿富汗也有自己的故事。一场干预自有生发起落,不同的侵略者则在来往更替。不过,他们并非阿富汗这个故事的主角,他们只是搅乱了故事的发展。每次外部势力造访,故事都得从头再来,此前的情节发展悉数毁于一旦。同样一个故事,被人屡屡搅局,也难怪那些搅局者总会吞下同样的苦果。
“帝国坟场”一类的论调,笔者不想重复。介入阿富汗事态的大国势力似乎总会一败涂地。这里地形复杂、人民善战,这对征服者而言确实是特殊的挑战。如此想法看似智慧超然,实则大错特错。历史上,阿富汗沦于外敌铁蹄之下的情况实在不知凡几。3000—4000 年前,雅利安人(Aryans)便征服了这片土地。因此,这里才会被人叫作“雅利安人的国家”(Ariana)。后来,“雅利安人的国家”被纳入波斯帝国的版图。阿富汗人以波斯语(阿富汗官方称之为达里语,近 90% 的阿富汗人将达里语作为第二语言)为通用语言,正是出于这层关系。后来,希腊人又成了这里的征服者,他们建立的希腊王国延续了 200 多年。时至今日,在阿富汗的一些地方,偶尔还能见到金发碧眼的希腊征服者后裔。佛教徒也一度成为这里的主宰,独一无二的希腊式佛教艺术由此在阿富汗起源并走向繁荣。
如今,99% 的阿富汗人都信仰伊斯兰教。显然,这是阿拉伯人征服阿富汗留下的一项遗产。突厥人更是隔三岔五就会吞并此地。横扫而过的蒙古大军,把阿富汗化为了一片鬼域。阿富汗是“帝国坟场”,但不是蒙古帝国的坟场。15 世纪,喀布尔还曾沦为一名突厥军阀的领地。此人后来南下印度,开创了莫卧儿帝国。种种事例表明,阿富汗这片土地并非不可征服,只是所有成功的征服者现在都被称为“阿富汗人”。
早期的征服活动塑造了现在的阿富汗。本书讲述的是阿富汗最近 200 余年的故事。其间,西方强权想要主宰这个国家,阿富汗人先后五次(次数取决于读者对“战争”的概念)与之交战。阿富汗的故事与大国干涉的故事交相勾连,仿佛同一个故事的两条叙事线。它们互不隶属,却又相互影响。唯有站在世界的高度,才能解释阿富汗为何屡遭侵略,而侵略者却无法遂愿,其原因可能就在这个国家的内部。
接下来,笔者将带领大家深入阿富汗内部,好好看看这个国家的故事。其实,这个故事并不是很长,阿富汗几乎和美国一样年轻。内有顽疾,外有持续不断的干涉,才让这个国家步履蹒跚、求存艰难。
02
大画景
谈古而不论今,这是本书的主旨。时事瞬息万变,自然不好妄下断言。但是,本书行到结尾,我也想谈一谈今天的阿富汗。毕竟,“今天”代表了阿富汗历史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由来已久,并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对阿富汗来说,地理位置是最重要的问题。阿富汗是一个中间地带,是列强之间为争夺比阿富汗更大的赌注而苦苦挣扎的地方。在古代,突厥、波斯与印度文明在此交汇,他们都对阿富汗有所影响,但阿富汗却又那么与众不同。人民在此不断融合,但这片土地从来不是波斯的边疆,也未变成印度北部的一部分。古往今来,介入阿富汗的大国势力不断变化,争夺从未停止,但阿富汗却从未消失。阿富汗非但没有被融合,反而不断从入侵者那里吸收各种因素,将自己塑造成一个有别于邻国和入侵者的实体。
2002 年,最初的塔利班被推翻后不久,我 37 年来第一次回到喀布尔。我一路北行,游历了大片乡村,一直到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曾经的据点潘杰希尔山谷。当时,首都的三分之一或更多的区域被夷为平地,北郊的平原上还有战火的硝烟。我发现,阿富汗还是那个我离开时的阿富汗。
我和我的朋友们在潘杰希尔河畔走走停停。几分钟后,我发现周围都是牧羊人和农民。他们会从我们身边走过,看看我们是谁,并给我们带来了热茶和新鲜的桑葚。每到一地,都有陌生人主动攀谈。他们常常说起他们的故事,也会天南海北地随意聊天。类似的际遇实在太多,我已记不清当时的谈话内容。这个国家的物质文明遭受了难以置信的破坏,但是其文化在死亡和时间面前还是那样冷静和漠然。这里的人们还是那么乐于交际,不管哪个国王在位,阿富汗的老百姓都会热情得有点咄咄逼人。
为了争取男女平等,阿富汗人曾经付出过太多血的代价。不过,这个国家仍是一片公私分明的世界。公共世界几乎完全属于男人,女人仍然要远离陌生人的视线,只能生活在高墙大院之内。不过,作为一个阿富汗人,我可以证明,至少在我的家族和家庭里,女性仍像以往那样充满力量、健谈而有活力。
2012 年,我再次回到阿富汗。我发现这个国家已经有了很大变化,虽然仍有许多事情没有改变。2002 年的喀布尔街头一片混乱,被破坏的建筑随处可见。2012 年,喀布尔的秩序也没好到哪里去,只不过,热火朝天的建设场面成了混乱街景的根源。2002 年,几乎没有人有电话。2012 年,虽然没有固定电话,但几乎每个人都有一部手机,很多人甚至有两部手机。在我上一次访问中,虽然城市里几乎看不到有人骑驴,但在乡下有不少人在骑。现在仍可以在农村看到驴子,但骑驴拉货的农村人运送的物品可能变成了电脑。
2002 年,喀布尔约有 35 万居民,这里的汽车很多,但(据我所知)只有两个交通信号灯,城市的交通状况自然很不乐观,但大家好像已经习以为常了。2012 年,喀布尔的人口已达数百万,具体有多少,众说纷纭。根据美联社的估计,大概是 300 万人。喀布尔的很多人认为有 500 万,也有些人估计是 1000 万。然而,正如我所说的,许多方面仍没有改变。这个拥有数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仍然缺乏交通信号灯,交通拥堵仍旧无解,但似乎依旧没人关心。他们只是一边等车,一边用手机做生意。“今天我们不被堵在这里,也会被堵在其他地方,有什么好着急的?”一个人耸了耸肩,补充道,“一切听从真主的安排!”
这个国家的物质文明遭受了难以置信的破坏,但是其文化在死亡和时间面前还是那样冷静和漠然。
阿富汗的乡野一如既往地古老而宁静。驶出喀布尔 100 多英里,我们进入了一处看似没有人烟的山谷。我们停下来换了一个轮胎。一个白发苍苍的当地人从我们根本看不见的村庄走过来,邀请我们上门喝茶。城市里的人可没有这等闲情,那种从容不迫的平静感已经让位于金钱和科技引发的疯狂喧嚣。然而,这只是阿富汗人性格中的一个方面。这个社会也一直是一个比拼人际关系的丛林竞技场,掌握权力的人可以恣意妄为。从艾哈迈德·沙阿时代开始,这个情况完全没有任何变化。
时至今日,十年前的喀布尔人所藐视的那些交通规则,大家仍然觉得只是一种不合国情的舶来品。有人笑言,在喀布尔开车就像玩布兹卡谢。司机们随意变道,只要瞅准一个空当,甚至会驶入对方车道,逆向行驶。您可能认为这里毫无秩序。
您如果这么想,或许也有失偏颇。如果真的没有规则,街上每天的车祸数量会多达成千上万起,但我看到的是上千次的险些碰撞,没有一次真的碰撞。车辆非常之多,刮擦相撞的情况却从未发生。外国人眼中这些规则可能并不明显,但对阿富人来说,它真实存在,并理解这种规则。毫无疑问,这个国家的社会和政治生活也是如此。
阿富汗人的规则很难辨析、领悟,部分原因是那里拥有不止一套规则。当阿富汗在 18 世纪作为一个民族国家联合起来时,它可能就有一种一贯的文化,虽然它在不断演变,但它是在一个连贯的框架内发展变化的。
随后,这个国家经历了来自欧洲的一系列入侵,引发了一系列的相互冲突。阿富汗人民的凝聚力来源于传统的部落和伊斯兰价值观,人们希望政府不遗余力地尊重和捍卫这些价值观,希望政府能对自己的生活少一些管束。不过,阿富汗的统治者也不能简单地顺从,因为周边总有两个或更多装备精良的西方巨人在竞争,而阿富汗就在他们混战的战线上。每一方都想进入这个空间,都想与阿富汗合作成功,他们都觉得自己能为阿富汗带来文化上的进步、物质上的改善,各方都乐于和阿富汗领导人打交道,只要他们在欧洲人熟悉的文化基础上运作。
阿富汗的统治者试图在内外之间进行周旋,但这使他们陷入了双重困境。想要确立地位,他们必须谋求当时最强大的外国势力的支持。但是,没有一个阿富汗人能够在没有本国最强大的力量支持下长期统治这个国家。在外部强权看来,阿富汗的统治者必须为己服务,内部势力却又要求统治者摆出力拒外敌的姿态。成功的国王总得学会两面平衡,表面上声称自己是保守的社会传统和伊斯兰价值观的拥护者,实则在暗中追求现代化。
如今的阿富汗面临着同样的情况。不过,内外势力对于卡尔扎伊政府都心怀疑虑。阿富汗人觉得卡尔扎伊不断妥协,总在答应美国人的各种条件;卡尔扎伊的各项政策,美国政府看在眼里,认为阿富汗在开倒车。美国人甚至担心,卡尔扎伊会和塔利班沆瀣一气。其实,任何人只要坐上卡尔扎伊的位置,都会表现得如此“精神分裂”。他的所作所为并非无能的表现,他的矛盾表现只是阿富汗社会图景当中各类矛盾的集中体现而已。
大国之间的交锋,导致人们对阿富汗的民族性产生了不同的看法。每一支外国势力都觉得自己是在干预“一个国家”,其实,他们每每横插一杠,不过是加入了一场阿富汗人关于国家认同的内部斗争。每一支干涉力量都扮演着这样的角色,他们总要扶植代理人,帮助自己统辖整个阿富汗。但由于傀儡的权力得自国外,因此,阿富汗传统社会对于喀布尔中央政权的信任度在一路走低。外国势力原本觉得,只需抓住把手,就能握住阿富汗这把瓷壶,没想到瓷壶破裂,他们的手里只剩下一个把手。舒贾·沙阿和亚库布·汗就是英印当局的把手,巴布拉克·卡尔迈勒和穆罕默德·塔拉基则被苏联人握在手中。他们虽处于不同的时代,但其代理人的角色相似。至于卡尔扎伊,则是新时代的代理人,只不过他无须顾及英国或者苏联的命令,只需听命于美国和北约而已。
外国干涉,不仅削弱了傀儡政权的执政能力,也破坏了喀布尔在阿富汗的权威。中央权威涣散,导致地方割据势力纷争而起。最终,入侵者都陷入了难以收拾的乱局。这种乱局消耗了他们的资源,以致其没有时间和力量来实现干预最初的目的。问题不在于统一团结的阿富汗不可征服,而是分裂内乱的阿富汗让征服者无力管制,这才是问题的所在。外国干涉势力想要重建中央权威,却总是无能为力,毕竟,能够团结阿富汗的只有阿富汗人自己,这取决于阿富汗文化内部矛盾的解决。只有当外国势力从这个他们无力控制的国家撤出,阿富汗的城市(或农村)统治阶层重新掌权,阿富汗才能重新迎来团结的局面。驱逐外敌一定会使新政府的威望高企,阿富汗历史的钟摆也会从分裂转向中央集权。在新政府的努力下,国家将整合各民族和团体,形成统一的合力。
阿富汗的每届政府都在进行这样的努力,因为外国势力总在干涉阿富汗的局势,没有哪个政府可以眼睁睁地看着这个社会分崩离析。
一旦获得阿富汗人的信任,新的统治者就会着手推进两件事:表面上,他们要秉持不结盟的原则;暗地里,则要和外部势力达成谨慎的妥协。而且,他们要让阿富汗的文化传统融入整个世界潮流。后一项任务,尤其需要他们谨慎操作,因为一不小心就可能身败名裂,失去权位。
同样的情况会再次发生,无论是华盛顿属意的人选获得阿富汗的统治权,还是塔利班分子席卷城市、确立统治。面对大国干预的持续威胁,喀布尔中央政权渐渐习惯向外看,并倾向于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员。如果塔利班分子夺取政权,他们很快也会生出同样的迫切心态。这种向外看齐的心态和对某种形式的现代性追求很快会显现出来。
他们每每横插一杠,不过是加入了一场阿富汗人关于国家认同的内部斗争
面对阿富汗,世界列强有两个选择:要么征服这片土地,要么秉持公正立场,促进阿富汗社会达成和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使阿富汗在文化和政治上建立起主权国家的和解,最符合所有各方的利益。我之所以说“讽刺”,是因为阿富汗一旦获得主权,它将采取中立的外交政策,这将不符合其他国家的利益。由此一来,大国可能宁愿彻底征服这个国家。可是,这一目标完全不可能实现。那么,外部势力到底想要一个中立的阿富汗,还是一个俯首帖耳、四分五裂的傀儡政府呢?
奠定民主、消除腐败、解放妇女,皆非美国在阿富汗面临的主要难题,这些问题应由阿富汗人处理。对美国政府来说,真正的问题是如何放手。华盛顿当局必须让阿富汗政府学会自立,但又不至于落入其他国家的掌控。这样的局面并非美国或者北约能够单独掌握,因为任何关心周边利益的国家,都有可能介入其中。因此,各方必须达成一致,确保“中亚瑞士”阿富汗的永久中立地位。
一旦外部压力减弱,阿富汗人就能着手解决国内的文化矛盾。这条道路注定布满荆棘。但是,希望并非那么渺茫。虽然城市和农村这两个世界的冲突由来已久,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条鸿沟正在渐渐缩小。十年前,我在阿富汗的家乡还没有像样的路政设施,虽然这个小村就在喀布尔不远处的郊区。要想到达那里,得适时脱离公路,沿着那个方向一路翻山越岭,步行、骑驴或搭乘汽车。不过,这些已成历史。如今,我的那些亲戚正在忙着对他们一直耕种的土地进行确权,因为无主的土地即将被政府征收。笔者老家所在的德叶海亚(Deh Yahya)村,将来会成为首都新区的一部分。
2012 年,我偶然结识一位普什图司机。他来自瓦尔达克农村,不过已来喀布尔谋生多年。听说我在为阿富汗写作,他立即表示要为父老乡亲发声:“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可能觉得,阿富汗人只知道互相杀戮、互相伤害,但那不是事实!看看我吧,难道我不是个温柔可爱、行为得体的男人吗?”(没错,司机先生的确是我见过最温柔可爱、行为得体的人)他还说,“政府已经修好了路。以前,从我家到喀布尔需要 4 个小时,现在 45 分钟就够了。母亲一旦身体欠安,我可以迅速带她到喀布尔的医院。所以,你觉得我们会反对修路吗?我们农村人不会反对修建道路,也绝对支持兴办医院。我们只想和平地生活,就像一直以来那样平平安安地生活。”
那一次,我还去了巴米扬。矗立在那里的大佛已经被塔利班摧毁。上一次来到此地,我只有 2 岁。对于庄严的佛像,我已经毫无印象,只能通过旧日留影进行缅怀。我们沿着谷地,一路走进巴米扬省的腹地。道路两旁的所见所闻,并未让我生出太多陌生感。附近的巴扎和我幼时的记忆没有太大差异。对我而言,这里就像喀布尔的德赫布里(Dehbouri)市集,窄窄的街道两边,密布各类小商铺,肉店的吊钩上挂着各种新鲜肉类,水果和蔬菜被高高地堆着,火柴、电池、铅笔、睫毛膏、玩具等物品也能在这里找到。店里的老板和顾客一边喝茶,一边谈生意,街上的小贩在高声叫卖,为手中的货物寻找销路。人群当中,我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他坐在高脚凳上,身前还有一方小桌。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他是个达拉克。从前,村民需要剃头或者行割礼,就会请他们。
他当然不是达拉克,这种工作早就没了。我走近一看,才发现他身边有好些现代玩意儿。桌边立着一个手提箱大小的太阳能电池板,电池板的一头连着一个 12 伏的汽车电池,用于支持笔记本电脑的运行,笔记本电脑可以通过无线信号连接互联网。即便身处阿富汗中部农村,他仍可以从喀布尔或印度的网站上下载歌曲。他的生意非常有利可图。所有的歌曲都经过电子调制,虽然风格现代,但明显源自 20 世纪 50 年代我在喀布尔电台听到的那种音乐。这种音乐源于山区的民间音乐,可以追溯到 12 世纪乃至更久以前,就像美国的乡村音乐可以追溯到阿巴拉契亚的蓝草音乐,英国乡村音乐可以追溯至都铎王朝时代,摇滚乐也可以通过密西西比三角洲的蓝调找到非洲这个源头。
这就是阿富汗。在这里,21 世纪与 12 世纪紧密相连,不过,其文化与历史的漩涡冲击终将汇成一条新的巨流。站在大佛曾经凝望的巴米扬集市,我突然生出一种感觉:周围的一切并不代表过去和现在,也许它们象征着未来,它们正从阿富汗历史的沼泽中升起。我无法想象它最终的形态,只是突然觉得,阿富汗就像一个实验室。数个世纪以来,无数势力席卷过这片土地,这个国家充满了矛盾——我们的星球又何尝不是如此。如果阿富汗能成功地将国内的众多民族融合成一个具有凝聚力的文化整体,那么,也许这个星球也会有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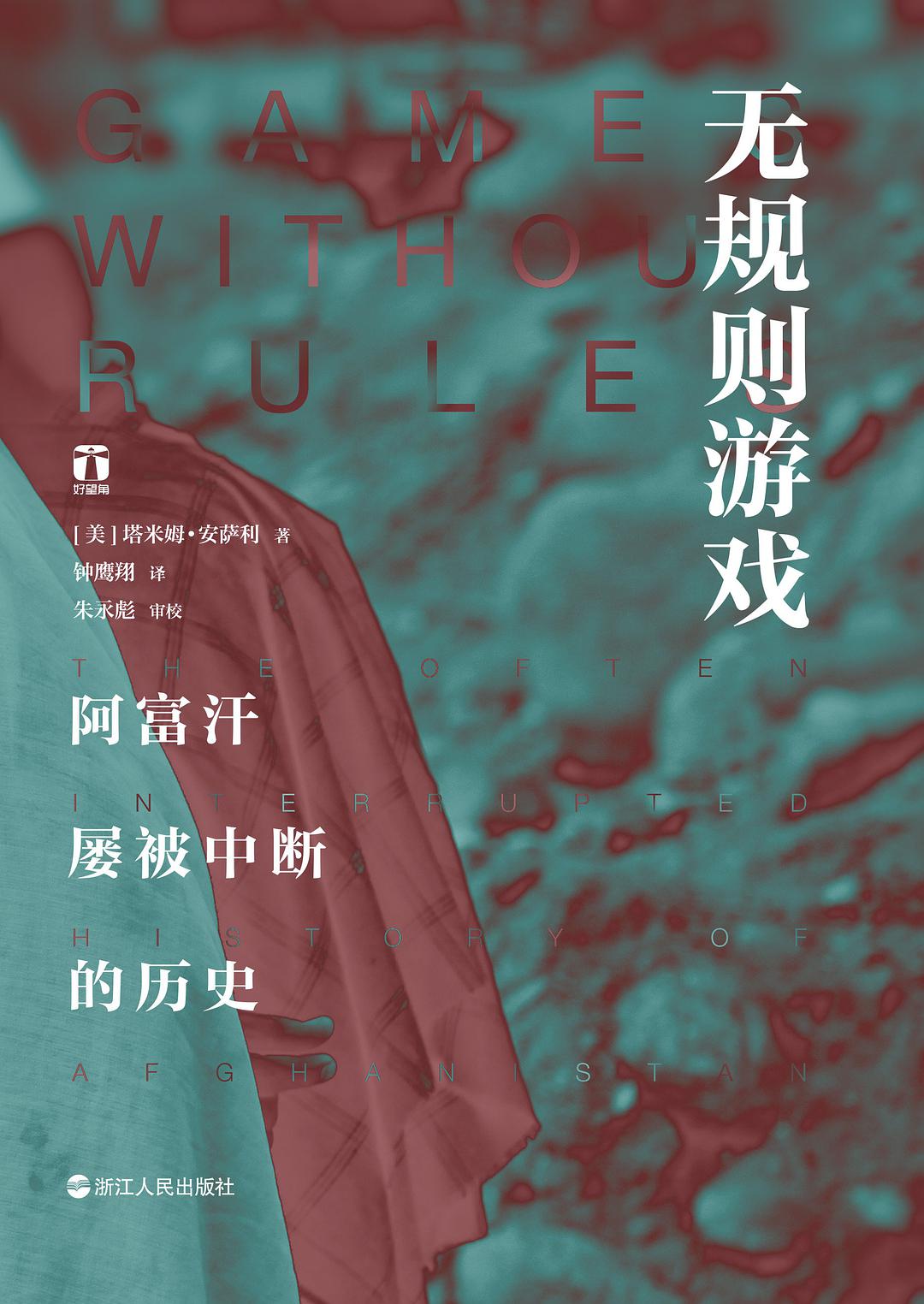
本文摘自《无规则游戏:阿富汗屡被中断的历史》
[美]塔米姆·安萨利
钟鹰翔 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8 年 11 月
题图来自 Mohammad Rahmani on Unsp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