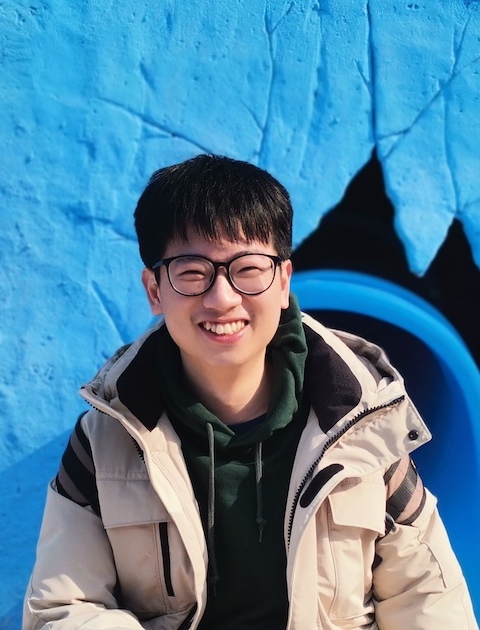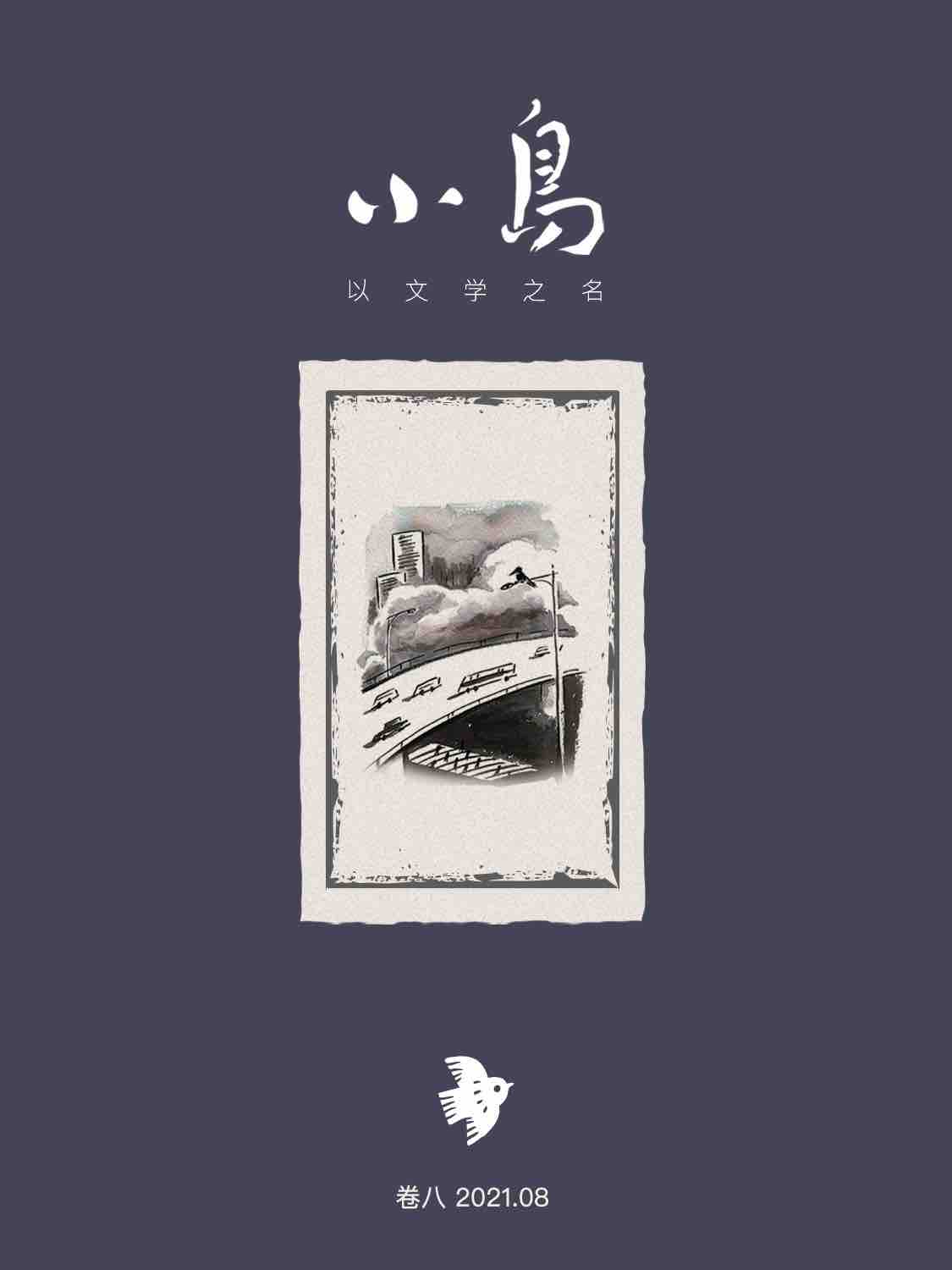1996 年,《读书》杂志组织李零、陈平原、葛兆光、陈星灿等学者搞过一个笔谈,讨论“考古学与人文知识问题”。当时,许宏对陈星灿的文章《公众需要什么样的考古学》深以为是,但觉得只需极少数人考虑公众考古的问题就行,而自己不在其列。
10 余年后,许宏的思想发生转变,走出象牙塔,成为公众考古的倡导者和践行者,著有《最早的中国》《何以中国》《大都无城》等多部面向大众的作品,经常在微博上和百万粉丝分享和交流考古学相关问题,还参与考古学通识课程的音频录制等。
许宏称,自己的变化跟整个大时代的变化有关。最近这些年,许倬云、葛兆光、王明珂、王柯等学者都出版了讨论“什么是中国”的著作。他认为,这可能显现当代中国人的某种整体焦虑,想从古代历史文化中寻找答案。作为田野考古人,看到大家都在思考这个问题,觉得挺好。
“考古学本来就是提供精神食粮的,而且百年之前,中国考古学以显学身份诞生,它要解答康有为的‘上古茫昧无稽’、胡适的‘东周以上无史’、顾颉刚等的‘古史辨’。在中国上古史一片空白情况下,才是傅斯年提出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前几十年,考古人在寻找破解无字地书的密码,所以给人的感觉是一度躲进了象牙塔。后来,中国从农业社会转向工商业社会,人们从衣食足到知礼节,像我这样传统的考古人,也开始往外转,觉得应该回馈公众。”许宏说。
回馈公众是个澄清误解的过程。比如在许多人印象中,田野考古就是一场“寻宝”之旅,但许宏称,与其说考古学研究“物”,不如说考古人对“物”背后的“原境”(context)更感兴趣。这代表了考古学的范式转型,从关注物的文化史到物背后的关联、背景和意蕴。他的主要贡献也属于后者,自称“不动产专家”,率队发现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含第一个大十字路口)、中国最早的“紫禁城”(宫城)、中国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宫室建筑群和多进院落宫室建筑、中国最早的官营手工业作坊区和绿松石器制造作坊等。
“考古学是一门充满野心的学科。这群人想通过物质遗存来探究人类的全部过去,根本不是为了寻宝。我们更像侦探,通过残存的碎片尽可能复原当时的社会文化面貌。虽然我们永远不可能获知真相,但是仍然怀着最大限度迫近真相的执着去做碎片拼合工作,所以我们才对物背后的 context 感兴趣。就像绿松石龙形器的 2000 多块碎片,如果没有‘龙’这个 context,它的历史价值就会大打折扣。”
再比如总有网友问许宏“夏是否存在”。他其中一个回答是:“夏王朝,还处于传说时代,我们是从比它晚千年以上的东周到汉晋时代人的追述中知道夏的。一般认为,考古学上的中原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可能是夏王朝的遗存。这个问题,还没有定论。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发现当时具有自证性的文书材料,所以对夏的存在,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
也许,更值得琢磨的是人们着迷这个问题背后的文化心理。许宏说:“寻找夏是我们当代人的一种欲求,是要解决自己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些阐释都是当代人的阐释,可能性之一而已。其实,我们几千年的祖先应该先被当作他者,探知究竟发生了什么,然后再跟我们关联在一起。”
还有网友爱问三星堆文化是否来自外星文明,许宏说这是考古圈同事最懒得回答的问题(另一个他们最不愿回答的问题是盗墓和考古的区别,觉得盗墓是对其专业的侮辱)。他称,大家看三星堆某些青铜器的造型感到怪异,那是由于当代人视野狭窄。其实,三星堆文化明显受到中原二里头文化的影响,再加上其他尚不知出处的外来文化和土著文化,三者结合才构成这样的青铜文明,根本没有超出考古人既有的认知范畴。
当然,学者走出象牙塔不免受到“墙里开花墙外红”之类的质疑,但许宏并不惧怕,觉得自己有学术上的文化自信。现年 58 岁的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专攻中国早期城市、早期国家、早期文明研究,执掌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考古队队长 20 年(1999—2019),著有近百万字的专著《先秦城邑考古》,主编考古报告《二里头(1999-2006)》(全五卷)、集成性专著《二里头考古六十年》等,份量足够。
但是,很多读者觉得许宏谦虚、和善、严谨。他的书有点“述而不作”的味道,爱把自己藏在文字背后,不会直接表露观点,而且常说这个不清楚,那个没定论,有待进一步探究。他强调,考古学最擅长知其然,至于所以然,那就进入了猜想、阐释阶段,具有多元和不确定性。
“在上古史和考古学领域,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能排除任何一种假说所代表的可能性。在认识论上你必须有这样的认知,打破标准答案这种思维,才能是一个心智健康的人。”许宏说。
2021 年,许宏迎来一个“出版年”,一口气出了 4 本书,包括 3 本新书——《东亚青铜潮:前甲骨文时代的千年变局》《发现与推理:考古纪事本末(一)》《踏墟寻城》,和一本再版修订的《最早的中国:二里头文明的崛起》。
他在《东亚青铜潮》中写道:“英国剑桥大学考古学家伦福儒教授说过,‘考古学使我们有可能把每个国家的早期历史看作整个人类更大范围的历史的一部分’。串联起人类文明史的发展脉络,找回我们失去的文化记忆,正是考古人的使命所在。……与后世人类文明的壮美相比,书中所展示的最早的金属文明的遗存似乎还缺乏视觉冲击力,但缘起,往往是最迷人的。”
未来,许宏称自己要转型为“非虚构作家”,继续创作“解读早期中国”和“考古纪事本末”两个系列,希望写出将古代和现代串联起来的佳作。“我们考古人的野心不限于过去,鉴古的目的是知今,甚至还要考虑如何走好未来的路。”他说。
以下是 2021 年 8 月我和许宏的访谈节录,包括青铜器和中国社会结构变化的关系、三星堆文化来源、青铜全球化和早期全球文明史、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和新的大都无城时代、从考古学角度展望人类未来等内容。
01
以青铜为代表的“模范中国”
小鸟文学:《东亚青铜潮》引用了汉学家雷德侯的说法,中国人发明了包括青铜器铸造在内的“以标准化的零件组装物品的生产体系”,“模件化生产以多种方式塑造了中国社会的结构”。这里有点抽象,能不能具体讲讲你如何理解青铜器和中国社会结构变化的关系?
许宏:中原地区青铜时代的到来应该叫中国青铜礼器时代。从二里头开始,东亚最早的青铜礼器群出来了,就是用比较复杂的复合范,或者叫块范法来铸造青铜器。我注意到,它的出现时间跟我所说的广域王权国家在东亚大陆出现的时间是同时的。
这个很有意思。以前有学者提出,在青铜时代之前,中国是不是出现过玉器时代?可以从龙山时代,或者稍早一点的良渚时代、仰韶时代后期开始?因为像汤姆森等欧洲学者提出“石器—铜器—铁器时代”,主要指工具和农具。到了中国,青铜的使用不是工具和农具,而是礼器。如果前边有一个主要用玉来做礼器的时代,现在看来是可以接受的。
玉器时代恰好跟古国、邦国时代一致。这些古国、邦国,不少中国学者认为就是国(state)了,也有的认为相当于酋邦(chiefdom)——前国家时代复杂社会,所用的重要礼器以玉器为主,所以玉器是“前铜礼器群”最重要的象征和标志。
我们几千年的祖先应该先被当作他者,探知究竟发生了什么,然后再跟我们关联在一起。
玉器是通过物理变化加工石料,只能改变形式,没法改变化学成分,而青铜是最早的合金,它开始利用化学变化来生产出大自然不曾存在过的新物质。玉器只能一件一件做,根本不可能用模件化思维,所以每件玉器都不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有像以后青铜列鼎那种成套感,甚至用同一个模范来做。
这是一个本质差别,甚至有一种隐喻。按理说,玉器只需要几个人,不用车间就可以做,但司母戊大方鼎起码需要二三百人,还不包括后边的管理阶层、后勤保障。等于说从单个不一样的玉礼器,形成不了范式、规制,到青铜这种成批量用内模外范,后边必须有国家的强力支持,一整套来做显现权威,显现形而上和意识形态。有了这样的动力,导致它大规模管控这种高科技,投入很大人力和物力,做出整齐划一,有点体制美学感觉的东西。
“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你做的玉器和他做的玉器完全不一样,但是现在中原王朝起来了,二里头、二里岗时代的青铜礼器生产,一开始就是独占,等后来进入殷墟时代,这种独占的高科技才外流或者说“泄密”,关中、三星堆、湖南湘江流域、江西新干大洋洲等地,才得以模仿着来做。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古代青铜文明就有高度一致的范式(model)。从技术到形而上的政治理念,这跟广域王权国家同步,有密切的对应关系。现在,中国人还把“模范”看得很重。以前北大做了一个展览叫“模范中国”,名字起得太好了,最接近中国人思维和行为方式的东西就是模范。
小鸟文学:你说:“在二里头文化时期,二里头都邑是唯一能够铸造青铜礼器的地点,可谓一花独放。随葬青铜礼容器的墓葬,也仅见于二里头都邑,表明它不仅独占了高等级青铜器的生产,而且基本独占了对它们的政治消费。到了二里头文化末期即二里岗文化初期,青铜礼器才开始向外扩散。”我比较好奇,为什么当时二里头都邑能够在铸造青铜礼器上一花独放?
许宏:这跟上面的题目密切相关,我一直在思考,悬而未决。至少在二里头,我们发现了中国最早铸造青铜礼器的大型铸铜作坊,还有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器群。礼器包括礼容器和礼兵器,礼容器里尤以酒礼器最为重要。这些东西开创了三代王朝青铜文明先河,这个传统和制度往下延,大家比较熟悉,就不多说了。
但是,现在还有缺环。二里头一期没有发现青铜容器,二期只是铜牌饰和铜铃,也没发现青铜容器。到了二里头三期,也就是二里头晚期,一下就能做青铜容器,爵开始出来,突然上了一个大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