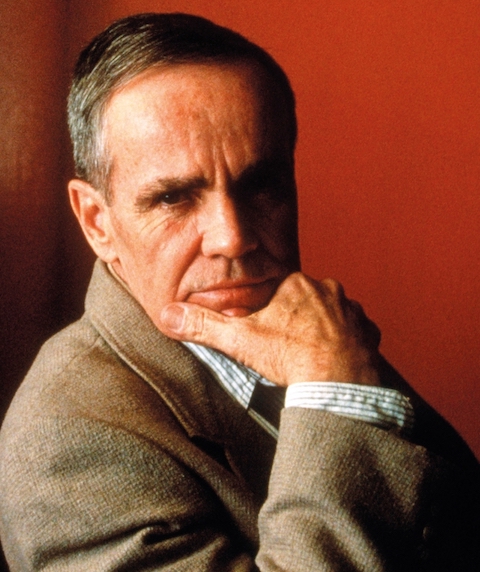希尔德去蒙克酒吧,喝啤酒直到六七点钟,终于起身回家。八点钟,他已经把一些衣物叠进一个老旧的硬纸壳箱里,阴沉沉地坐在那辆小汽车的方向盘跟前,车头灯划开前方的夜色,编号 129 的狭长柏油路在他身下如同从卷轴上拉出的缎带。他在乔特附近的一个酒吧停了一回车,用咖啡杯喝了两杯温啤酒,买了些烟。山路狭窄,满地都是沙砾,他抓着方向盘,车轮一直打滑。一只山猫窜到路上,腿极长,双眼如灯,弓起身,跑到路肩,不知道往哪个方向去了。
往前再往前,高地在黑暗中起伏汹涌,变得陌生,长路在幽暗森林里崎岖蜿蜒,那里有猫头鹰的树,蝙蝠的洞穴,还有巫婆们的聚会。
他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烟,摇着手柄把车窗关上,拿烟头又点燃了新的一根烟,它们接连在一起,发出一点强光,他看着玻璃上映出自己的人影,如暗橙色的浮雕,他吐出一口烟,那一点火光消退,缓缓爬上黑暗的镜子,像是太阳莫名地在夜里升起,他又把玻璃摇下去,让湿润的空气冲进来,他把烟头丢了出去,在引擎盖上划出一道短暂的弧线。他在布莱尔斯维尔加满油,之后就再没有停过车。平原的另一头,山脚的阴影里有河流,月光蜿蜒曲折地流淌在河面上,在激流之处,雕出一众垂饰,更如成群闪光的蛇,越过幽鸣的岩块,逆流而上。有凉快潮湿的空气从挡风玻璃下吹进来。
临近午夜时,他到达亚特兰大,但没有进城。他在一个路边旅馆前停下车,离城只有几步之遥,然后在车里又眯着眼睛待了几分钟。还有三四辆车也停在旅馆前,在霓虹下映出朦胧的光泽。
他穿过门前黄色灯光下那团飞舞的蛾,走了进去。越过跳舞人群的头顶,他从吧台后面的镜子里看见自己眼窝凹陷,阴着一张脸,他感觉到一阵汹涌的疲惫感。他沿着墙边的高枱桌,来到吧台前要了威士忌,连喝了四杯。他开始觉得好受一些了。第五杯酒送到他跟前,一阵玻璃碎裂声从跳舞的人群中传来,他扭过头看见两个男人手里握着酒瓶,正兜着圈子,小心翼翼地盯着对方。一个魁梧的身影从吧台的另一头出现,从围过来的人群里走出来,他揪住那两个打斗者的裤腰带,一手一个,像拎着火鸡一样把他们拉到门外,两人手里的瓶子始终在无力地晃着。
哈哈!瞧瞧那两只火鸡,吧台边有个男人喊道。那个大块头回来了,朝着另一个方向走过去,面无表情,又融入了阴影之中。希尔德喝完他的酒,花了几分钟看了看周围的面孔,他没有一丝酒精带来的兴奋,只有不断涌来的疲惫感觉。他甚至都不觉得自己有多疯狂了。又过了几分钟,他离开了,走到屋外,他迷迷糊糊地想着自己来这里要干什么,又要往哪里去。路易斯安那或者什么地方,从 1933 年 12 月 5 日开始,已经不存在他那种工作了。
他从寂静的黑暗中走出来,地上不怎么平,他踩在沙砾上,有点儿趔趄。他走到汽车边上,打开车门。
要说那是车内顶灯的光,不如说是从那个男人脸上发出来这幽幽的暗光,希尔德愣住了,他举手挥打着车门拉开时搅动的空气。那是一张冷漠而无法捉摸的脸,正盯着他看,希尔德思索着,他不需要解释和说明,只是想和自己的理性经验连接起来,让自己能够搞明白一个人坐在自己的车里,仿佛只要拉开车门就能在顶灯亮起来的瞬间,让他魔术般地出现。那张嘴咧开了,缓缓露出一个难看的苦笑,有个声音说:你去诺克斯维尔吗?——那音调因为紧张比正常高了八度,带着一丝祈求。
希尔德的手抓住车门,吐出长长的一口气,他提高嗓门:你他妈的在我车里干什么?坐在车里的人仿佛看见什么让人厌恶的东西一样,迟疑着要不要伸手去揪住他,就像看见鸟屎落在自己肩膀上而迟疑着要不要去碰它的人。
那张嘴还开着,又说道:我看到你的车牌上写着布朗特县,我也从那儿来的,从玛丽维尔来的。我猜你是要往那个方向去。我需要有人拉我一程……我病了。那语气让人烦恶,眼神垂了下去,看着希尔德的皮带,好像是在对着希尔德的胃说话。不是有什么预感让希尔德觉得应该把这个闯入者赶下去,而是因为他深切而不可撼动地感到了一种恶,他确信,面对这个已经坐在自己车里的人,至少要捍卫自己的财产。
你确实有病,希尔德说。立刻挪开你的屁股从那里给我滚出去。
多谢了,老兄,那个男人说着一边在车座上移动,一直挪到了另一侧的车门旁,看起来一点儿也没用到身上的什么部位,反而像是顺着滑行装置往下滑了过去。然后他坐在了那里。
希尔德疲倦地把头顶在车顶上。他知道这个人并不是没搞懂他的意思。
我知道你不会把一个老乡丢在路边的,那个声音说道。你从玛丽维尔来的吗?我住得离那儿很近,我从佛罗里达来的……
希尔德跌坐进车里,后颈上的汗毛开始站了起来。他看着那家伙。我可以亲手把你丢出去,他冷冷地说,但并没有伸手碰他。他把钥匙插进去,拧动发动机。他觉得自己非常需要洗个澡。
这真是辆漂亮的车子,那男人称赞道。
顺着地上的沟壑把车倒出来,开到马路上的时候他心想:还是个话痨,这个混蛋。他肯定会滔滔不绝说个不停。
这个想法立刻被证实了,那个男人开始了。老兄,你这帮了我大忙。你知道的,大半夜要搭个便车真的不容易。
是大清早,希尔德嘟囔着,突然换到了二挡。
——尤其是根本就没什么车,而且就算有车过来那些家伙根本不会让你上车……
哈,希尔德在心里想着,不该换挡的。他从眼角瞥见了那个男人的膝盖,他把腿搭在座位上,斜着身子,正在看他。
——我妈也病得不轻,她……
希尔德悄悄把手从方向盘挪到了变速杆上,像鸟儿一样。车速里程表上的指针在发动机的轰鸣声中往上爬升。
——医药费比那什么还高……
他的左脚松开了离合器。此时此刻。在他微微张开的掌心之下,车速猛地降下去了,变速杆在那男人的膝盖几秒钟前待的地方抖动着。
——我真的要好好谢谢你……那男人又接着说下去了,声音低沉,他现在已经把腿跷起来,轻轻抖着,似乎十分舒服。
希尔德把手搭在车窗上,风呼呼地吹到耳边,他还听见不甚均匀的排气声,轮胎在柏油路上开过时咝咝的摩擦声,他试着不再理会那个说话声。
路上没车。他几乎走神了,无休无止无法逃脱的说话声在侵蚀他,把他带入某种湮灭,某种意识的迷糊之中,在预备着……预备着什么?他挺了挺身子。那男人一直没有把视线从他身上移开,但也从未直视过他。
你个混蛋,希尔德心里想。他开始觉得自己会一路开到亚特兰大的唯一目的是把这个家伙送到那里,然后他就会驱车返回玛丽维尔。他的后背很痛。我绝对是疯了,他告诉自己,把手伸进口袋里找烟。这个狗娘养的会把我逼疯。他用拇指和食指从容地从盒子抽出来一根烟,送到嘴边。盒子拿在另一只手里,然后被丢到方向盘前面去了。我打赌我做不到,他在心里默念,我够不到它。他用右手把烟放到嘴里,然后伸手去够那个烟盒,想把它放好。他的手刚回到方向盘上方一半的地方,那个声音,忽然变得清楚又充满希望,说道:那个,我在想能不能跟你要一根(身体往前倾,已经伸出手)……我已经抽完好些时间了,也没有……
无休无止无法逃脱的说话声在侵蚀他,把他带入某种湮灭,某种意识的迷糊之中
希尔德轻笑着伸直了胳膊把烟盒递给他。可以,他说,你自便。他等了几秒钟,听见盒子发出沙沙的声音,那男人拿出了烟。他察觉了他的犹豫,转头看他。烟盒被递了回来。
谢了,老兄,男人说道。
希尔德等着。男人没有再说什么。继续等着。希尔德想了想,掏出了火柴盒,他抬起腿用膝盖固定住方向盘,然后有些刻意地慢慢从里面摸出一根火柴,划燃。他用手护住火苗,点燃了烟,然后把火柴棍从胳膊上方丢进了车窗外的气旋里,重新抓住方向盘,他舒畅地吐出一口气,把火柴盒放回口袋里。他等待着。
那个,老兄,我能不能借个……啊,多谢,谢谢。
火柴被划燃,噼啪几声。希尔德在挡风玻璃里看见在那火舌上方,男人那张脸被黑与红的颜色投射了出来,像个眼睑低垂的铜像,像面具,既不含糊也不神秘,只不过有些荒诞而不知所云。就在希尔德把视线从男人脸上转去看了眼马路又转回来的这一瞬间,男人抬起头从玻璃里观察希尔德,这一刹那两个人在那火光里看着对方,仿佛两个彼此仇恨的酋长,正坐在部族会议的篝火两侧,下一秒,男人像条鱼一样咧开嘴,叼着烟,熄了火柴。
他们抽着烟,暗夜空气的热浪环绕着他们,沉闷而黏稠。在道路绵延的黑色玻璃里,仪表板是嫩绿的黎明,他们红色的烟头起起伏伏,是黎明之上遥远的信号灯。
他在盖恩斯维尔停车加油,实际上汽油还有,然后带着车钥匙去了厕所。那男人一直待在车里。希尔德在厕所里抽了根烟,呼出漫长的几口烟,最后把烟头丢进了马桶里。用冷水抹了把脸,就走出去了,把钱付给睡眼惺忪的加油站员工,回到车里。那男人还保持着他下车之前的姿势,有一道明显的新的烟雾漂浮在潮湿的空气里。
黎明。薄雾缭绕,牧场上有水汽升腾而起,树白如骨。灌木丛在清晨的湿气里看起来有如金属般坚硬。水珠从挡风玻璃上滑落,他把雨刷打开了。他看着雨刷缓缓落下,像是在祈福的手。他正伸手擦后视镜,右后侧的轮胎传来一声沉闷的爆裂声,
汽车往下一沉,停在了路边。
后来希尔德才意识到,那男人错过了一次用千斤顶手柄的机会,他一直等到希尔德从车底下把千斤顶又搬出来然后亲手递给了他,让他把它收回后备箱。也意识到那男人第二次是错误估算了自己徒手把车轮罩重新装回去所需要的时间。因为,尽管他什么都没有瞧见,也没有察觉异样,他刚拧到一半便站了起来,那时候千斤顶砸到了他的肩膀,把他砸倒在车子的一侧,然后是有什么东西砸到了他的头上,他撞在了汽车的后部——他也想起了这一点,但一直到后来才明白,那个东西就是千斤顶的底座。他也没有完全躲过第二次,不过那只是在车门边滑了一跤,那时候那男人从侧边砸过来—他现在回想起那男人的动作了—把车皮上砸出了一个破破烂烂的洞。他跌坐在地上,脑袋抵着车门,抬起头看见了那张居高临下的脸,还不觉得愤怒,只是感到疑惑,他的手臂沾满了泥土,像一只破碎的翅膀。而当那男人拉着千斤顶的手柄,要把它从车门上被砸出的洞里扯下来的时候,希尔德心里想着,动作要慢,他伸出手臂,把手搭在了千斤顶的底座上,然后同样缓慢地在底座上收紧了拳头。男人低头看他,流光逐渐聚集在车身光亮的油漆与路上扬起的白色尘埃之间,他在光之中看见了那张被恐惧雕刻和塑造的脸庞,仿佛某种缺陷。他们就那样保持了几秒钟,他坐着,那男人站着,一人抓着千斤顶的一头,就像停在了它被一个人递给另一个人的瞬间。然后希尔德站起来了,仍然如梦游般迟缓地移动,仿佛是时间自己放缓了速度,他看见男人转身,然而并不像是在水下进行这一切,更像在黏稠的液体里搏击,极端的缓慢。在垂死般的重力作用之下,千斤顶斜斜地落下了,它离开希尔德的手,跌在地上,缓缓地弹跃了几下,而那时希尔德抬起了沉重而僵硬的手臂,他的手指像进攻的猫爪一样弓起来,陷进了男人肌肉柔软的喉咙,那男人当下正要逃走,却如在噩梦之中走投无路。
也不知道是他自己往前摔去了还是那男人把两个人扯倒的,他们已经在地上了。那男人的脸抵在地上,希尔德在他上面,有那么片刻的时间,两个人一动不动,像是相拥而眠的爱人。希尔德肩膀上有什么东西斜斜地坠下来,随着他的呼吸直插他的肺,像是要切断他的气息。他的一只手仍然钳在男人的脖子上,他微微往下倾去,在男人耳边轻声道:怎么不说话了啊,混蛋?怎么不接着扯淡啊?
他猛地要揪起那男人的头,但男人双手护着自己,似乎任凭自己在马路的沙砾上陷入了思绪。希尔德松了松手,然后沿着后颈一直到抓住了他的喉咙。那男人酝酿了几秒钟,忽然往旁边一扭,朝着希尔德脸上啐了一口,试图挣脱。希尔德也跟着扑过去,按住了他,那男人躺在地上,希尔德跨坐在他身上,手臂像一条绳,从受伤的肩上垂下来。他稍稍往前倾,把一只腿插进了男人脑袋下面,让他把头抬起来一些,看起来就像个体型过大的护理师在照顾伤者。他把男人的脑袋往自己的腘窝里按,手臂已经伸得笔直,他压上了自己的全部重量,用尽全力扼住了男人的喉咙。那张脸庞如没有了骨头一般抽搐了几次,然而却一直没有改变哪怕一丁点儿神色,始终是被恐惧扭曲的表情,带着震惊和不解。希尔德不觉得是自己造成了这副神情,反而这才是男人原本的模样。那张嘴的下颌仍然开着,然而并不像是什么可以从关节上卸下来的零部件,更像是一堆废料,一个在他手里缓慢衰败腐烂的可憎而无用的物料。然后希尔德意识到那男人想要咬他,这一切如此荒谬,希尔德从鼻子里冷笑了两声,那男人的手终于抓在了他的手臂上,那些肿胀的手指头拉着他的手掌、他的手腕,这让他想起了自己曾经见过的幼年负鼠,那些眼睛还看不见、有着粉色皮肤的小东西。
希尔德那样保持了很长一段时间。他觉得这像在挤一个疖子。那个男人最后想说点什么,但什么也没说出来,只发出了咕噜的声响。希尔德看着他,沉浸在一种让人着迷的吸引力之中,他看见那眼睛眨了几下,舌头耷拉了下去。然后他松开了手,男人的眼睛瞪得巨大。
神啊,他喘着气低语,以基督的圣名啊,宽恕我。
希尔德把脸贴到男人的脸庞跟前,轻声说道,你本该找个离那里更近一些的人的。然后他看着男人的肩膀,看见男人正看着自己。他把自己的大拇指伸进了男人的喉咙里,那里已经坍塌了,像一条干瘪的水管。男人把手举起来了,闭上了眼睛,开始打希尔德的脸和胸口。希尔德也闭上了眼睛,防卫着把脸埋进肩膀里。男人打得越来越狠,但越来越慢,最终停了下来。当希尔德再睁开眼的时候,男人瞪着猫头鹰一样的眼睛盯着他,一小截舌头伸在嘴唇外。他掰开男人蜷曲的手指,如同一只凶残的猫爪,也像死去的蜘蛛。他试图让那手掌重新张开,但失败了。他又看了一眼那男人,时间回来了,拨回原状,所有的时钟又都准点了。

本文摘自《守望果园》
[美]科马克·麦卡锡
黄可 译
理想国 | 河南文艺出版社
2021 年 6 月
题图来自 Gabriel Arancibia on Unsp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