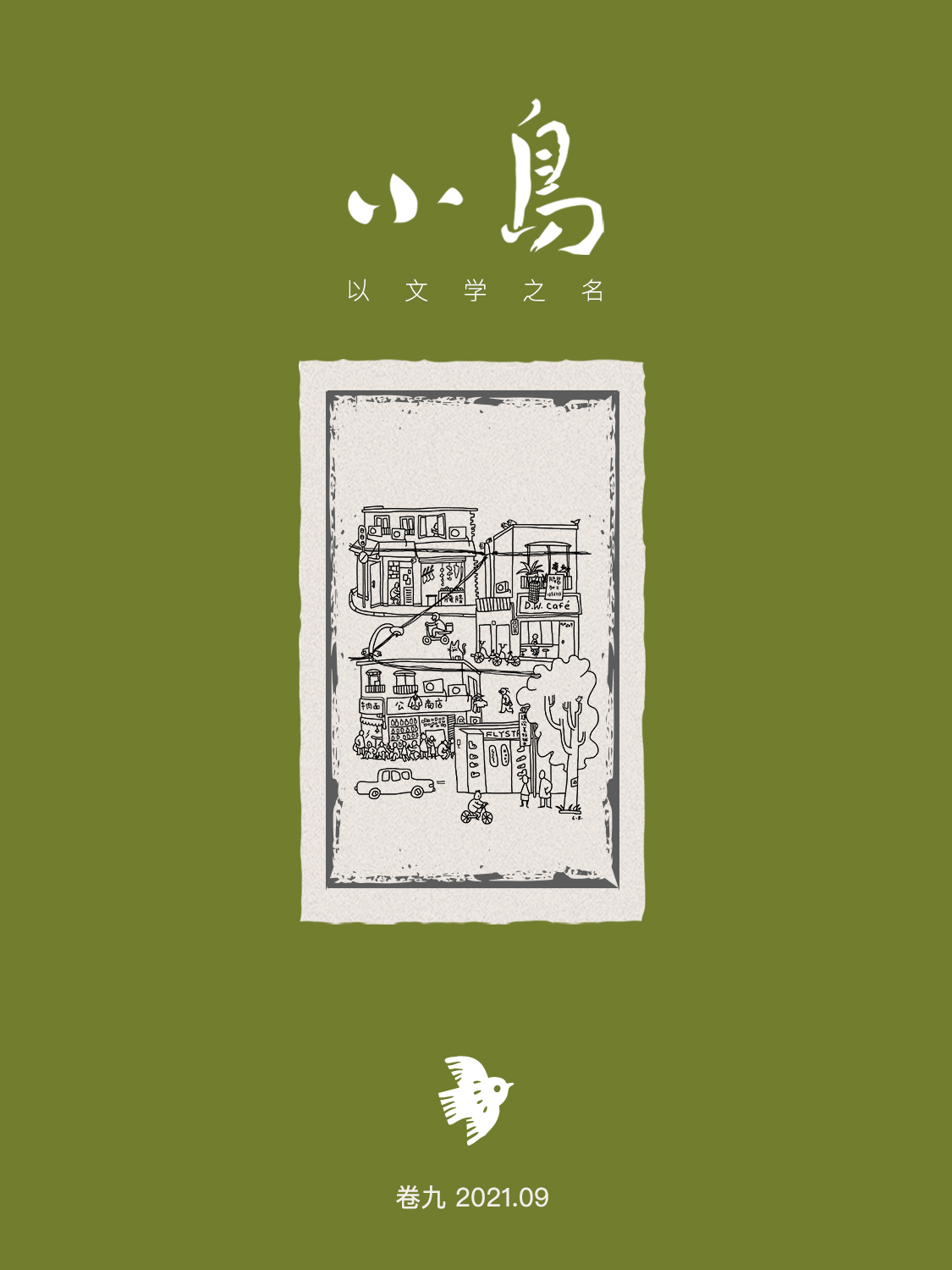在我学过的所有藏文字中,རྒྱ字是让我最困惑、也最着迷的一个。我的藏文,学是学了一些,掌握的并没有很多。不过我想,即便我今后完全放弃学藏文、将学过的这一点点通通忘记,རྒྱ字也是永远不会忘记的。因为我就是一个རྒྱ,རྒྱ是我学习藏文时的身份,是我说藏语时的身份,也是我在藏区做田野调查和展开生活时的身份,更是我与田野中认识的一条母狗共同的名字。
རྒྱ字的读音,可以简略地记为“加”。拉萨话里的“加”会有某种声调,这是我不熟悉的。用我稍微熟悉一点的安多话念“加”的时候,在舌头与上颚摩擦发出“jia”音的同时,还需要用喉咙和鼻腔配合发出一个浓重的、浑厚的、仿佛整个颅骨都在共振的重音。这曾是安多话带给我最大的发音挑战。我是一个人类学学生,学藏语主要是为了做田野调查、写人类学博士论文,不是专门搞语言学研究的,所以我的藏文学习其实很缺乏系统性,主要是学当地方言和口语,学习过程则几乎全靠自己摸索以及田野中的缘分。而我在田野中遇到的那么多半路师父,没有一个跟我讲明白过,这个重音到底是个什么质地、什么原理。琢磨了很久之后,有一天我突然懂了,才终于清楚地念出了རྒྱ字,能够向人清楚地介绍自己的身份:
“ང་རྒྱ་མོ་ཟིག་ཡིན།”(我是一个加莫。)
在这句话中,加是汉族的意思,莫是女性的意思。我是一个汉族女性。
有时加莫不仅是我的身份,还成了我的名字。人们“加莫!加莫!”地喊我。或者有时我听人们聊天,他们时不时会蹦出一个“加莫”,我就知道应该是在说我。可我不知道他们究竟说我什么了,我的藏语还没有好到可以轻易“偷”听别人闲聊的程度。这本应是田野工作的必备技能——彻底掌握当地语言,像当地人一样去使用它,像当地人一样去八卦、去“偷”听。可我的藏语学得太差了,只够在噼里啪啦席卷而过的一片安多口语音节中,精准地识别出一个接一个——我又被叫作加莫的时刻。
其实我是有藏语名字的。我叫德吉措(བདེ་སྐྱིད་འཚོ),僧人朋友起的,意思是“幸福的生活”。我可以用安多话标准地念出这个很难念的名字。当然,任何人都是有名字的,所有来藏地的加莫都是有名字的。可是所有加莫都会被叫作加莫(而所有汉族男性都会被更简便地叫做加)。有一天我实在有点委屈,在朋友又一次叫我加莫之后,对他说:“能不能叫我德吉措?我不想总是被叫加莫。我感觉没有被尊重……”
他惊奇地说:“没有呀!哪里不尊重了?你就是加莫呀!加莫就是汉族姑娘,卧莫(བོད་མོ)就是藏族姑娘。”
“但是你们不会管藏族姑娘叫卧莫,而是叫她们的名字,却会一直加莫加莫地叫所有汉族姑娘,好像所有汉族姑娘都是一样的,没有自己的特点。这让我有点不舒服……”
“怎么会不舒服呢?”
“嗯……假如有一天你去汉地生活,大家都不叫你名字,而是叫你‘诶!藏民!’ 提到你的时候就说‘那个藏民’,你会高兴吗?”
他没回话,咬紧牙举起拳头,做出要打我的样子。看样子是听懂了,算是明白了尊重的相互性。设身处地地想想,我们是不是都经常在这样一些微小而关键的场合,不自知地伤害了少数人的感情?
一个小时之后,他又开始叫我加莫。说一时半会儿真改不过来。
不过,在这个地方呆了一两个月之后,我发现叫我德吉措的人越来越多了,叫我加莫的大多是不认识或刚认识的人。后来有一次,又来了一个汉族女生,突然间她就占据了那个本属于我的加莫的位置。大家都叫她加莫。而我则因此彻底变成了德吉措,大家都叫我德吉措了。我既释然又悲哀,反正无论如何,得有一个加莫。
其实在整个田野的两年中,有一半的时间我也被叫作“周博士”。
我的研究是一个关于藏獒经济以及人狗关系的民族志,所以有一半的时间我在藏族牧区学习牧民怎么饲养和使用自己的护卫犬,观察这些狗在“成为”藏獒之前,如何与牧民一起生活。而另一半的时间,我则是在以汉人为主的藏獒市场和藏獒养殖场里待着。这些养殖户和消费者组成了一个圈子,称为“獒圈”。獒圈里的人互称“獒友”,因为大家都是热爱藏獒的朋友。认识我的那些獒友都叫我周博士,虽然我还不是博士,没拿到学位,只是博士生。但在一次又一次徒劳的纠正之后,我也累了,他们叫我博士博士我也就应着。我知道这是他们对我的尊重,虽然关于藏獒的知识我一窍不通,他们才是这个领域的专家。可能也正是出于对“读书人”的尊重,当我向他们请教关于藏獒的品种、习性、养殖技术以及行业现状的各种问题时,他们总是非常热情地向我讲解,甚至感恩我对此感兴趣。
有一位獒友叫我时的发音很好玩。他也是安多藏人,是獒圈里少数几个还在坚持的藏族人之一,但他并不叫我加莫。他叫我“周博”。他的汉语挺好的,但有时还是发不清双元音,所以他叫我周博时,其实叫的是“卓博”,听着就很像藏语里的“朋友”(གྲོགས་པོ)。每次他见到我都像在说:“呀!朋友!”与此对应,我就总是叫他“呀!老板(སྦྱིན་བདག)!”
老板当然也是有名字的,暂且叫他次仁吧。我在次仁的藏獒养殖场里住了几个月,跟着他以及工人一起养狗、看狗,在牧区和养殖场之间来回运狗。他从事藏獒这一行已经二十年了,可他自认为从来没有真正进入过内地市场,主要是在做本地藏獒的“保护”工作。他从牧区搜寻最好的狗,买回到县城的养殖场里配种、繁育,再将所生小狗以相对较低的价格卖给附近的牧民,以补贴成本。有时也免费送给亲朋好友。他还有别的生意可以赚钱,藏獒只是“兴趣”和“理想”。他认为只有将好狗集中起来,精心培育,然后反哺牧区,才能让藏獒在本地就得到保护,而不是不断地流入内地市场这个“无底洞”,不断地在价格的浪潮中沉浮迷失,让“纯种”藏獒的血系掺进越来越多、越来越乱的“杂质”。
这种理想主义的态度让他甘愿做獒圈的一个边缘人。猜测他的人很多,也有拉拢的、攻击的。其实獒友们之间的关系一直都是如此,不过是任何圈子都有的那些恩怨。只不过藏獒的圈子在国内的名声似乎尤其不好,不仅是由于曾经让天价藏獒走上“神坛”的“炒作”,还有后来被媒体大幅报道过的“高原流浪狗问题”。只不过在我这样一个涉世未深的“书呆子”眼里,獒圈里的争夺就还要带上一层更为浓烈的滤镜罢了。
与次仁为伍却是轻松的,虽然他的一部分观点我并不认同。他似乎离漩涡中心非常遥远,远在牧区的小县城,绝大部分时间置身事外。他的视野似乎不是面向内地,而是面向牧区的,那片从县城开车半小时就可以进入的、一望无际的、獒友们口中的“深”牧区。
他从深牧区找出了许多好狗,带回养殖场,因为他熟悉人、熟悉路、熟悉草原,不像内地獒友,得下定决心、翻山越岭才能进入藏区、进入牧区,开展所谓的“寻獒之旅”。而他,轻而易举就可以在牧区寻到大多数人寻不到的好狗。他没事就开着车在草原里转悠、打听,探索新的路线和角落,打量各村各乡、各家各户的狗。遇到中意的,就赶紧出钱拿下,赶在其他獒友发现之前,尤其是本地其他养殖户发现之前,带回自己的狗场。

- 黑河汇入黄河处
七年前的一天,次仁就是在这样一次探寻中,找到了加霍玛。
他早就听牧民朋友说过,在黑河汇入黄河的那个三角地带,有一条难得的好母狗,叫加霍玛,只是不知道她的确切位置。那地方到县城的直线距离其实不远,但由于两河汇流、水系复杂,且没有桥,得绕一个大圈子才进得去。他开皮卡车去过很多次,那里不仅是两河汇流,还是两省交界,基础设施残破。车开着开着,路就颠了起来,再开着开着,路就消失了,再开一会儿,可能就彻底开不动了,陷入泥潭。许多寻獒的人来到这里,只在有路的那几个牧民定居点周边晃一圈,就打道回府了。正因如此,次仁说这里的狗没太受到“外血”的“污染”。陆路难进,可黄河结冰的时候,这里的牧民却能在冰面上走来走去,与对岸的牧民来往。对岸的那个部落,据说正是“河曲藏獒的核心产区”,因此这个三角地带虽然偏远闭塞,却也出产公认的好藏獒。
他清楚地知道,要想找到那条母狗,就必须付出比别人多得多的耐心。他用空闲时间把整个三角地带摸了个遍。有一天,他在一户人家门前,发现了加霍玛。
那是一个冬天,加霍玛正卧在一堆干牛粪旁边,忙着生小狗。藏獒产仔都是在最冷的严冬,这似乎对幼崽的生长很不利,但若考虑到牧民秋季会大量屠宰,会产生许多牛羊肉和内脏,又似乎很合理了。小狗们在最冷的季节降生,却摄入最丰富的营养,次仁说这样的狗才最强壮,才是最好的护卫犬。
看到加霍玛的一瞬间,次仁就吃了一惊:怎么会有这么高大粗壮的母狗?简直比好多公狗还要大!他赶紧进屋拜访,与主人攀谈。之后又去了两次,就光聊。最后他慢慢地提出,想要买这条母狗。正好这家人当时缺钱,就以并不高昂的价格卖给了他。
他给我看过加霍玛的照片。以我浅薄的识獒阅历而言,我并不能看出这条狗优越在什么地方。但我直观地感到她长得挺好看的,头型、五官、四肢什么的,好像分布得挺和谐的,而且眼神里、姿态里似乎真的散发出一种威严的气度,虽然她是一条母狗。毛色是黄褐色,比较浅,并不像大多数藏獒那么深,但却属于藏獒中最普遍的一个类型:这样的狗都是躯体偏深色;四肢、胸口、下巴、嘴部以及尤其是双眼上方好像是眉毛的位置,则都是浅色。光看脸的话,就好像眼睛上面多长了一双眼睛。在内地獒圈,这样的花色被称为铁包金、铁锈红、铁包银等等。“包”是个很形象的动词,大面积的铁色“包”住了一些金色、或锈红色、或银色。就好像肉“夹”馍,只不过这种狗的不知道算“肉”还是算“馍”的部位,都是“贵金属”。
当然,这都只是内地獒圈的说法、汉语的说法。藏语完全没有对应的说法。在藏语里,这种花色叫“加”。

- 加霍玛
这个“加”字,就是我开头提到的那个“加”——རྒྱ,加莫的加,我那个加。首次发现这个巧合时,我惊讶极了:“所以……这种花色的藏獒是汉族的狗吗?!”我迅速做出了这样直白而荒谬的推理。“当然不是啦!”每一个向我解释这个字的人都说:
“你说的那是加切(རྒྱ་ཁྱི),哈巴狗。那的确是指汉族的狗,因为我们这边的宠物狗很多来自汉地。但作为一种花色的加(རྒྱ་བོ),或者说加加(རྒྱ་རྒྱ),跟汉族没关系。也没法直译成汉语。这种‘四眼’的狗都叫加加,‘四眼加加’(མིག་བཞི་རྒྱ་རྒྱ)。不只是狗,有的牛脸上混了两种颜色,也会被叫作加加。”
接着,我又学到了加这种花色内部更细致的分类:獒圈所谓的“铁包金”,在藏语里叫金加(རྒྱ་གསེར),“铁锈红”叫红加(རྒྱ་དམར),“铁包银”叫白加(རྒྱ་དཀར),还有灰色的叫灰加(རྒྱ་སྐྱ)等。甚至还有“四眼”的颜色比身上的毛色还要深的狗,那种叫黑加(རྒྱ་ནག)。
而这些颜色的叫法,也正是带有这些颜色的狗们在牧区的名字。通常一条红加色的狗,就会被命名为红加,一条黄加色的狗就叫黄加,如此等等。不只是加色的狗,至少在我待过的牧区,几乎所有狗的名字都是对其毛色、外形的普遍描述,是一个类别,一个种属,而非个体化的、专属的命名。比如一条纯黄色的狗很有可能叫“黄虎”,一条纯黑色的狗很有可能叫“黑熊”。在牧区,同一种类型的狗都叫同一个名字,所以重名的狗非常多。同一片草原中,可能就有许多条黄虎,许多条灰加,许多条黑熊。每一条狗的个体性很难从其名字直接反映出来。我不由想起了作为加莫的自己。
这条叫加霍玛的母狗也是一条加。加字是她身份中普遍性的部分,就如同她的姓。但与许多其他加色母狗不同的地方在于,她同时也是一条霍玛。“霍玛”(ཧོ་མ)二字给予了她独特的个体性,就如同她的名。“霍”(ཧོ)字其实是“坡”(ཕོ)这个字的安多口语发音,意思是男性,是“莫”(མོ)的反义词。而“玛”则是一个表示女性身份的后缀,所有的母狗名字都包含这个后缀。比如,黄加色的母狗就叫黄加玛。
所以“霍玛”两个字放在一起时,直观上就给人一种矛盾的感觉。怎么会既是男性又是女性呢?一条狗可以既是公狗又是母狗吗?其实这是因为,加霍玛是一条非常优秀的母狗,简直就跟公狗一样优秀了。所以她的名字里才有个表示男性的字,“霍”,意思是说她“就像公狗一样”。后面再加上表示女性的字,“霍玛”,合起来意思就是说:这是一条像公狗一样的母狗。加霍玛就是一条像公狗一样的加色母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