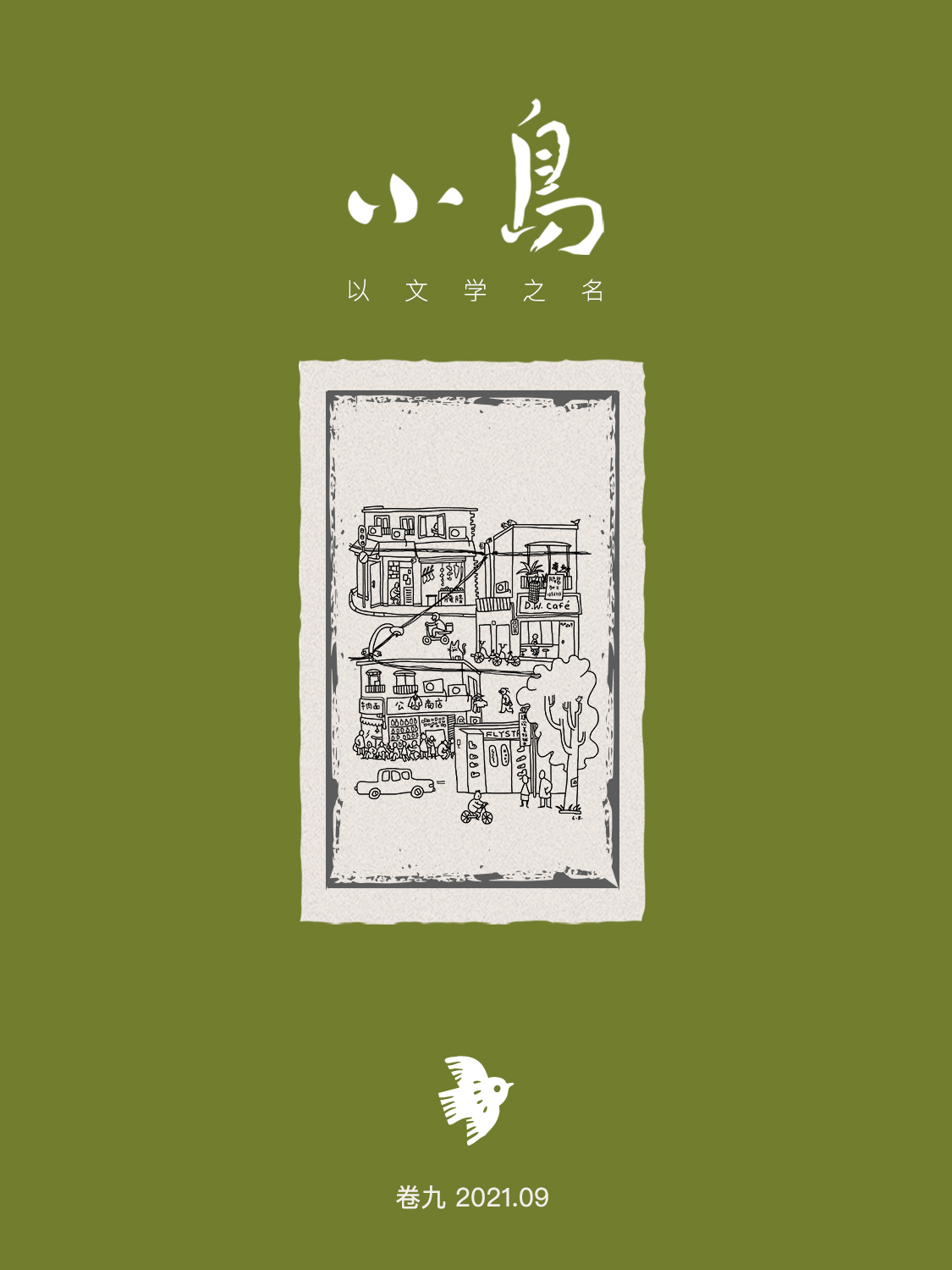从到达的那一刻起,弗雷德里克就受到了黛尔菲父母的热烈欢迎。这是她第一次带男人来见他们,事情很明显了。他们什么都想知道。大概要等下次来才会有所谓的“不强迫”说话。尽管一想到要提及自己的过去,弗雷德里克就会觉得尴尬,但此刻,他一上来就被关于他的生活、父母和童年的问题团团包围。他努力显得善于交际,回答的时候还穿插些趣闻轶事。黛尔菲有理由怀疑,那些故事都是他凭空捏造的,好让他的讲述比枯燥的现实更加生动。
热拉尔早已专心致志地读完了《浴缸》。一位出版了一本默默无闻的小说的作者遇上了自己的读者,而读者为了哄他开心,便不停地聊关于这本书的话题,这反倒挺让人郁闷的。当然了,对方是出于好意。但才刚安顿下来,在露台喝上第一杯开胃酒,面朝着令人心旷神怡的美景,弗雷德里克不禁感觉到有些尴尬,如此美妙的时刻却要谈论如此平庸的小说。他已渐渐从那部小说中走了出来,看到了其中的缺点,和那种过于求好的写法。就好像每一个句子都一定要证明作者有了不起的文采。第一部小说总是好学生写的。只有天才能上来就有那种懒学生的做派。不过,自然是需要一些时间,才能懂得叙述的缓急节奏,懂得隐藏在表面文字之下的内在情节要如何发展。弗雷德里克有预感,他的第二部小说会更好,他不住地这么想着,却没有告诉任何人。直觉说多了便不再灵验。
“《浴缸》是一部关于当今社会的绝妙寓言。”热拉尔继续道。
“啊……”弗雷德里克回应他。
“你写得很对: 过于丰富充足的物质生活一开始会让人迷惑。而如今,它却叫人想要放弃。什么都有,就等于什么都不再想要了。在我看来,这个等式恰当极了。”
“谢谢您。真是不敢当……”
“你就收下称赞吧。这里可不是每天都这样的。”他大笑说道。
“您受到了罗伯特·瓦尔泽的影响,不是吗?”法比妮接话道。
“罗伯特·瓦尔泽……我……是的……是这样,我很喜欢他。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但您说的当然是对的。”
“你的小说让我尤其想到他的短篇小说《散步》。在谈论闲逛这件事上,他有种了不起的天赋。瑞士作家是最会描写无聊和孤独的。你的书里也有这种东西: 你让空虚变得生动。”
“……”
弗雷德里克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他有多久没遇见过这样的善意和关爱了?寥寥几句话,他们就抚平了大众的不理解给他留下的伤痕。他看向黛尔菲,是她改变了自己的生活。她给了他一个温柔的微笑,而他心里想,他很想要看看那张床,那张没有任何男人到过的床。在这里,他们的爱情似乎又升华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在初见面热切的谈话之后,黛尔菲的父母不再向弗雷德里克提太多问题。一天天过去,他在这个陌生的地方快乐地写作。早上,他专心致志地写小说,下午,他与黛尔菲一起散步,他们信步闲逛在这片土地上,一个人也不会遇到。这里是适于忘记一切的所在。她也喜欢一路走,一路向他讲述自己少女时代在这里留下的印记。过去一点点拼凑起来,现在,她生命中的每一个时刻都铺展在弗雷德里克面前,他可以在所有的时光里去爱她了。
空暇时,黛尔菲会与孩提时代的伙伴们重聚。这是一种特殊的友谊: 他们在特定的地方才显得格外亲密。要是在巴黎,她与佩里克或者苏菲也许就没话好聊了,他们已经变成了如此不同的人,但在这里,他们可以聊上几个小时。每个人都讲述自己这些年的生活。大家向黛尔菲打听她遇见的名人的事。“许多人都很肤浅。”她言不由衷地说道。人们总是讲别人希望听到的话。黛尔菲知道,儿时的朋友们希望听到她批评巴黎;那会让他们感到宽慰。她和他们在一起慢悠悠地聊着,只有一件急事挂在心上:回去见弗雷德里克。她很开心,他在布列塔尼能如此自在舒心地写作。她向自己的朋友们推荐他的小说。
“有口袋本吗?”
“没有。”黛尔菲结结巴巴地说。
尽管她的影响力日益扩大,但仍没办法说服任何人去再版这部销量一塌糊涂的小说。没有任何客观的理由可以证明,便宜些的价格就能扭转《浴缸》在市场上的命运。
黛尔菲想要转换话题,聊聊她此行带回来的小说。得益于新科技,她不需要再在假期里吃力地拖着成箱的书稿旅行。这个八月,她有二十几本书稿要看。全部书稿都存在电子阅读器里。大家问她这些小说都讲了些什么,可大部分时候,她也没办法说出个大概。她没读到什么让人印象深刻的作品。但她依然在每次开始阅读一本书稿的时候都激动不已。要是这一本很棒呢?要是能就此发掘一个新作家呢?这份职业总是能最大程度地调动她的激情,她怀抱着孩子般的热情投入工作,就像在找寻藏在花园里的巧克力。而且,她还很喜欢重新审校那些已经出版的书稿。她至少看了十几遍《浴缸》。当她真的喜欢一部小说的时候,一个逗号的去留都会牵动她的心绪。
这天晚上的天气好极了,他们决定露天吃晚餐。弗雷德里克帮忙摆了桌子,很是开心,觉得自己终于能派上点用场。这心情说来有些荒谬。当作家们想到自己能完成一项家务,就会感到非常高兴。他们的灵魂总是虚无缥缈地游荡,需要一点实实在在的快乐来平衡一下。黛尔菲与父母聊了很多,这让她的伴侣十分着迷。他们之间总是有那么多话可讲,他想。他们的对话永远不会有冷场,总是一句接着一句。眼前的场景让弗雷德里克越发意识到自己与父母之间的沟通障碍。他们到底读过他的小说吗?应该没有吧。母亲很想改善和他的关系,但由来已久的疏远很难再去弥补。毕竟,他已经很少再想到父母。他有多久没和他们说过话了,他真的说不出来。小说的失败让他更不愿意接近他们。他不想看到父亲鄙夷的眼光,父亲定会向他历数所有那些大获成功的小说。
弗雷德里克甚至不知道这个夏天他们在干什么。在他看来,他们俩能待在一起已经够奇怪的了。分开二十年之后,他们最近又生活在了一起。他们到底是怎么想的?无法理解自己的父母,这一定算是一个成为小说家的好理由。可以想象,他们尝试了各自生活,但发现并没有过得更好,因此又回到原点。童年时,弗雷德里克总是得拖着行李不停地两边往返,这让他很是痛苦,而如今没有了他,父母却重新过上了共同的家庭生活。他应该为此感到愧疚吗?真相也许更为简单: 他们只是害怕孤单。
他们到底读过他的小说吗?应该没有吧。
弗雷德里克停下了思绪(他已经走神多久了,谁也说不上来。人类有这种独特的能力,可以一边想别的事情,一边装作全神贯注地听着别人的谈话,还会不时点头应和。这也是为什么永远都不要指望能在任何人的眼神里读到他真实的想法。——原注),重新回到当下的谈话之中。
“你还没读厌那些稿子吗?”法比妮问女儿。
“没有,我非常喜欢。但最近,我真的有点累了,没读到什么特别有趣的。”
“那《浴缸》呢?你当时是怎么发现它的?”
“很简单,弗雷德里克寄来了书稿。我在翻堆书稿的办公室时注意到了它。我被题目吸引了。”
“其实,我是把书稿放在了接待处,”弗雷德里克补充道,“我去了好几家出版社,但心里并不大信这一套。我完全没有想到会有人第二天早上就给我打电话。”
“进展这么迅速是很少见的,不是吗?”热拉尔问,他总是很积极地参与谈话,就算实际上并没有那么感兴趣。
“当然,我们很少那么快给出反馈。并且,也很少那么快就出版。在格拉塞,邮寄来的小说里,一年只有三四部能被出版。”
“一共能收到多少部呢?”法比妮问道。
“几千部。”
“我想,应该有人负责退稿吧。这工作量可不小。”热拉尔轻声说。
“一般来说,是由实习生寄出一份统一格式的信件。”黛尔菲解释道。
“啊对,著名的退稿信:‘尽管您的稿件质量很高……但我们遗憾地通知您,贵作并不符合我们的出版风格……顺祝……’出版风格,这可真是个好借口啊。”
“你说得对,”黛尔菲对母亲说,“而且,其实所谓出版风格根本不存在,不过是个借口。只要看一眼我们的出版目录就知道,我们出的书什么类型都有。”
对话出现了短暂的冷场: 德斯佩罗家极少出现这样的现象。热拉尔趁机又给每个人都倒了一杯红酒;已经是这个晚上的第三杯了。
法比妮接过话头,讲了一个发生在当地的小故事。
“好几年前,克罗宗图书馆的馆长兴起一个念头,要收集所有被出版社退稿的书。”
“是吗?”黛尔菲十分惊讶,她竟然从来没听说过这件事。
“是的,我想这项计划的灵感来自一家美国图书馆。我对细节不是很确定。我只记得那时候,大家纷纷谈论这件事。人们觉得这件事很好笑。有人甚至说,这是一个文学废品回收站。”
“这个说法很蠢,我觉得这是个好主意,”弗雷德里克打断道,“如果没有人想要我的书,我也许也会希望它至少能被一个地方接收。”
“现在还在进行吗?”黛尔菲问道。
“是的。我不觉得还非常活跃,但几个月前,我去图书馆,看到最靠里的所有书架都还是专门留给退稿的。”
“那里该供奉了多少草包圣人啊!”热拉尔开玩笑道,但似乎并没有人欣赏他的幽默。
弗雷德里克知道,他应该留给母女俩单独对话的空间。他给了黛尔菲一个心照不宣的微笑,不过没有太明显地笑出声来。热拉尔收敛起戏谑的语气,承认他觉得这个想法很荒谬。身为一名数学老师,他没法想象能有个地方专门用来保存那些失败的科学研究,或者是没有生效的专利。成功和失败之间本应泾渭分明。他还有另外一个没那么奇怪的比喻:“要是在爱情里,这就好像是一个女人拒绝了你,但还是允许你和她不清不楚。”黛尔菲和法比妮并不是很懂这个类比,但仍然大大赞扬了这个理性男人的感性发言。科学家们有时候会喜欢这些诗意的隐喻,它们是那么精彩,正如四岁孩子写出的诗篇(该睡觉了)。
一躺到床上,弗雷德里克便抚摸起黛尔菲的双腿,先是小腿,然后是大腿,最后将一根手指停在她身体的某一点:
“如果我把手放这儿,你会拒绝吗?”他呢喃道。
第二天早上,黛尔菲向弗雷德里克提议一起骑车去克罗宗,实地看一看那家图书馆。通常,他至少要工作到下午一点钟,但他同样也十分迫切地想要一探究竟。真切地感受一下别人的失败也许会让他好受一些。
玛嘉利仍旧在图书馆工作。她胖了不少。她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也就任由体重增长。她并不是在两个儿子出生后立即变胖的,而是在好几年之后。或许,在领悟到她会一辈子待在这里,做这份工作直到退休的那一刻,她就对外表放弃了追求。而当她发现,她多长的体重实际上并没有让丈夫觉得不舒服,也就继续听之任之,最后简直都要认不出自己来了。他对她说,无论她的身体如何变化,他都会爱她,她本可以从中得出结论,认为他深深地爱着自己;但其实,她已看出,他只是漠不关心。
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变化:年复一年,她对于文学更加内行了。开始这份职业时,她不过是误打误撞,对书本毫无兴趣,如今却能为读者提供咨询服务,带他们去找自己需要的书。她逐步改造了这个地方的面貌。她为青少年开辟出一块宽敞的专用区域,并为想要高声朗读的读者设立了休闲室。她的儿子们已经成年,常常在周末来搭把手。这两个大块头像父亲一样,也在雷诺修理厂工作,他们会蜷着身体,为孩子们读《想要知道是谁把粑粑拉在它头上的小鼹鼠》。
不再有什么人为退稿图书馆而来,连玛嘉利自己都快忘了它的存在。有时候,会有看起来有些鬼鬼祟祟的人进门,害羞地说没人想要他的书;同样没被出版的作家的朋友的朋友告诉他,这里有地方可以收留它。在这个梦想幻灭者的群体里,消息悄悄地流传着。
年轻的情侣踏进图书馆,黛尔菲自我介绍,说她住在莫尔加。
“你是德斯佩罗家的女儿吗?”玛嘉利问道。
“是的。”
“我记得你。你小的时候常来这里……”
“是的。”
“其实,主要是你母亲常来帮你借书。不过,你不是在巴黎的出版社工作吗?”
“没错,说的就是我。”
“你可以免费帮我们弄些书来吗?”玛嘉利问道,她有着与自己的文雅气质不相称的商业头脑。
“呃……当然了,我会去看看我能做些什么。”
“谢谢。”
“不管怎么样,我可以给您推荐一部特别棒的小说——《浴缸》。您可以免费拿到几本。”
“哦对,我听说过这本书,似乎写得很差。”
“不,一点都不差。正好,我来给您介绍一下作者。”
“哦,对不起。我真是一出口就是蠢话。”
“别担心,”弗雷德里克安慰她,“我有时候也会没读过就凭空说一本书很差。”
“我会好好读的,并把它放在前排书架。毕竟,在克罗宗,不是每天都有大明星大驾光临。”玛嘉利努力找补。
“大明星,也有点夸张了吧。”弗雷德里克嘟哝了一声。
“怎么样都是被出版了嘛。”
“对了……”黛尔菲插话道,“我们过来见您,是因为我们听说这里有个有些特别的图书室。”
在这个梦想幻灭者的群体里,消息悄悄地流传着。
“我想你说的是存放退稿的那个吧。”
“没错。”
“在大厅最里面。我把它保留下来是为了向创立人致敬,但那儿差不多就是一堆废纸吧。”
“是的,当然了。不过我们喜欢这个主意。”黛尔菲说。
“你这么说古尔维克一定会很开心,是他创立了这个图书室。他喜欢有人对此感兴趣。可以说,这是他一生的心血。他将他人的失败转换为了自己的成功。”
“这真是太美了。”弗雷德里克总结道。
玛嘉利不经意地说出了这句富含诗意的话;她让小情侣自己走去存放退稿的区域。她想,她已经很久没有清理过那些书架上的灰尘了。
几天之后,黛尔菲和弗雷德里克又回到了图书馆。读那些莫名其妙的书稿让他们很是开心。他们会在看到一些书名时发出爆笑,但也会因为一些私人日记而感动不已,尽管写得蹩脚,其中的感情却是真真切切的。
不知不觉,他们就在这里待了一整个下午。傍晚时,黛尔菲的母亲焦急地在花园里等待着。终于,在太阳下山之前,她看到小情侣回来了。他们从远方出现,自行车车灯在他们身前闪烁。她立即认出了女儿,她总是一丝不苟地笔直前行。那条有点紧张和机械的光线后面就是她。而弗雷德里克的车灯光线则更有艺术家气质,他随意散漫地骑着车,并不沿着既定的轨道向前。可以想象,他一路上都这里那里看个不停。法比妮心想,他们真是天生一对: 他们是现实和幻想的结合。
“对不起妈妈,我们的手机没电了。并且我们被耽搁了。”
“被什么耽搁了?”
“被一件非比寻常的事情。”
“发生了什么?”
“咱们先把爸爸也叫来吧。所有人都得在。”
她以郑重其事的语气说出了最后这句话。
几分钟后,在喝开胃酒时,黛尔菲和弗雷德里克讲述了他们在图书馆度过的这个下午。他们轮流发言,相互补充各种细节。感觉得到,他们想要尽可能讲得久一些,将悬念留到最后。他们讲到那些让他们乐不可支的书稿,特别是最猥琐或者最离奇的那几本,例如《自慰与寿司》,那是一首对生鱼片的色情颂诗。父母坚持要他们讲快一些,但无济于事,他们偏要选择弯弯曲曲的小径,时不时还停下来欣赏一下路边的风景,他们的故事俨然成了一段慢悠悠、乐滋滋的旅途。直到突如其来的转折:
“我们发现了一部杰作。”黛尔菲宣布。
“啊,是吗?”
“一开始,我告诉自己,有几页不错,这也不是没可能,但接着,我就被故事给吸引住了。我没法放下这本书,在两个小时里一气读完。我完全被打动了。而且,作者的文笔是那样奇特,既简洁又充满诗意。我一看完就给了弗雷德里克,我从来没见过他那个样子。我觉得他看得入了迷。”
“是的,就是这样。”弗雷德里克证实她说的话,他看起来好像还没从震惊中缓过来。
“这本书是讲什么的?”
“我们把书稿借出来了,你可以读一读。”
“你就这么把它拿出来了?”
“是的,我觉得没人会有意见。”
“那么,故事的主题是什么?”
“书名叫《爱情故事的最后时分》。妙极了。故事讲的是一段就要结束的感情。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主人公情侣不能再继续相爱下去。这本书讲述了他们在一起的最后时光。但这本书的非凡之处在于,作者在同时平行叙述了普希金的临终时刻。”
“是的,普希金在一场决斗中受伤,”弗雷德里克继续道,“他在死前深受折磨。将一段爱情的结束与俄罗斯最伟大的诗人的临终痛苦结合在一起,这是个无与伦比的想法。”
“而且,这本书以这句话开始:‘没有读过普希金,便无法理解俄罗斯。’”黛尔菲补充道。
“我简直等不及要读这本书了。”热拉尔宣布道。
“你?我以为你不怎么喜欢读书呢。”法比妮说。
“是,但这本书让人想读。”
黛尔菲打量着父亲。此时,她是以编辑而不是女儿的目光看着他。她立即明白,这本小说能够打动读者。并且,当然了,发掘它的故事也会让书的出版成为一个绝妙的话题。
“作者是谁?”母亲问。
“我不知道。他叫作亨利·彼克。书稿上写着他住在克罗宗。找到他应该很容易。”
“我对这个名字有印象,”父亲说,“我在想,是不是开了很长时间披萨店的那个家伙。”
小情侣盯着热拉尔。他不是一个会弄错事情的人。他所说的听起来很不真实,但这整一趟奇遇都是如此。
第二天早上,黛尔菲的母亲也读完了书。她认为故事情节非常美,并且相当简洁,她又补充了一句:
“的确,因为有平行发展的普希金垂死之际的故事,小说展现出一种悲剧的力量。我在别处从来没听说过这个故事。”
“法国人对普希金所知甚少。”黛尔菲回应道。
“他的死竟是这样荒谬……”
法比妮还想多聊聊这位俄罗斯诗人和他的临终境遇,但黛尔菲打断了她,想要谈一谈小说的作者。她一整个晚上都在想这个人。是谁能够写出这样一部书但又无人知晓呢?
找到这个神秘男人的踪迹并不复杂。在谷歌输入他的名字,弗雷德里克发现了两年前的一则讣告。所以,亨利·彼克永远都不会知道,他的书会拥有如此热情的读者,其中还有一位女编辑。应该去见一见他的亲友,黛尔菲想。讣告中提到,他有妻子和一个女儿。那位遗孀住在克罗宗,她的地址黄页里就有。这称不上是一场多复杂的调查。
玛德琳·彼克刚过八十岁,在丈夫去世后便一个人生活。四十多年来,他们一同经营一家披萨店。亨利负责后厨,她在前厅服务。他们一辈子的生活作息都跟随着餐馆的节奏。退休彻底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但他们的身体的确已经跟不上了。亨利得了心脏病。之后,他只得违心地卖掉餐馆。有时,他会以顾客的身份回到披萨店。他向玛德琳坦承,当时的心情就像是一个离了婚的男人,看着前妻和新任丈夫在一起。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他变得越来越忧郁,对一切都漠不关心,对什么事都提不上劲儿来。妻子一直都比他要活泼合群,此时也毫无办法,只好眼睁睁地看着他日渐消沉。一次,他在雨中走的时间有些太久,几天以后,就在自己的床上离开了人世;这貌似是因为不够谨慎,但很难说是不是一次伪装好的自杀。在去世的床上,他看起来很是安详。如今,玛德琳大部分时间都一个人待着,但从来不会觉得无聊。有时,她会坐下来刺绣,她觉得这种消遣挺可笑的,但同时又做得不亦乐乎。在她绣一块桌布的最后几针时,有人敲了门。
她打开门,毫无慌张的神色,这让弗雷德里克很惊讶。这个地方的人好像从来不会害怕有坏人闯入。
亨利·彼克永远都不会知道,他的书会拥有如此热情的读者
“您好。很抱歉打扰您了。您一定是彼克太太吧?”
“是的,要是没有别人的话,就是我了。”
“您丈夫叫作亨利?”
“直到去世前,他都是叫这个名字。”
“我叫黛尔菲·德斯佩罗。我不知道您是不是认识我的父母。他们住在莫尔加。”
“是的,也许认识。我开餐馆的时候见了那么多人。不过我的确有印象。你小时候是不是扎着辫子,骑一辆红色自行车?”
“……”
黛尔菲哑口无言。眼前的女人怎么能清楚记得这样一个小细节?一点没错,说的就是她。那一瞬间,她恍惚又变回那个扎着辫子、骑红色自行车的小女孩。
他们走进客厅。那里有台存在感很强的时钟,一直滴滴答答地走个不停。但玛德琳已对此听若无闻。每一秒的声音都已经与她的日常融为一体。到处散落的小玩意儿让这儿俨然像个布列塔尼纪念品商店。在这座房子里,人们一秒钟都不会怀疑自己身在别处。这里散发着布列塔尼的本地气息,没有一点点外出旅行过的痕迹。当黛尔菲问这位老妇人是否偶尔会去巴黎,她的回答不留一点情面:
“我去过一次。简直是个地狱。人潮拥挤,压力巨大,臭气熏天。而且说实话,那个埃菲尔铁塔,人们总是大肆宣扬,我完全理解不了。”
“……”
“我给你们拿点什么喝的吧?”玛德琳又说。
“好的,十分感谢。”
“你们想要什么?”
“都行,看您方便。”黛尔菲回答道,她已经看出来,最好不要得罪这位女主人。玛德琳去到厨房,将客人留在客厅。小情侣彼此尴尬地对视了一会儿。玛德琳很快就端了两杯焦糖茶出来。
出于礼貌,弗雷德里克喝下了他的茶,尽管他其实十分讨厌焦糖的味道。他在这间屋子里并不自在,这里让他透不过气来,甚至有些害怕。他觉得,在这里发生过什么可怕的事情。这时,他注意到壁炉上挂的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个神情忧愁的男人,蓄着茂密的胡子。
“这是您的丈夫吗?”他轻声问。
“是的。这是一张我很喜欢的照片。他看起来很开心。而且他在笑,这可很少见。亨利不是个外向的人。”
“……”
她的回答可谓是相对论的实证:在这张照片上,两个年轻人找不出一丝微笑的痕迹,连一点开心的神色都没有。相反,亨利的目光里蕴含着深沉的忧伤。然而,玛德琳继续评论着丈夫的快乐,在她看来,这是一种不同于流俗的快乐。
黛尔菲不想催促女主人,觉得最好先让她随意聊一聊,聊聊她的生活、她的丈夫,然后再点出此行的主题。玛德琳谈到了他们过去的工作,聊到亨利投入在餐馆里准备一切的时间。其实也没什么重要的事好讲,她最后不得不承认道。时间过得太快了,就是这样。一开始,她说话的语气有些淡漠,但突然之间,她动了情。因为她意识到,自己从来没有谈论过亨利。去世后,他消失在了各种谈话和日常生活之中,甚至或许已从大家的记忆中抹去。于是,她开始任由自己吐露心声,这并不是她往常的习惯;她甚至没有问问自己,这两位坐在她客厅里的陌生人到底为什么要来听她讲亡夫的故事。当某件事情让人觉得自在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去寻思它的由来。慢慢地,一个男人的轮廓被勾勒了出来,他的一生过得平凡无奇、谨小慎微。
“他有什么爱好吗?”在片刻的空白之后,黛尔菲问道,她想加快一下节奏。
“……”
“您有没有在披萨店里见过一台打字机?”
“什么?打字机?”
“是的。”
“没有。从来没有。”
“他喜欢读书吗?”黛尔菲又问。
“读书?亨利?”她微笑着回答道,“不,我从来没见他读过一本书。除了电视节目单,他什么也不读。”
两位访客的神情惊讶至极,但同时又透着一股兴奋。面对客人的沉默,玛德琳突然补充道:
“说起来,我又想到了一个细节。我们出让披萨店的时候,花了好些日子去整理。这么多年来,我们堆了那么多东西。我记得在地下室看到了一个装书的纸板箱。”
“所以您觉得,他会在您不知情的情况下在餐厅里读书?”
“不。我问他那是什么,他说那是这么多年来顾客们忘在店里的书。他把书都放在那里,以备他们回来找。当下我觉得有些奇怪,因为我不记得有顾客把书忘在桌子上过。但我不是总待在那里。打烊后,我常常先回家,留他收尾。他在餐馆的时间比我要多得多。他早上八九点钟就会到,半夜才回家。”
“是的,那是很长一段时间。”弗雷德里克评论道。
“亨利很高兴能够那样。他喜欢没人打扰的早上。他会准备面团,会想着如何更新菜单,免得顾客厌倦。他喜欢创造新的披萨。他觉得给它们取名字很有趣。我记得有碧姬·巴铎,还有一款有红辣椒的叫斯大林。”
“为什么是斯大林?”黛尔菲问。
“哦,我也不大清楚。他常常会异想天开。他很喜欢俄罗斯。确切地说是俄罗斯人。他说,这是个骄傲的民族,有些像布列塔尼人。”
“……”
“抱歉,我要去医院看一个朋友了。我现在外出都是这样的行程。医院、养老院或是墓地。奇妙的三点一线。不过,你们是为什么想要见我来着?”
“您马上就得走吗?”
“是的。”
“这样的话,”黛尔菲失望地说,“最好还是等下次见面吧,因为我们要跟您说的事情得花点时间才能讲清楚。”
“啊……您把我搞糊涂了,不过我真的得走了。”
“谢谢您费心费时招待我们。”
“不客气。你们喜欢焦糖茶吗?”
“是的,谢谢。”黛尔菲和弗雷德里克异口同声道。
“那就好,因为这是别人给我的,我一点儿也不喜欢。所以我努力在有客人的时候甩掉它。”
看着两个巴黎人的惊讶神色,玛德琳补充道自己在开玩笑。随着年岁渐老,她意识到,不再有人觉得她还能玩幽默。老人家就应该阴阴沉沉、糊糊涂涂的,连一句机灵话都不会说。
离开的时候,黛尔菲问她是否还能再见面。玛德琳戏谑着说道,她现在随时都能约会,他们希望是什么时候就是什么时候。他们约定第二天见面。这时,老妇人走近弗雷德里克:
“您看起来脸色很差。”
“啊,是吗?”
“您应该在海边多散散步。”
“您说得对。我出门时间的确不够多。”
“您是做什么的?”
“我是写小说的。”
她惊愕地看了他一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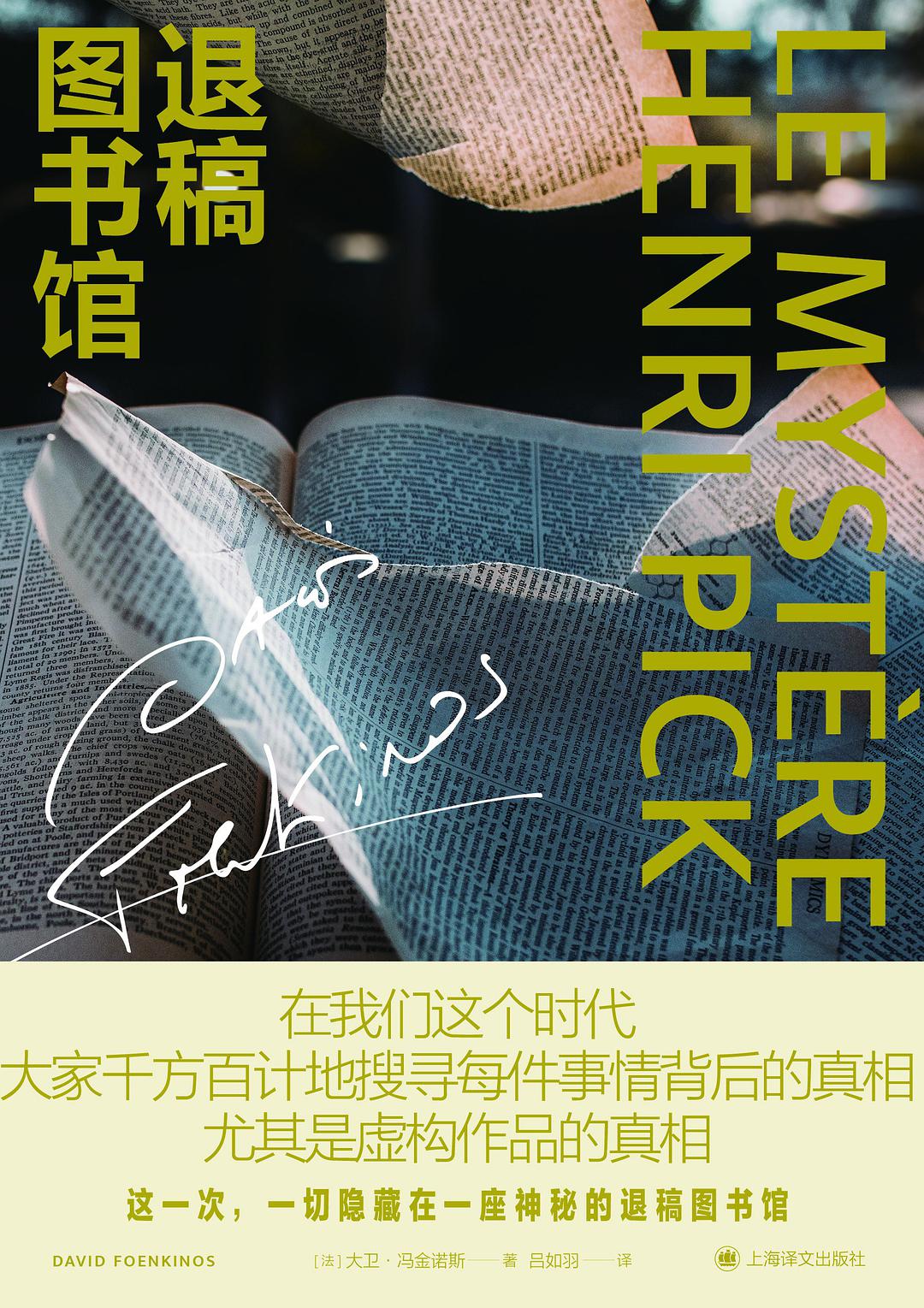
本文摘自《退稿图书馆》
[法]大卫·冯金诺斯
吕如羽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1 年 6 月
题图来自 Asal Lotfi on Unsp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