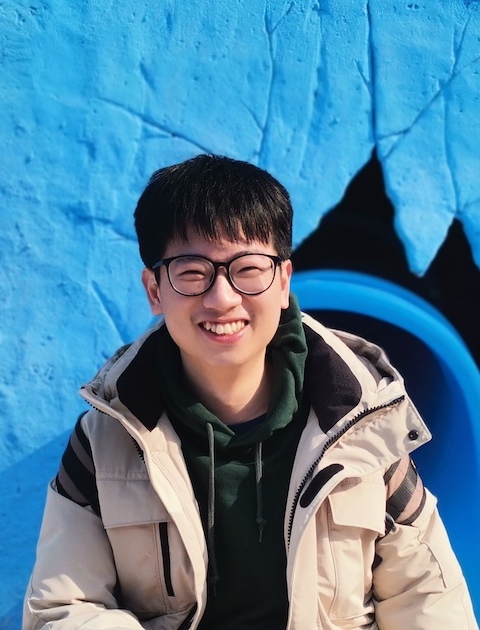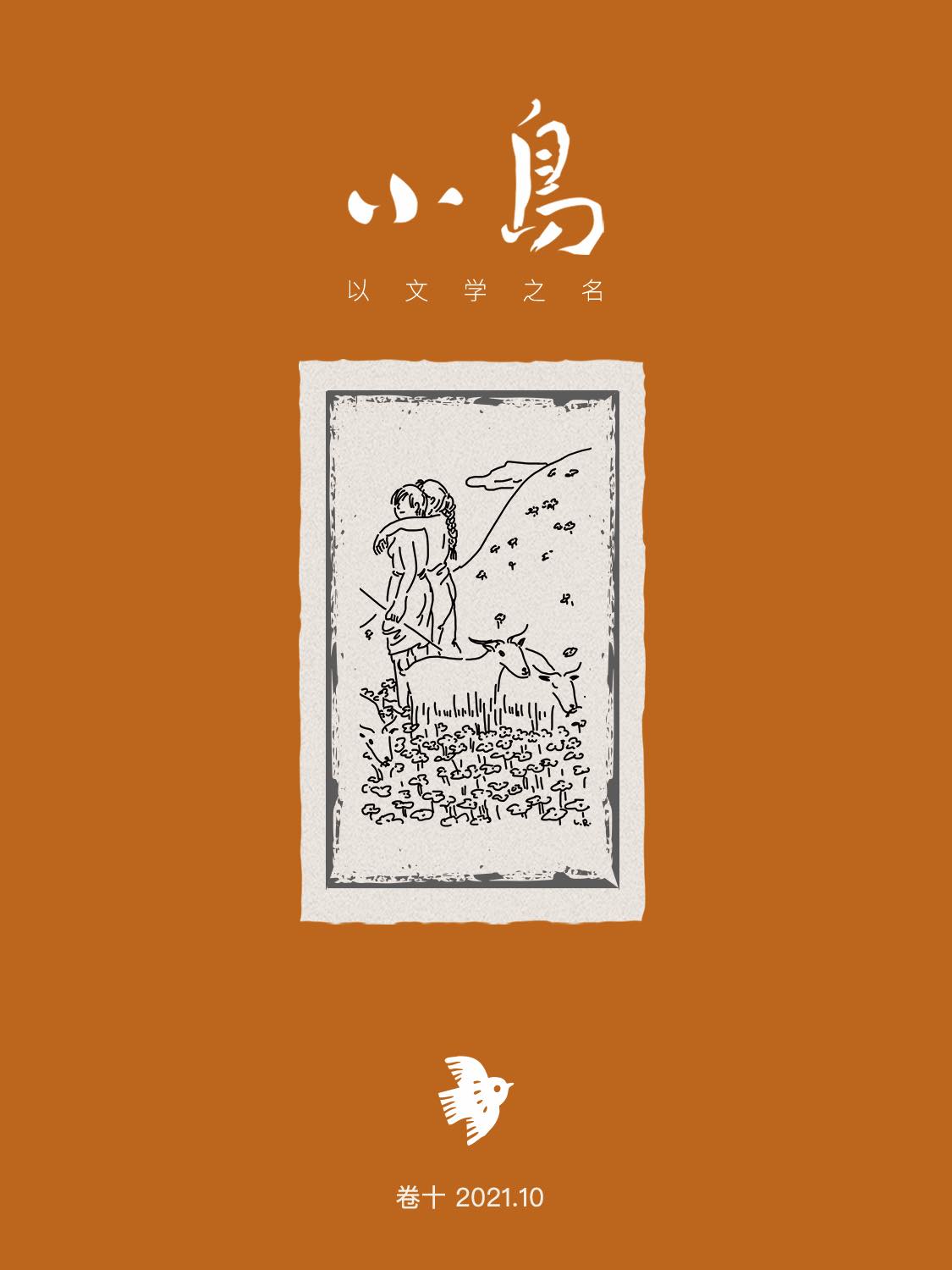1970 年,不到 20 岁的许成钢在北大荒建设兵团被打成“反革命集团”的“头目”,被关押、审讯、批斗以及监督劳动管治。在监督劳改过程中,他自学高中和大学本科的数学、物理、英语、电子工程教材,还搞了不少技术创新。到 1977 年,他获得平反,但只能是无业游民。之后他有考入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成为该校唯一没有本科学历的研究生。
许成钢称,这十年,他从阶下囚到被平反,再到所谓“科举及第”,成为人生中最重要的转折。事实上,他一生对制度问题的探索从没离开过“文革”。早在 1967 年,身为清华附中初中二年级学生的他,就因无法理解亲身经历和目睹的社会现象,产生探索制度根源的强烈兴趣,于是主动离开北京前往黑龙江农村。这才有了后来的坎坷经历。
1982 年从清华毕业后,许成钢被分配到了中国社科院正在组建的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工作。两年后,经所在单位推荐和哈佛燕京学社资助,他得以赴哈佛大学经济系访问,后转为博士研究生,师从诺贝尔奖经济学家埃里克·马斯金和匈牙利经济学家雅诺什·科尔奈,接触到了激励机制理论和转轨经济学,成为他后来的研究方向。
1991 年博士毕业后,许成钢先去了伦敦经济学院工作,后在香港大学、清华大学、首尔大学等大学任教,于 2013 年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奖,2016 年获得首届中国经济学奖。他的研究涵盖中国改革机制及其制度原因、苏联和东欧转轨失利机制、计划经济体制对技术革新的影响、中国乡镇企业的发展等,提出了不完备法律、分权式威权制等具有影响的学术概念和分析框架。
现在,71 岁的他是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和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及伦敦经济学院的客座教授。他正在写作一本题为“制度基因”的著作,希望在更长的历史时段和跨国比较的视野内理解中国现代制度的历史根源和演变。许成钢称,这本书预计 2022 年完成、2023 年出版,英文版是在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中文版是在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对我来说,弄清楚社会制度问题,就像爬山的人要爬珠穆朗玛峰,做自然科学的人要弄清楚自然现象一样,具有很大诱惑力。”他说。
2021 年,许成钢出版了第一本中文著作《探索的历程》。这是预计四卷本的《许成钢文集》的第一卷,收录的多是曾发表于媒体的非学术和半学术文章。他希望这些文章不仅可以启发对社会科学感兴趣的读者,也能帮助更广大的读者了解自己以及父辈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启蒙的历程。
在《探索的历程》中,最为打动人的是许成钢回忆自己、父母、师友的文章。比如他称,自己在“文革”期间一度处于极度悲观状态,觉得人生不值得活,最后很大程度上是靠探索的愿望才支撑下来。当时,他抓紧一切时间自学。有一次,所在农场有知青因意外去世,需要有人在晚上看护尸体。很多人都怕,但他主动报名,觉得这是脱产学习的好机会。于是,他每晚在仓库打着一盏油灯,在尸体旁边认真自学英文版《模拟计算机原理》的教材。
许成钢说,父母对他的人生有深刻影响。父亲许良英是科学史家,母亲王来棣是中国近代史家。他们在大学教书和学习时曾是地下党的干部。在反右运动中,两人均受打击。许良英被打为中科院第一“右派”,因抗拒强迫劳改的处置,被开除公职,被迫回到农村老家劳动改造,一去就是二十年。王来棣则因当时拒绝驱赶丈夫离家被开除党籍、行政降级、取消研究党史资格。
但是,在劳改期间,许良英组织编译了三卷本的《爱因斯坦文集》。这套书在“文革”结束后出版,使得爱因斯坦的科学、民主精神影响了几代中国人。许成钢深受爱因斯坦观念、精神和方法论的影响。他从中认识到,最深刻学术研究的基本动力,是研究者对学术探讨无止境的好奇心,而不是在竞争在取胜。
父母去世后,出版遗著《民主的历史》。在精神和学术意义上,许成钢最近十年研究中国制度的历史根源和宪政也是他们工作的延续。
除了父母,对许成钢的学术和人生有着深刻影响的人中不得不提的还有导师科尔奈。这位被看作匈牙利社会主义改革的策划者和设计师、经济思想史中独树一帜的理论家,在许成钢眼中,更像是一个亲切又严厉的父辈,有着父辈般的关怀和激励。
比如在 2009 年芬兰赫尔辛基附近一个小岛上,科尔奈和许成钢边走边谈了一个多小时。当时,科尔奈直率批评许成钢的一篇论文太过看重经济发展,认为中国面临远为重要的问题是其政治制度对将来的影响。“他说,你自己知道这一点,但是你的读者不一定知道,作为一个诚实的学者,你必须要让你的读者知道,让你的读者知道那些你知道但他们不一定知道的事。这次长时间的谈话还深入许多具体的细节,远远超出一篇论文的范围,至今影响着我的研究工作的基本方面。”许成钢回忆。
2021 年 9 月底,我通过视频见到远在伦敦的许成钢教授。他诚恳、耐心地向我讲述自己一生探索历程的几个重要节点和感受,也分享了他思考制度问题的演进过程、正在写作的“制度基因”这本书的部分内容,还有对分权式威权制和东北限电、软预算约束和恒大危机等问题的看法。
以下是经过编辑的访谈节录。
01
亲身体验中、美、英的不同制度
小鸟文学:《探索的历程》这本书,我是先读下篇的“思想之路和师友”,再读上篇的“经济学和科学”,对你及其父辈、师友的经历深受触动,也更加理解你一生探索“制度”问题的根源。你在书中提到,1970 年在北大荒的因言获罪和 1979 年考入清华机械系读研究生是一生最重大的两个转折点。如果让你现在回看这两个转折点,比较大的感受是什么?除了它们,后来你觉得还有什么重大人生转折点可以讲讲吗?
许成钢:第一个转折点是“文革”期间,我被打成反革命关起来。为什么这是个转折点?有两重含义。第一重含义是对这个社会认识的转折点。因为在这之前,虽然我的探索兴趣是想要理解为什么这个制度会产生文化革命,但是比较抽象,没有意识到这个制度里边非常重要的内容,直到被打成反革命,被关押、审讯。
在审讯时,有一个核心问题反复出现,本来我只是在探索,只是找一些同学讨论,都是书本和抽象讨论,但被关押时,专案组有意识地要改变问题性质,变成所谓的反革命集团罪,强迫你承认你在组织反革命集团。这是对这个制度很重要的认识转变。原本是书本讨论,看马克思的著作等。在实际中,在亲身体验中,才知道在这个制度中,人们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为什么最关心的问题是这些。这是书本里很难学到的。
第二重含义也非常重要,因为当时我有一个感觉,我可能会一辈子是反革命,一辈子就会被关在这里了。我所有的书和写的东西全都被没收,根本丧失自由,所以我感觉我可能一生不再有可能探索社会问题。但是,那时有一种理想主义教育留下来的重要成分,就是要为社会做贡献。如果你不可能探索社会问题,而且是反革命,还有没有可能为社会做贡献?
“文革”之前,我的兴趣是工程,而且已经自学电子工程,觉得也许我唯一剩下可能做一些贡献的就是在电子工程和自动控制方面,搞些发明、技术革新。但是,我过去只念过初中二年级,只靠自学读过中专水平的电子工程教材和做过一些简单设计,所以为了搞发明和技术革新,我就开始自学数学、物理、英语等。在自学过程中已经开始搞发明、设计。这个自学过程非常重要。因为在这之前,我对社会科学的理解比较窄,只限制在马克思主义范围,这个自学内容的转变使得我全力以赴自学数学、物理、工程和英语,对我后来的研究工作奠定重要基础。
有直接对制度的体验,重要性不低于学术训练。
第二个重要转折是我进入清华念研究生。因为我是 1970 年被打成反革命,一直到 1976 年才正式得到平反。即便平反,我也只是一个无业游民,进入清华大学是我正式被承认进入学术界的第一步。这是非常大的变化。我在清华毕业之后,进入社科院正在组建的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从此正式进入了社会科学的研究机构。相比进入清华,这就是比较小的变化。
以后到美国留学是个大变化。这里边也有两重含义,第一重含义是,到了美国,有机会亲身体验那个制度。我讲个具体例子。我是 1984 年以访问学者身份进入哈佛大学。因为我没有念过高中、大学,只在清华有相当短的研究生经历,所以英语是完全自学的,自学最大缺陷就是听跟说。我在国内长期听 BBC 和 VOA 的新闻,有一定听的能力,但说的能力很弱。进入哈佛之后,哈佛燕京学社出钱把我送到哈佛暑期英语训练班,在那里有个项目,学生可以做里面任何你想做的事。
当时各种可以想做的事里,有一个提示是你可以访谈当地官员和议员。于是我选择访谈剑桥市市长,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挺大体验。你从中国的环境来,突然到了美国,在这么短时间里,我一个英语还说不清楚的人,就要采访市长。然后就到了市长办公室,直接跟市长谈任何敏感问题,市长回答你。另外,你还看到满大街竞选的各种安排。你从完全不同的政治环境进入美国,有直接对它制度的体验,重要性不低于学术训练。
另一面是哈佛大学提供的学术环境。学术环境里第一重要的就是自由。这个自由是过去从来没有体验过的。过去只在抽象文字上见过这样的讨论,但你并不知道自由是什么意思,到你进入自由的环境,才知道自由是什么意思。当然,它的学术水平很高,我不需要再多说。
在这之后,对我来说很重要的转折是我的第一个工作是去伦敦经济学院。离开美国到英国,进一步亲身体验和理解这个制度产生和演变的环境。伦敦经济学院也是另外一个国际上最优秀的学术机构,在这里从事教学跟研究,你有机会和世界各国最好的学者来往。尤其在当时,伦敦是研究苏联跟东欧的国际中心,有大量苏联跟东欧持不同政见的人们,包括最杰出的学者都在周围,所以直接和大量的这些人接触。
这都是非常重要的亲身体验以及对这个社会的认识。这个认识就超出了一个国、两个国,而是对全世界不同制度的认识。当然,伦敦是个欧洲中心城市,再加上地理方便,所以有一个比较全面的对于近代人类文明和制度发展好的认识,都和这些环境有关。
02
追寻中、俄相似制度的历史根源
小鸟文学:从学科角度,你探索的历程是从政治经济学到工程学,再到经济学及整个社会科学。其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你在“文革”十年间自学数学、物理等课程的经历。你说:“这么多年来,在‘文革’之初困扰我的基本问题,即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从来都没有远离我。我研究的课题从来没有脱离过制度,只是更宽广了一些,包括世界各国的制度,包括各种体制的制度。重读近 40 年【注:现在是 52 年】前自己的文稿,除了当年的政治用语和年少的踌躇张扬让我忍俊不禁,面对文中提出的很多问题,我依旧没有办法给出让自己满意的答案。”我很好奇,你觉得支撑你一直探索的动力来自哪儿?1969 年那份文稿中提出的什么问题让你至今没有满意的答案?你现在对这些问题的困惑和思考又是什么?
许成钢:动力从哪儿来?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一个动力是好奇心,觉得这件事情很有吸引力,很想弄明白。另外一个动力是,在我懂得多了以后,意识到自己年轻时有一种很强的宗教情绪。为什么叫宗教情绪?我觉得人的一生要有价值,而这个价值体现在要能够对社会有所贡献。我认为我能够有的贡献,就是弄清楚什么东西,所以到最后就更归结为好奇心本身。好奇心并不会只限制在某个地方,可以相当广泛,而且特别强的好奇心本身是带有某种意义上的宗教力量。
这样讲有点抽象,我讲具体的一个例子。我作为反革命被关起来,而且被审讯,那是非常严重的打击。我也曾经认为活着是不值得的,很努力才克服了这个情绪。能够让我还能有一点信心支持下来,觉得我还能做一点贡献,大概就是在工程上发明一些东西来显著改进生产力。我想如果我能够在技术、工程上发明什么东西显著提高生产力,也就算我心里有了安慰。这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宗教情绪,但这仍然还抽象。
再具体一点,我在自学时,每弄清楚数学跟物理的重要基本概念后,都会非常兴奋。我那时是反革命,而且时不时会被拉去批斗。我读的所有书都靠我母亲从北京寄过来,那么我和我母亲之间的通信和寄东西都要由专案组逐项操作。我不能写一封信自己装在信封里,必须把写的东西交给他们,再由他们寄走,然后所有来的东西他们拆开,再给我。所以当我纯粹阅读数学、物理时,他们不阻碍,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停止探索社会科学。
在被批斗的环境下,我有时在劳改时还会情不自禁自己唱歌,当时很多人觉得奇怪,觉得我神经出毛病了,但我真的心里愉快。我愉快的原因不是因为我蔑视批斗,而是因为在自学中弄清楚重要的基本概念。每当弄懂一个基本概念,都感到多了一点对世界的认识,会由衷地兴奋。当然,知道自己懂什么和不懂什么本身也很重要。
那时我探索的问题是,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会产生特权阶级?
至于讨论到具体社会制度问题,在文化革命时期,毛泽东说,文化革命是阶级斗争,每七八年就要来一次。但是,阶级斗争的对象,毛泽东没有讲得很清楚。他曾在文革后期说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而他在文革早期讲文革的对象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什么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当时认为更确切的描述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产生的特权阶级。
所以那时我探索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会产生特权阶级?这是我当时最关心的问题。为什么这个问题这么重要呢?原因在于我过去相信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道理。按照这个道理,共产主义是一个无阶级社会,而社会主义是一个从阶级社会过渡到无阶级社会的过渡阶段。过渡阶段必须是阶级逐渐消亡,如果在过渡阶段,阶级不能逐渐消亡,那么就永远不可能过渡到共产主义。对于相信共产主义的人来说,这个问题当然是最大的问题。
当时在我看来,通过发动文化革命或者阶级斗争的方式去和特权阶级做斗争,永远不能解决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所以为了要向它过渡,一定要想办法发现为什么会产生特权阶级?这样才能让特权阶级不再产生。我认为这是个没解决的问题,要探索。
虽然早就不再相信乌托邦的主义,虽然我现在的探索问题有了大变化,但本质上仍然和这个问题相关。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从俄国学来的,并不是中国独创。我的问题是,为什么在俄国会产生这样的制度?为什么中国后来会追随俄国建立一个苏联式的制度?让我把这个问题稍微展开一点。当年俄国创立苏联制度的时候,它的背景是什么?它的背景是俄国已经经历了差不多一百年的努力,希望建立宪政。那么在这一百年建立宪政的努力过程中,一直没有获得成功。
原本它是沙俄帝制,在争取宪政的过程中,1917 年 2 月帝制垮台。帝制垮台几个月后,布尔什维克发动武装革命,推翻已经建立的宪政政权,历史上叫十月革命。在原来已经建立的宪政的临时政府中,布尔什维克是其中的一部分。为什么俄国争取宪政的努力一直不能获得一个稳定的宪政制度?为什么布尔什维克后来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最后稳定下来,并一度扩大到占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持续了几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