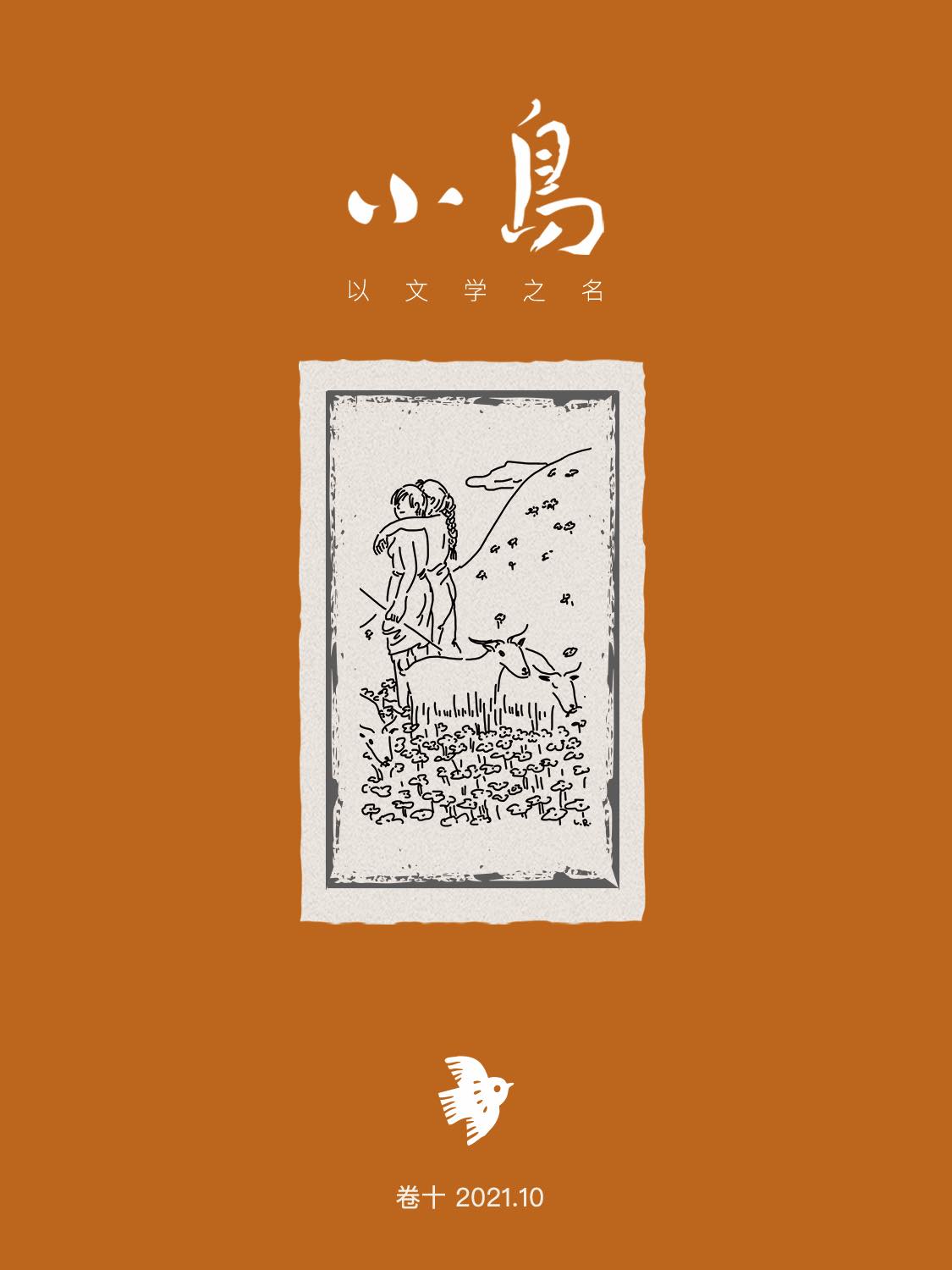01
夏洛滕堡是柏林的富人区,中间穿过一条开阔的马路,四条宽车道,对开的车辆各占两条,辅路也比一般的辅路要宽,走汽车、自行车和滑板都绰绰有余。辅路边上还有一条人行道,碎石子铺的,石头缝中钻出蓬蓬野草,说明这条道上虽不至于人迹罕见,但也是冷冷清清的。路边的铁围栏一直向前延伸,上面爬的灌木,有的叶子已经血红,在虚弱的阳光下露出点强烈感。围栏和灌木后面,是那些建筑风格迥异的高档别墅,它们从路边退进去至少有三四十米,形象地注释了什么叫深宅大院。路人的眼光再好奇,也很难清这些住宅的全貌。每栋别墅都跟下一栋隔得很远。住在这里的人,只要愿意,就可跟邻居和世界都老死不相往来。
在一处铁栅栏前,我找到了我要找的门牌号码。铁门上贴了三个名字,用字母写成,严歌苓的名字居中,上面是她的美国丈夫的名字,下面也是一个中国名字的拼音,但姓氏为马,我猜应该是她和先生收养的女儿的名字,可她为什么既不随父姓,也不随母姓呢?
门铃摁下,门就开了。严歌苓站在约四十米远的楼门前等我。她的两只狗汪汪叫着,朝我欢奔而来。我马上认出了这二位,小比熊嘟嘟和松狮犬壮壮。几天前,我刚读过严歌苓的一本散文集《穗子的动物园》,其实我只读完了《壮壮小传》这一篇就读不下去了。严歌苓写痛苦从来全力以赴,既不吝惜自己也不心疼读者。结局是壮壮死了,死得很艰难,严歌苓也很艰难,她给自己的挣扎找到了一个解决方案,就是又养了一只松狮犬,也管它叫壮壮。所以我知道,朝我跑来的壮壮是壮壮二世,嘟嘟还是嘟嘟本尊,那只严歌苓从北京带来的白色弃狗。
严歌苓穿一件长袖的蓝底白花衬衫,贴身绵软的那种,下面是一条九分紧身牛仔裤,洗白的蓝色。黑发披在肩头,有些蓬松,她说她刚游完泳。这就解释了院子里怎么有个类似京郊种菜用的长条型大棚,原来里面是她的游泳池。我们约了下午三点见,她说上午要写作。这天恰好是星期天,可见她的写作不管周末,只分上下午。我惊讶于她的纤细瘦小,她惊讶于我的惊讶,说,一直是这么瘦的呀。我想了想,上次见她,是在 2018 年柏林电影节期间,我跟着刘震云和他的一伙朋友来她家,那天她穿着一条有点灯笼型的长裙,款款的,没让我看出她的细瘦。
我们不熟。有一些共同的朋友,比如刘震云。直接进了厨房后,严歌苓边泡茶,边说,她跟刘震云是鲁迅文学院的同学,上学时两人没说过话,成为朋友是多年后的事。我能想见,刚当作家的刘震云,不是那种主动跟女生搭讪的人。遥想八十年代,他们这一代作家还是多么青涩,但都已经才华横溢得不像样子。严歌苓现在还说,她出国前写的长篇小说《雌性的草地》依然是她最好的小说之一。
02
国内媒体对她的身世报道已经很彻底了,口径统一的标签是:著名美籍华人女作家。她是 1989 年出国的,随身带走了三十年的人生阅历——12 岁参军入伍,进了部队文工团当舞蹈兵,去过抗越反击战的包扎所采访伤员,在部队里完成了从文艺兵到作家的身份转变。当兵 15 年后复员,结婚离婚,发表过小说,写过电影剧本,读过鲁院。单身去美国后,先吃苦,学英语、打工,考上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学院的虚构写作硕士专业,随之甜蜜,认识了美国外交官莱瑞,他为她一度放弃了外交前途。她则靠写作一举成名,电影剧本和小说创作两栖。今天,她的名字常和李安、陈冲、张艺谋和冯小刚这些名导演连在一起。李安买了《少女小渔》的电影版权,陈冲把《天浴》拍成同名电影并获奖。张艺谋拍的《金陵十三钗》和《归来》、冯小刚拍的《芳华》也都跟她本人写的小说一样,既叫好又叫座。
我读过一则她在 2006 年的访谈,她直言不讳地说,自己写两个电影剧本,就能拿到诺贝尔文学奖发的那个数儿。作为商业和品质双成功的作家,她肯定有她的秘笈,但一个绕不过去的事实是,她的名声和财富都是她自己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
她的沏茶方法很中国,热水对冲茶叶,两者都留在杯子里,慢慢泡去,喝的人自己负责用嘴巴和舌头撇开茶水里的茶叶。我端着茶杯,跟她从厨房走进了她家的一层。她和家人的私人空间在二楼,连着厨房的楼下这层,更像是一个公共空间,一个欢迎朋友们来玩的地方,也像一个博物馆的局部。几个大大小小的厅室互通有无,家具摆陈、灯具和装饰、三角钢琴,无不带着成熟的艺术品味和对高价位的漫不经心。每个空间都是多功能的,可餐聚,可茶饮,可酒会,可开家庭音乐会和舞会,可陷入沙发一角密谈……总之无法用常规的客厅、餐厅、书房之类来界定。
跟我 2018 年第一次来相比,我发现她的墙面明显不够用了。大型和小幅的艺术作品挂得满满当当,而她肯定还在继续收藏。尤其吸引我的,是两幅大尺寸的画作,蓝绿基调,安详里透着气势,有水墨感,又是当代抽象艺术的底子。严歌苓说这是一位德国艺术家,她在旧金山的时候就开始收藏他的作品,现在在柏林就接着往下买了。她又领我去看她刚买下的一位中国女艺术家的摄影作品,这位艺术家由默克尔出面相邀,三年前搬到了柏林来住,之前我只知道她画画,在严歌苓这里,我头一次看到了她的摄影作品。“你瞧瞧她拍出来的力量!”严歌苓想去到那两个镜框前比划给我看。她走在我前面,撇着典型的芭蕾外八字,像极了一个练功房里的少女,仿佛再走几步,就要把腿搭到把杆上去压。这个背影毫无年龄痕迹,让我一时恍惚。这时她转过身来,又变回了在媒体上看熟的那个样子,鹅蛋脸,美而媚,只是脸上的皱纹比媒体影像上的要多些。这些皱纹让我放心。她写过的几十篇小说无不历史深重人生多辛,这份浓烈的脑力工作不在脸上留痕就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