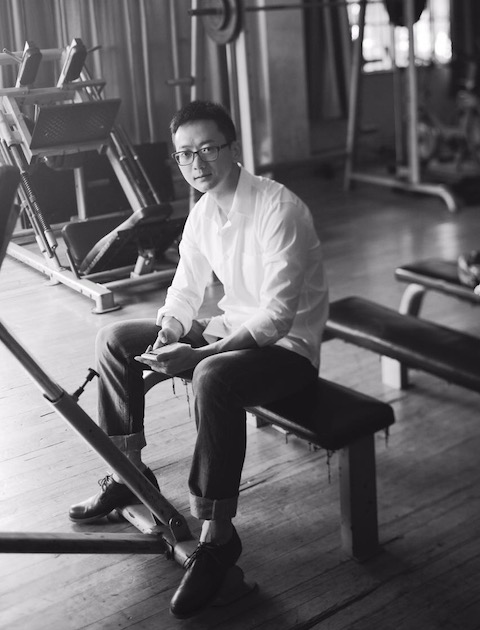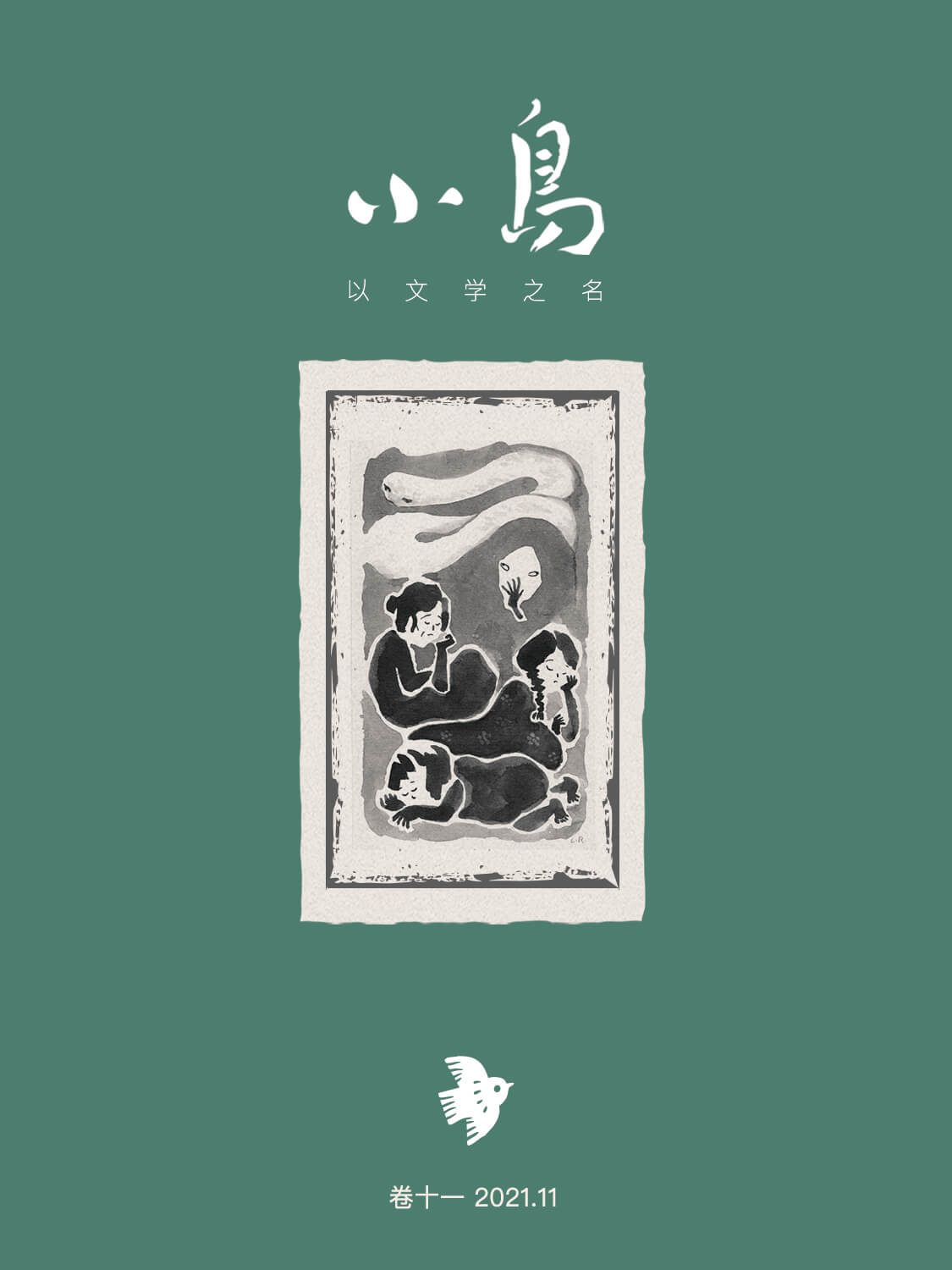陈禾算了算,等过完这个年,自己就七十六了。往后踢球得悠着点,多传中,少过人,尽量待在自己的区域。让那些五六十岁的“年轻人”去折腾吧,他就意思几下,算了。
龙头足球场在杨树浦路的一个居民小区里,初冬的早晨,天气晴朗,气温骤降至 3 度。八点半,黄浦江上的雾气还没完全散去,足球场上已是人声喧哗。这里面积不大,相当于标准场地的一半左右,地面坑坑洼洼,“草色遥看近却无”。场边搭着简易的雨棚,底下是一排塑料椅子。一个路过的居民跟我讲,别小看这个球场,连同周围日本人留下的红砖房子,将近一百年了。
第一次见到陈禾就在这里。朋友拉了一支七人制足球队,周末到处约场子。“龙头”租金比静安体育场、万体馆便宜不少,附近有十二号线,下来骑个共享单车就到。那天我们踢到下半场,场边来了两支老年足球队,七手八脚地热身。其中一个爷叔,身材高瘦,腰板笔挺,穿一件红色阿迪达斯防风外套,鞋子是耐克当季款,在这充斥着老式运动线裤、杂牌球鞋的队伍中显得鹤立鸡群。
下场时,我走过爷叔身边,讲了句,爷叔身体真好。
一般一般。他眉毛都没挑一下,神情寡淡得像小馄饨的汤,不啰嗦的。
然后他们开始比赛,坐在场边休息的我们傻了眼。各种跑位、传切配合,动作是慢了点,技术毫不含糊:踩单车,拉球过人,马赛回旋,像慢镜头下的西甲。浪费了一个得分机会,或者停球出现失误,场上开始飚骂人话,各种切口乱飞,随即又嘻嘻哈哈。
等他们踢完,我走上前,给刚才那位爷叔敬了一支烟。球赢了,爷叔心情不错。我这才知道,这帮老头子里,有进过国家集训队,有从上海队、部队球队退下来的。毕竟是年纪大了,眼下,老头子们像散落一地的弹簧,坐在塑料椅上,或一屁股盘地上,喘气,咳嗽,毛巾擦汗,喝保温杯里的茶,吃香烟,讨论拆迁事宜。一个老头用毋庸置疑的口吻说,这记肯定要动了。另一个声音附和道,好了,明年的房钿不用交了。
01
定海桥是定海路上一座桥的名字,后泛指定海路、波阳路交叉口附近的区域。因毗邻黄浦江,交通便利,自十九世纪末起,此地陆续建起船厂、造纸厂、自来水厂、热电厂、煤气厂、大型纱厂、肥皂厂、食品厂……“百工麇集,遂成市面”。与此同时,大批苏北移民涌入、聚居。49 年后,经历社会主义改造,更多的产业工人来到这里,形成大规模工人生活区。与法租界的老洋房,老城厢的石库门相比,定海桥的弄堂是粗犷阳刚的。论打相打,定海桥走出来的模子,还真没怕过谁。
陈禾家在定海路 449 弄,距龙头足球场不到十分钟步程。外人看定海桥,仿佛铁板一块,其实分两大区域——一块是定海港路,房子多为自家搭的私房;一块是 449 弄,最早为日资裕丰纱厂的职工宿舍,叫“公房”。住公房的人和住私房的人彼此看不大上,大抵上,是威虎山和奶头山的关系。七八十年代住房紧张,居民们自力更生,充分发挥想象力,各种违章搭建野蛮生长——在八级钳工扎堆的定海桥,这算不得什么困难事。两层楼加盖成三层,楼顶用石棉瓦再搭一个半露天的灶披间;木楼梯被移到墙外,省出的几个平方正好放进一张衣柜;外墙凸出一块,是无中生有的淋浴室兼卫生间;夹弄最窄处,仅容一个穿羽绒服的男人侧身挤过;楼与楼之间可以握手。小时候,陈禾的姆妈在阳台养花,一到夏天,各种香味混在一块。对面楼的老太太看了喜欢,一根晾衣服的竹竿伸过来,姆妈剪下几枝栀子花,用棉线绑在竹竿上,是遥远温暖的回忆。
童年的生活,像极了周璇歌里唱的:粪车我们的报晓鸡,多少声音都跟着它起。前门叫卖糖、后门叫卖米,哭声震天是二房东小弟弟,双脚乱跳是三层楼小东西。只有卖报呼声,比较有书卷气。煤球烟薰得眼昏迷,这是厨房里的开锣戏。旧被面飘扬像国旗,这是晒台上的开幕礼……事实上,直到今天,定海桥的许多居民,起床头一件事,就是把马桶、痰盂拎出去。“啥叫定海桥的男人,马桶拎拎看,侬就晓得了。”
姆妈是上棉十七厂的纺织工人,年年评为劳动模范。谢晋来厂里拍《黄宝妹》,有姆妈的镜头。爹爹是十七棉的门卫,据说有“历史问题”,在陈禾四岁时被送去大丰农场。爹爹为争取减刑,拼命劳动,加上伙食恶劣,急性盲肠炎发作,没抢救过来,离释放日期不到三个月。
陈禾上头有个阿姐,下面有阿弟阿妹,他是长子。打小他就是最乖巧懂事的一个,也最讨姆妈的欢心。夏夜,姆妈下了中班,回到家快十一点了,手里拎一个西瓜。姆妈把西瓜切好,叫醒小囡,姐弟四个便狼吞虎咽起来。西瓜又甜又沙,姆妈笑眯眯地坐在一旁。姆妈不吃。
陈禾生得好看,皮肤白皙,鼻梁高挺,绰号叫“阿尔巴尼亚”。那时能接触到的外国电影,除了朝鲜的《卖花姑娘》,就是阿尔巴尼亚的《宁死不屈》《第八个是铜像》。他跑回家,假装一本正经,“姆妈姆妈,人家讲我像阿尔巴尼亚人,姆妈你有问题伐?”姆妈做势要打,“小逼样子骂我。”
定海桥人谦虚地表示,这地方没啥了不起,无非是“出过几个流氓”,“出过几个大亨”,“出过几个球星”。几十年来,定海桥走出了张宏根、袁道纶、张水豪、申思等多位国脚,省级市级的球员一大把。还有一句话——“杨浦是中国足球的摇篮,我们这块,是摇篮的摇篮。”
“九一八”后,一批东北学生流亡到定海桥,带来了作风硬朗的北派足球,与本地足球相交融,成为定海桥足球的滥觞。抗战胜利,又有不少伪满洲国的大学生南下,单一个中纺十七厂(后来的上棉十七厂),就有大小“龙头”两支足球队。“大龙头”以东北籍球员为主,“小龙头”大多是本地球员,年龄偏小一些,其中有后来成为国家队队长的张宏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