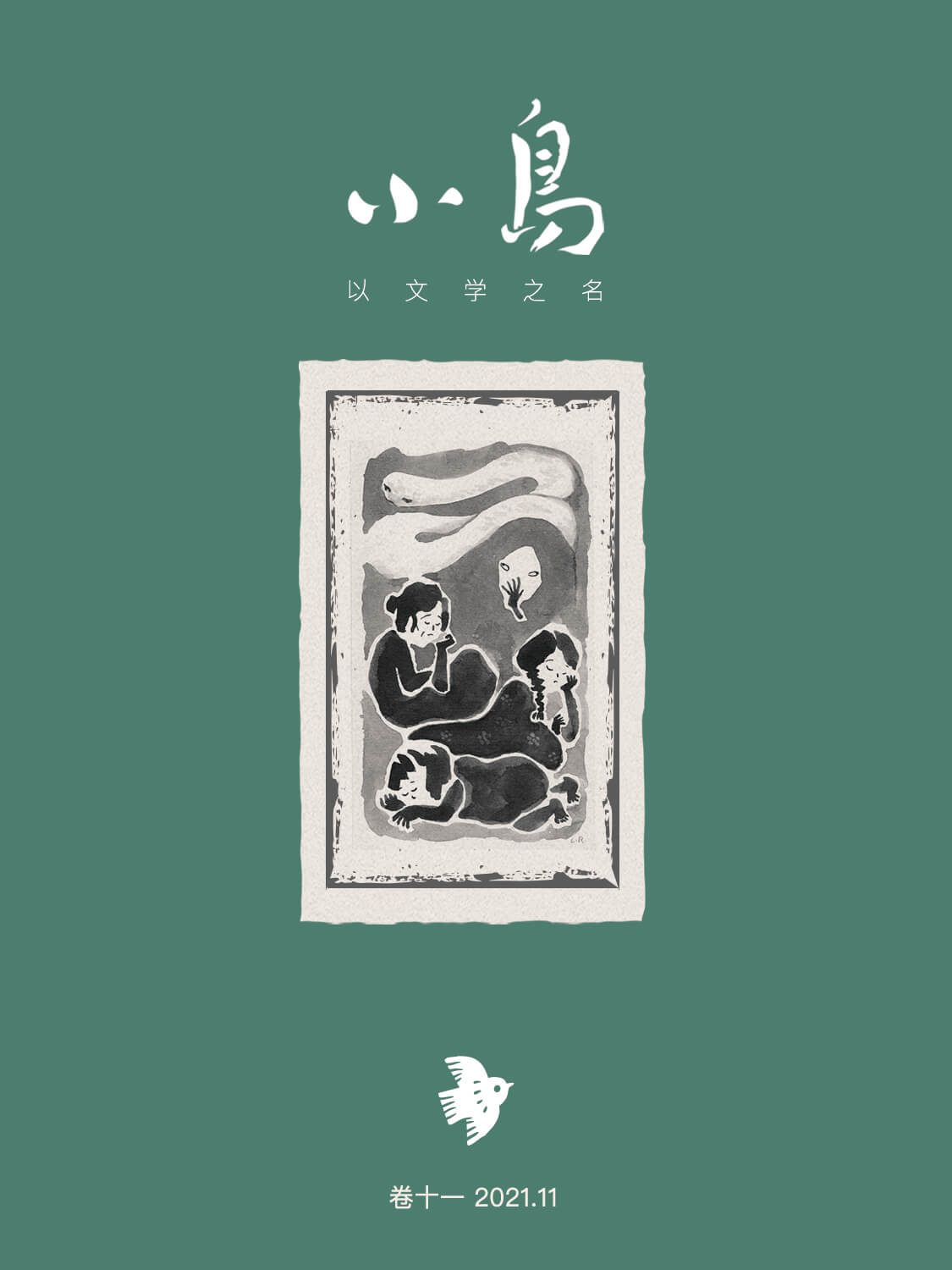两个浪漫的人
约翰内斯·勃拉姆斯和克拉拉·舒曼
[美] 丽泽·穆勒
现代的传记作家们纠缠不已的,
是他们温存的友情“到了什么地步”。
他们想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意思
当他写信说总在思念她,
他的守护天使,挚爱的朋友。
现代的传记作家们总是问
这种粗鄙的,我们这个时代特有的
无关宏旨的问题,似乎有了
两个肉体交织在一起这件事
就决定了爱的程度,
而忘记了爱神在十九世纪
是怎样地蹑手蹑脚,一次
时间稍长的握手,或是两眼间
一次深深的凝视,就能让人心潮起伏,
而一些在我们通俗化的语言里
已经无法辨认的微妙措辞
曾经就足够使芬芳的空气
因为某种可能的热望而颤抖
而闪闪发光。每当我听到
那些间奏曲,忧伤
而又如此纵情地温柔,
我就想象他们俩
坐在花园里
四周是迟开的玫瑰
和倾泻而下的浓郁的树叶,
任眼前的风景替他们倾诉,
什么也没有留下让我们听取。
写给加利福尼亚的信
[美] 丽泽·穆勒
我们给对方写信,似乎
使用的是同一种语言,
但其实不是。你的句子
轻轻地一句拍打着一句,就像
太平洋里的浪花,无拘无束;
你那悠长的,流畅动听的词语
像熟透了的牛油果在我嘴里回荡。
读你的来信是为了不再关注
有关地震和泥石流的新闻,
而是去想象时间在缓缓地流动。
是把太阳想象成
一个生灵,不会让任何不测
降临于你。
在偏远的此地
我们种下韭葱、菜豆和结实的
可以保存几个月的根茎作物。
我们这里没什么灾害;换言之,
没有任何雄伟壮观可言。我们只是
不动声色地不断挣扎
以求度过冬天,这个已吞下
两个季节,而且会把阴影投向
第三个季节的冬天。你会怎么办
如果没有一场大雪来告诉你终有一死?
一阵风会突然让我们驻足停下
也让我们说的话获得形状,一字一顿
清楚、直率地落下。这里的鸟
大多是山雀
和灯芯草雀,都是单色的
长得跟四周的景色浑然一体,
比如那铅云密布的天空
那瘦骨嶙峋的树木,它们
月复一月地保持着
舞者最初的姿势。但也有
一些我们懂得的启示:偶尔之间
一只红雀会动听地啁啾,
浑身火红得就像一位圣徒胸中
那出人意料的艳丽的心脏,
它在我们这通情达理的
灰褐色的景致里冒出来,若无旁人。
我搜遍语言,想要找到一个词
来告诉你这红有多红。
丽泽·穆勒 / Lisel Mueller (1924-2020)
出生于德国,十五岁时移居美国,1997 年凭《活在一起》成为至今唯一一位荣获普利策诗歌奖的德裔美国人,这也是她最后一本诗集。诗作典雅婉约,静水流深,有对欧洲 故国文化的怀念,也充满对美国中西部辽阔风物的依恋。
一篮无花果
[美] 艾伦·巴斯
向我敞开你心里的疼吧,亲爱的。把它
像精致的小地毯,像绸质饰带那样铺开,
像从粗麻布袋里掏出的热鸡蛋,桂皮香料,
和丁香花那样。把所有的细节
都展示给我吧,领子处精美的
绣花图案,细小的贝壳扣,
缝好的褶边,就像你学会的那样,
只挑出了一根线,几乎看不见。
像解开首饰那样解开它吧,金子
仍然带着你的体温。把你篮子里的
无花果倾倒出来。把酒洒出来。
那一块硬硬的疼,我会用嘴来吮吸,
我的舌尖摇篮一样围抱着它
就像一粒滑溜的石榴籽。我会
小心翼翼地拎起它,像一只大动物
张开秘密洞穴般的嘴
叼起一只小动物。
小小国度
[美] 艾伦·巴斯
苏格兰语里的 tartle,我觉得,真是绝无仅有,形容
你介绍某人时因为忘了他的名字而迟疑无措。
又有哪个字能替代 cafuné,说葡萄牙语的巴西人用它来
描写你的手指,温柔地,从某人的头发里捋过?
所有的语言里,有没有一个词,意为选择做一个幸福的人?
而我们包在自己锯末屑一样的内心里的冰块,描写它的语言又在哪里?
什么样的说法,可以唤起初夏熬果酱时
弥漫在空气中的杏子的味道?
什么词语可以接近昨晚我对你的抚摸——
仿佛我从来没有见识过女人——像一个勘探者,
兴致勃勃地去发现每一个特殊的
褶皱和洼地,不需要任何向导,
甚至不需要我自己的身体这面镜子。
昨晚你说你喜欢我的眉毛。
你说从前并没有真正留意到它们。
什么样的词可以把这种新鲜感
和此前错过的遗憾揉合在一起。
又怎么解释,连抚摸对我们俩的意义都不一样,
即使是在这个由我们的床所构成的小小国度里,
即使是使用只有我们两人将其作为母语的语言。
艾伦·巴斯 / Ellen Bass (1947- )
大学时代曾师从诗人安妮·塞克斯顿,1973 年出版第一本诗集;长期致力于帮助性侵受害者,为其提供心理辅导,2013—2014 年间在加利福尼亚州的监狱系统创办诗歌工作坊;其诗作的一大主题是女性间的爱恋和欲望。
尘世的爱
[美] 露易丝·格吕克
是那个时代的习俗
把他们维系在一起。
在那段(很长的)
时间里
一旦把心无偿地交给对方
就会被要求,以明确的姿态,
放弃自由:这种奉献
让人动容也是令人绝望的劫数。
至于我们自己:
多么幸运,我们得以抛开
这些要求,
当我的生活忽然破碎时
就这样提醒过自己。
因此我们长久以来所经历的
都是,或多或少,
心甘情愿的,直面生活的。
只是过了很久以后
我才另有所思。
我们都是人——
我们都尽量
保护自己
甚至不惜回避
事情的真相,不惜
自我欺骗。正如
我刚才提到的那种奉献。
可是,即使是这种自欺,
也见到过真正的幸福。
所以我想我会
原封不动地重复这些错误。
我也不觉得真的
就有必要去弄清楚
这种幸福是否
建立在幻觉之上:
它有其自身的真实。
而无论哪种情形,迟早都会结束。
静夜
[美] 露易丝·格吕克
你牵起我的手,于是危机四伏的森林里
只剩下我们俩。几乎是转瞬之间
房子里只有你和我;儿子诺亚
已经长大并且搬离;铁线莲十年之后
忽然开出白色的花。
我深爱我们一起相处的这些夜晚,
胜过世上所有的一切,
夏日里静谧的夜晚,天空此时依然发亮。
当珀涅罗珀牵起奥德修斯的手,
并不是不让他走,而是要把
这份安宁压印在他的记忆里:
从今往后,你穿行而过的所有寂寥
都是我的声音在追赶着你。
露易丝·格吕克 / Louise Glück (1943- )
曾被誉为“当下最纯正,也最有成就的抒情诗人之一”,2003—2004 年度美国桂冠诗人,2020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作品丰富,形式多变,语言精确而沉郁,反复探讨爱恋、离异、死亡、孤独等生存考验,常常用现代人的经验重写希腊罗马的神话和史诗,独树一帜。
致我自己
[美] 弗兰兹·莱特
你又坐上大巴
向着 80 号州际高速深处的黑暗扑去,
唯一的旅客
拧亮了头顶上方的灯。
而我跟你在一起。
我是你看不见的无尽的田野,
是远处微弱的灯光
(我们就生活在那其中的
一个房间)我也是雨水
是围绕着你的
其他人,是你喜爱的孤寂,
也许,是特别喜爱你的天地宇宙,
是那大难将至的黎明,
是你皮肤上蠕动的尼古丁——
因此当你开始
咳嗽时我不会捂着脸,
如果这次你呕吐,我会扶着你: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会轻轻地说。
不会总是这样。
我去给你买个三明治。
献词
[美] 弗兰兹·莱特
确实,我从来不写信,但我会心甘情愿跟你一起去死。
心甘情愿把你和我一起放进那个巨大的
张口等待的洞穴,没有了青春,没有任何狂欢,还记得
从前我们上阵之前会给对方化妆,互相把头发梳好
说我们所向无敌,我们如此可怕但英俊威武——
洞穴还在等,耐心地等。我将在那里跟你重逢
不会有滴血的荆棘,不停放大的瞳孔,和那什么效果也没有的火;
我已经到达那里,经过了雪白的云层,变秃的地苔,还有
连我们都可以踏上去的惨淡星群,这次要容易得多,我保证——
我已经在你的私人天堂等你,请握住我的手,
我会帮你跨过。我还是心甘情愿跟你一起去死,
尽管在这个灰色的机构里
我从来不写信。你看
他们迫不及待地要把我治愈,
我被判处了——抱歉——我是说分配了这份工作
不停地用吸尘器来清扫沙漠,当然,一天最多八小时。
实际上就是大约一千里长的自助餐厅;
怎么说都不算小。那里有微缩的塑料餐具刀,
有金枪鱼沙拉和保鲜膜包着的生殖器,哪位好心人
请把我救出来,真是不好意思。我很高兴地说
所有的方法,比如大剂量的药物,艺术疗法
教育影片以及一些我宁可不去提及的
其他手段——也就是说,那个洞穴所见过的
——抱歉!——我们最仁慈最有同情心的
科学所知道的每种技巧,都一一用上了
来帮我恢复到正常状态
让我重新兴高采烈情绪稳定。我不停地
朝着远方钻石一样微弱的灯光
吸尘而去。别忘了
我。你还
记得我吗?
夜间没有窗户的黑暗里
我躺在那里冰冷麻木
没有人在摆弄门上的锁,也
没有人用手电照我的双眼,
虽然我从来不写信,但暗地里
却渴望跟你一起去死,
这算不算呢?
弗兰兹·莱特 / Franz Wright (1953-2015)
出生于维也纳,著名诗人詹姆斯·莱特之子;2004 年获普利策诗歌奖,翻译过德国诗人里尔克,曾经在精神病诊所工作过。其诗歌多以孤独、失眠、死亡、精神崩溃等为主题,诗风凝重阴郁,绝望中流露出对爱的信念和对美的向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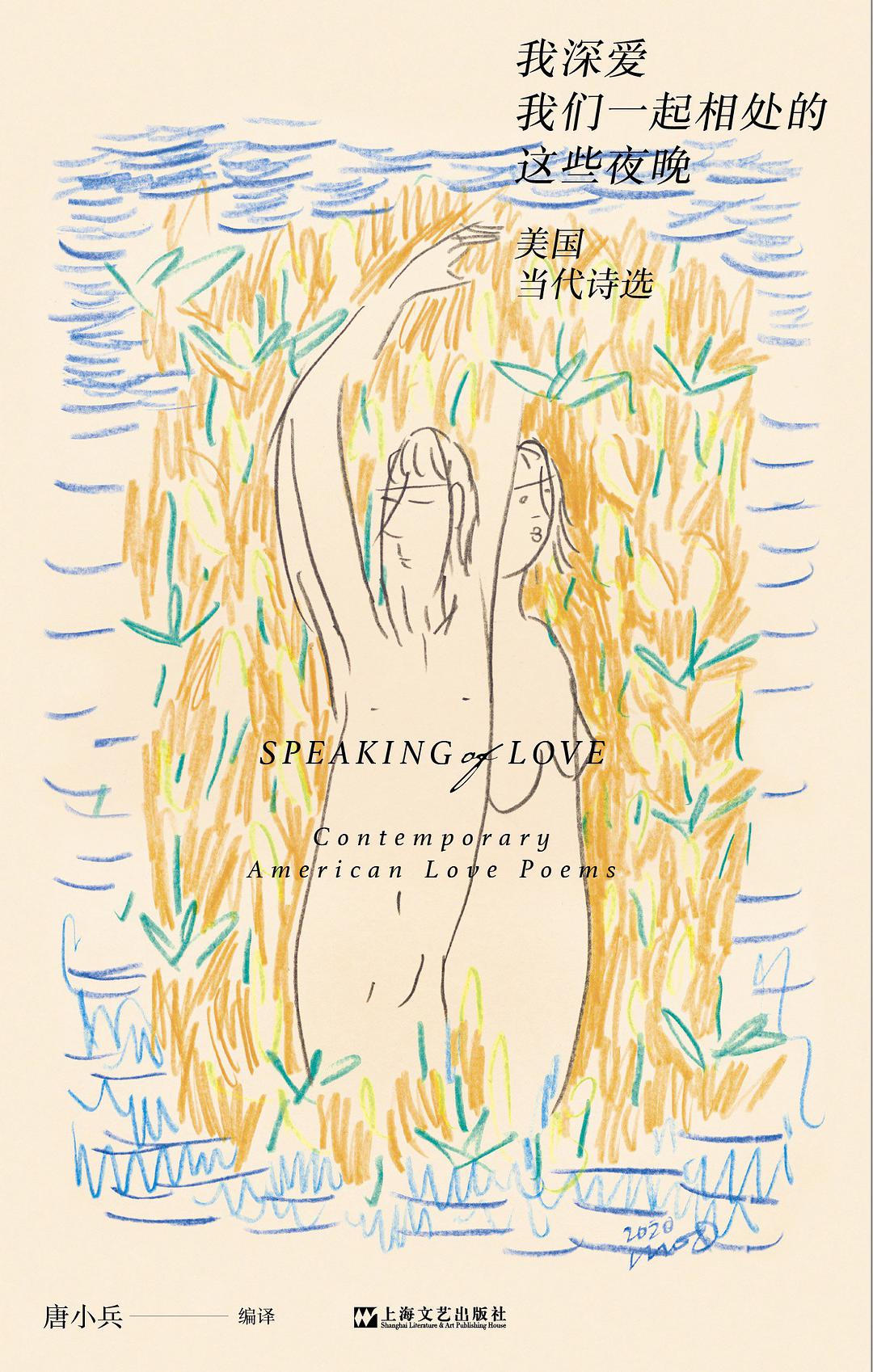
本文摘自《我深爱我们一起相处的这些夜晚:美国当代诗选》
唐小兵 编译
艺文志eons |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1 年 10 月
题图来自 Dan Musat on Unsp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