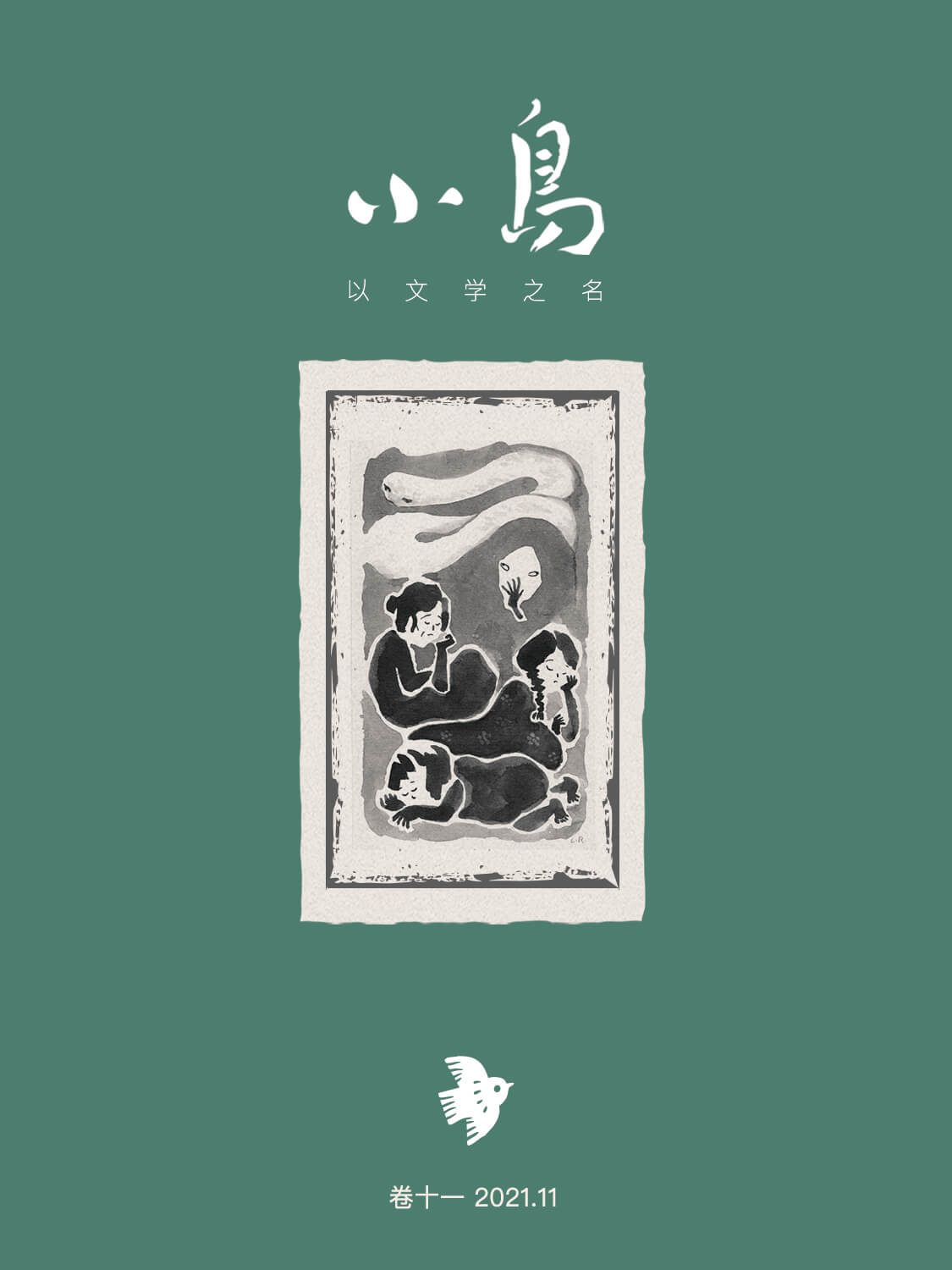他有时会问自己一个关于生命的问题。快乐的记忆,或不快乐的记忆,哪个更加真实?最终,他认定这个问题是无法回答的。
他有一本保存了几十年的笔记本,记录着人们对爱情的看法,有伟大的小说家、电视名人、自救专家,有他多年来在旅行中遇到的人。他在收集证据。之后每隔几年,他都会浏览一遍这些内容,删去不再相信的那些引语。通常,这样一来就只剩下两三句暂时的箴言。说它们暂时,是因为在下一次,他可能也会将它们删去,只留下另外两
三句。
前几天,他乘火车去往布里斯托。在过道里,一个女人把《每日邮报》摊在面前。他看到了显眼的标题和大幅配图照片。四十九岁女校长,喝酒八杯,将薯片放在上身,让学生“来拿”,有这样的标题,何须再看整个故事?在如此强烈的暗示之下,读者哪还能读出别的寓意?放在半个世纪前,报纸强烈的道德红线依然不可触碰之时,这样的一则故事甚至上不了当地的《广告客户报》。接下去的十多分钟,他思考自己的事如果见报可能会有怎样的标题。最终他想了一个:网球俱乐部新丑闻,四十八岁家庭主妇与十九岁长发学生因乱搞而遭驱逐。正文将这么写:“上周,树茂叶盛的萨里郡,在蕾丝窗帘和月桂树篱后面,出现了剧烈的起伏,随之而来的是淫荡的指控……”
有些人老了以后决定住在海滨。他们看潮起潮落,看沙滩上泡沫汩汩,远处浪花朵朵。或许,在这一切之外,他们还听到了时光浩瀚的波涛之声,在这样隐隐的广袤中为自己渺小的生命和日渐逼近的死亡找寻些许慰藉。他更喜欢另一种不同的液体,它具有自己的流动和归宿。但是,他从中并没有发现任何永恒之处:只是从牛奶变成奶酪而已。他对事物较为宏大的见解深抱怀疑,他谨防难以名状的渴望。他偏好应对活生生的日常事务。他也承认自己的世界和生活已慢慢萎缩。但他对此心满意足。
比如,他认为自己在死前可能不会再有性行为。或许。可能。除非。但总的来说,他认为是不会了。性涉及两个人。两个人,第一人称的我和第二人称的你,我和你。而如今,他心中的那个第一人称的喧嚣已寂静无声。就好像他是以第三人称在审视和过自己的生活。他相信,这使得他可以更加精准地评估自己的生活。
✽✽✽
于是,就来谈谈司空见惯的记忆问题吧。他认识到记忆是不可靠的,是有偏向的,可是偏向什么呢?偏向乐观?这合乎情理。你记得过去快乐的事情,因为这证实你的存在。你不必将自己的人生视为功成名就——他的人生几乎算不上成功——但你需要告诉自己你的人生是有趣的、愉快的、有意义的。有意义?这种定位似乎有些偏高了。但显然,乐观的记忆可能使告别生活变得更加容易,可能减轻消亡的痛苦。
但你同样可以持相反的观点。如果记忆倾向于悲观,如果回溯过去,一切都比真实情况更加黑暗和阴郁,那么,这或许会让丢弃过去更加容易。假如就像已死去三十多年的亲爱的琼,你这辈子已经到过地狱,又回到了人间,那么,你还会害怕真正的地狱吗?或者,更可能的是,害怕永恒的虚无?他的脑海中飘进了一名在阿富汗的英国士兵用头戴式相机录下的一番话,那是另一名士兵处死受伤的俘虏时,在扣动扳机前说的。“好吧,我来成全你。摆脱尘世烦恼的纠缠,你这个贱人。”他那时还想,在现代战场上,还能听到有人引用莎士比亚,这太难得了。他的脑海中为何会闪过这样的话语?或许是琼的咒骂引发了联想。所以他往好的一面想,感到人生就是需要摆脱他妈的烦恼的纠缠。男人就是贱,不是女人,是男人才贱。悲观的记忆可能也有进化上的优势。排队买食物时你不会介意给别人腾出空位,你可以将漫步荒野视作社会责任,或者为了更大的利益揭竿而起。
但那只是理论,生活才是实际。在他看来,他一生中最后的任务之一便是正确地铭记她。他并不是指精确地,一天天、一年年地,从开端到中途再到结尾全部一一记住。结局已十分糟糕,中途异常漫长,早已胜过开端。不是的,他的意思是,对他们两人来说,铭记和拥有他们最初在一起时的那个她,这便是他最后的责任。记得她在他心中依然纯真的样子:纯真的灵魂。在这样的纯真被玷污之前。没错,就用这个词来形容:醉酒之后狂野的涂鸦。还有,丢脸啊,后来,他再也不能见她了。在失去她、看不到她之前,在她遁入印花布沙发之前,去见她,去回忆她的模样——“快看,凯西·保罗。我要消失了!”他第一个——也是唯一——爱过的人消失了。
当然,他有照片,它们很有帮助。在某个遗忘已久的树林中,她倚靠在树干上朝他微笑。空旷的沙滩上,微风吹过,远处,在她身后,有一排装着百叶窗的小屋。甚至还有一张她穿着绿色镶边网球裙的照片。照片是有用的,但从某种角度来说,它们总是印证记忆,而不是解放记忆。
他尝试着在飞舞的思绪中捕捉她。想在一切被封闭之前,记住她的快乐、她的笑声、她的不羁和对他的爱。她朝气蓬勃,勇敢追求幸福,尽管她总是时运不济,尽管他们总是时运不济。是的,这就是他的追求:开心的苏珊、乐观的苏珊,尽管他对未来一无所知。这是她的天赋,是她性格中十分幸运的一部分。他自己倾向于展望未来,并通过评估来决定前景适合乐观还是悲观。他给自己的性情注入活力,她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性情。当然这更具风险,它带来更多快乐,但也没有任何安全保障。尽管如此,他觉得,至少他们并没有被现实击败。
这就是一切,而且她也是这样原原本本地接受了他。不,甚至,她享受这样的他。她对他有信心,她注视着他,毫不怀疑他。她觉得他可以成就自己,成就人生。某种意义上,他确实已经做到了,虽然不像他们原先所预见的那样。
她会说:“让我们把所有小鲜肉都堆进奥斯丁里面,开车去海边。”或者去奇切斯特大教堂,去巨石阵或二手书店,或者去中央有棵千年古木的树林。或者去看恐怖电影,不管它们把她吓得魂飞魄散。或者去游乐场,在那里他们可以尽情地玩碰碰车,将棉花糖沾满脸,怎么也取不出椰子肉,被各种装置旋转到空中,直到他们气喘吁吁,精疲力竭。他不知道那时他是否和她一起做了所有这些事情。有的或许是后来做的,有的甚至是与其他人做的。但他就需要那样的回忆,可以把她带回人间,即使她当时实际上并没有在场。
没有安全网。一想起她,某个场景就会在脑海中重现。他紧紧拽住她的手腕,她悬吊在窗外,他无法将她拉进来,也不能放手让她坠落,他俩的生命陷入痛苦的僵持,直到有事发生。发生了什么呢?呃,他曾想组织人们把床垫堆得高高的,以减弱她下坠的冲击力;或者,他让消防队准备好救生布单;或者……但是,他们的手腕绑在一起,像表演空中飞人的演员:不只是他拉着她,她也拉扯着他。最后,他的力气用尽,手一松,她就掉了下去。虽然有衬垫缓冲,但仍然很痛,因为,就如她曾经对他说过的那样,她骨骼沉重。
当然,他的笔记本中有这么一条:“爱过又失去胜于从未坠入爱河。”它在那儿保留了好几年,后来他把它杠掉了。后来他又写了一遍,又把老的那条再次杠掉。现在,这两句话并列在一起,一条清晰而真实,另一条已被杠掉,已成谬误。
回想村子里的生活,他记得村子无非就是个简单的系统。每种小毛病,都有一种单独疗法。嗓子疼用三氯苯酚,有伤口用滴露,头疼用阿司匹林,出现肺炎症状用维克斯止咳膏。除此之外,还有更重要的问题,但都有统一的解决方法。性的疗法是婚姻,爱的疗法是婚姻,不忠的疗法是离婚,不高兴的疗法是工作,极度不高兴的疗法是喝酒,死亡的疗法是对来世脆弱的信仰。
作为青少年,他渴望更多复杂的生活,而生活让他发现了这一点。有时,他觉得自己已受够生活的种种复杂。
和安娜争吵几周之后,他放弃租房,搬回了亨利路。在某部小说中,他读到过这么一句话:“他坠入爱河,就像自寻短见。”并不完全一样,但他觉得自己别无选择。他不能和苏珊一起生活,他也不能离开她独自生活,于是他就回去和她一起生活了。这是勇敢还是怯懦?或者仅仅是无法逃避?
至少到现在,他已习惯了这种模式化的了无波澜的生活,已再次屈从于这种生活。对他的再次出现,苏珊既谈不上不高兴也算不上慰藉,没什么惊喜可言。因为,这样一种回归是一件平常事。因为,虽然得允许年轻男人犯错,但是他们回到本不该离开的地方,这并不应该庆贺。他注意到了这一矛盾的反应,但心里并不怨恨,倒还真的达不到怨恨的地步。
于是——有多久呢?又过了四年,五年?——他们继续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一天天,一周周,有时风和日丽,有时天寒地坼,他们忍气吞声,偶尔也会暴跳如雷,他们愈加与社会隔绝。这一切都不再使他觉得有趣。恰恰相反,他深感自己是个失败者,是个弃儿。这期间,他从未接近过其他女人。一两年后,埃里克再也无法忍受这一氛围,便搬了出去。楼顶的两个房间就租给了护士。唉,他总不能租给警察吧。
不过,在那几年中,有一个发现使他颇为惊讶,正是这一发现使他的未来生活变得轻松起来。办公室经理怀孕后,他们就刊登广告寻找接替者,却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于是他毛遂自荐。这份工作无须占据一整天时间,他仍可处理一些法律援助案件。但他发现,日常的行政事务,譬如,记日志、收发邮件、开账单——甚至维护咖啡机和饮水机这类乏味的杂事——都给了他平静的满足。毫无疑问,在某种程度上,从亨利路赶来上班,他的状态不适合做更多超出这种低级别行政事务的工作。但他在料理这些事情时,收获了未曾预料的愉悦。同事们也都很感激他把他们的工作变得更加轻松。这与亨利路的故事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苏珊上一次感谢他让她的生活不那么费力,是在什么时候?
办公室经理讲述了母爱带来的种种惊喜,并以此为由,宣布自己不会重返岗位。他全职承担起这份工作。几年后,这一实打实的能力成了他的脱身之途。他为律师事务所、慈善机构、非政府组织管理办公室事务,因此得以到处旅行,根据需要跳槽。他曾在非洲、北美、南美任职。从事日常事务满足了他的一部分需求,他以前都没有意识到那部分需求的存在。他记得,当时在村网球俱乐部时,他对几个年龄大一点的会员的打球方式感到吃惊。他们确实很有实力,但缺乏表现力和创造性,好像只是因循守旧,一味地遵从某位早已作古的教练的指令。嗯,他们那时就是这样。现在,他可以在任何时间地点管理一家事务所,就像一位墨守成规的老苦力。他不断地给自己满足感。多年来,他也学会了理解金钱的意义:它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还有一点,这份工作的要求低于他的能力。这倒不是说他没有认真对待,其实他很认真。然而,从职业上来讲,由于他降低了自己的期待值,他发现自己很少失望。
他有责任去回顾她的过往,有责任去拯救她。但这也不只是关涉她,他对自己也有责任啊。回顾过去,然后……拯救自己?从……中拯救?从“他后来的生活残骸中”吗?不,那傻乎乎的,太夸张了吧。他的人生没受到摧残。他的心,是的,他的心却变得麻木不仁了。但他找到了一条活路,得以继续生活,走到了这里。就从这里,他有责任回顾那个曾经的自己。真奇怪,年轻时你对未来不负任何责任,但是等你老了,却要对过去负起责任。对你唯一无法改变的事情负起责任。
他记得,上学的时候,他在老师们的指导下读书看戏,书中戏里常出现爱与责任的冲突。在那些古老的故事中,单纯而炽热的爱往往与对家庭、教堂、国王和国家的责任狭路相逢。一些主人公赢了,一些则输了,有一些既赢了也输了。通常,悲剧也应运而生。毫无疑问,在宗教的、父权的、等级森严的社会中,这种种冲突依然在继续,仍在为作家们提供创作主题。但在村里呢?他的家人不上教堂,没有什么社会等级结构,除非你将网球和高尔夫球俱乐部委员会开除会员的权力算在内,也没有明显的父权制——他母亲还在。至于家庭责任:他觉得自己没有义务去安抚父母。的确,如今责任已转向,父母才是要接受孩子“人生选择”的一方。例如,与美发师佩德罗私奔到希腊小岛,或将穿着校服的准妈妈带回家。
然而,从旧教条中解放出来也会带来种种错综复杂的情况。责任感已被内化。归根结底,爱本身就是一种责任。你有爱的责任,而它一旦成了你的核心信仰体系,那就更是如此了。同时爱也带来诸多责任。因此,尽管表面上没有重量,其实爱的分量很重,约束也很强,种种责任也许会造成像往昔一样的巨大灾难。
他还逐渐明白了另一件事。他曾以为,在现代世界,时间与空间已不再与爱的故事相关。回望过去,他发现,时空在他的故事中扮演的角色比他想象的更为重要。他已屈服于古老、持续、根深蒂固的幻觉:不知怎么回事,爱侣们身处时间之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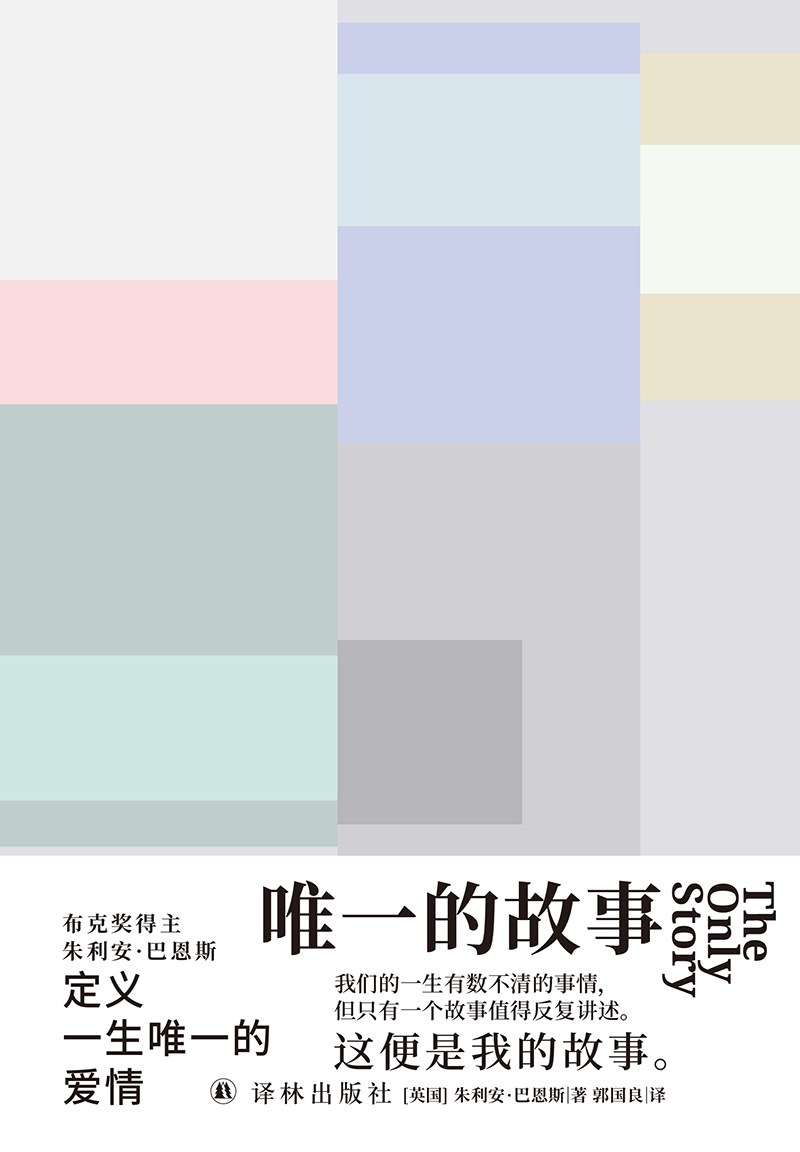
本文摘自《唯一的故事》
[英]朱利安·巴恩斯
郭国良 译
译林出版社
2021 年 10 月
题图来自 Hermes Rivera on Unsp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