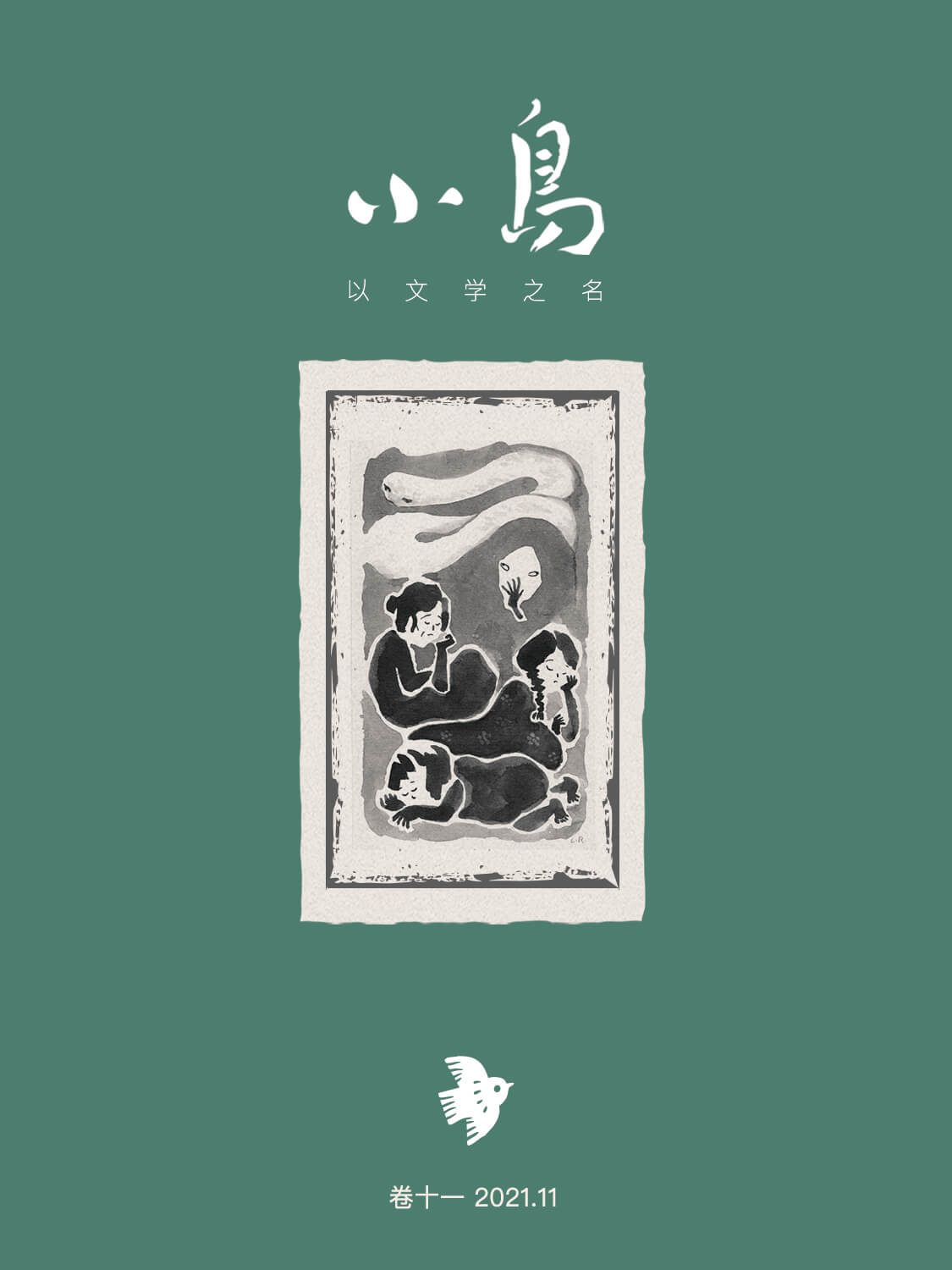01
从办公室东南窗子望出去,11 点钟方向,院子里有一棵真正的梧桐树。上海风情的若干要素中,总有人要说遮天蔽日的法国梧桐。法国梧桐既不是梧桐,也不来自于法国,就像说神圣罗马帝国的段子——它既不是帝国,也不在罗马,肯定也够不上神圣。它叫二球悬铃木,以它为行道树,好处不容置疑:叶子大,夏天挡得严实;秋天会落叶,疏朗有光,温暖而且又近乎完美。大家不喜欢它是因为春天有花粉,人就是这样,恨不得让行道树长成一个冬暖夏凉的棚子,不能有一点包容之心。这一点,京沪罕见一致,北京杨树多,春天飞花絮,就有很多人在那儿研究树的阉割术,没有能力研究的人就在那儿骂街——真是骂街。作为人类一员,我时常为包括我在内的人类的自私自利而脸红,但好像人类主要把阉割树这件事看成一种来自高智慧生物的力量,这更让人脸红。论上海好看的行道树,我觉得还是栾树,号称春夏秋都有好看颜色。香樟单调一些,但香樟很稳,绿得扎实,夏天特别友好。最近这几年,银杏作为行道树比较时髦,但它到了秋天总有小果子落下来,太臭——这是小事。主要是树干直,树冠不够大,纬度稍高地区太阳斜射可能还好,南方最热的时候太阳接近于垂直,效用就会大打折扣。上海最好的行道树,梧桐之外不应该忘了栾树:树冠大,春夏秋三季颜色不同,好看——秋日,夕阳,蓝天,栾树确实像火。
院子里这棵是真正的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梧桐树,叶子大,不是特别挺拔,但也足够蓊郁,开很铺张的花,与漫天撒细细花粉的二球悬铃木一点也不一样。但梧桐的花虽然大,颜色近于枯叶,观感并不好。
它下面有几株芭蕉。5 月份刚来的时候,芭蕉一副苟延残喘的破败相,前一年冬天发过大寒潮,仅剩的叶子薄而矮。但天一暖,芭蕉仿佛人生开挂,噌噌地长,最高处已到三楼。跟着芭蕉疯起来的还有不断压向窗子的绿色。

- 芭蕉。
办公室格局方正,主体朝南。楼下是院子,分成东西两爿。西半爿临着弄堂主路,现在是书法培训班的院子,种竹子,墙上挂点绣球,点到为止,主体是户外桌椅,走修身养性路线。东院截然不同,说是园子,其实更像一个荒僻的天井。一副晒衣架完全锈掉,在杂草里茕茕孑立,旁边一只废弃的空汽油桶,下过大雨就盛满亮亮一桶水,阿黄和她的两个小白仔会趴在边沿喝水。靠中间,就是筑起竹篱隔开两个院子的地方,是桂花和女贞。在自以为已经和周围所有沉默的大邻居们打过照面之后,隐隐觉得还是哪里不是很对。因为常有巨大的狭长心形大叶子飘落,但是探身出去只见女贞。万物其来有自,它是谁?它从哪里来?
四处看过之后,大叶子之谜才解开。在窗口一整个女贞树冠之上,还有一株两倍其高度的大梓树。大树整个树干倾斜到几乎横穿前院,却被女贞的茂密枝条完全遮蔽。两棵树混长在一起(其实女贞树皮发青、色浅,完全不同,还是得怪我识树不精),且奇怪的是覆盖全楼的常春藤舍女贞而求大树,顺着梓树一路往上,连藕断丝连的断枝都不放过。饶是如此,整棵树还是傲视整个蒲园,只不过把树冠挪得过于高远,以至于不努力后仰作治疗颈椎状,无法看清大树全貌。这棵树和它扎根的这个院子一样,也是野性不假修饰,是整个蒲园最高的树。
这跟东边窗外的桑树就搭配了。种桑梓,代表家乡,大家都知道这类说辞,但真在生活里对上号,还是有惊喜。桑树挂着紫黑色细长小果,举在窗前,与水果店里的粗胖版本不可同日而语。东边窗外远处是水杉和银杏,近处是两棵蒲葵,棕榈科的植物,百度百科上介绍它,“嫩叶编制葵扇;老叶制蓑衣等,叶裂片的肋脉可制牙签;果实及根入药”……关于生物界,百度百科相对来说没有太多胡说八道的东西,可看。但它们就是喜欢谈植物的实用价值,内容在简单的科普之后很快以饲养培育为本,总是讲一些如何以及什么情况下吃掉它们的秘笈,或者是如何种植如何嫁接如何繁殖,不知道什么人会到这里讨种植的技术。
办公室有西窗,朝向 5 号豪宅。整幢楼属于一家,正在装修,新刷的米黄色,亮得刺眼。这幢楼据说不断易手,每次都有成倍的天价出现。如今在整楼装修,搭起脚手架,工人站在脚手架上摘枇杷吃。
02
王老师家窗外有两棵大树。
一棵是枇杷树。树冠很低,果子极多。最初见到这棵树的时候我先见到了沿着外墙扔了一路的枇杷皮和枇杷核。这是豪宅的装修工人吃掉的。在王老师家和豪宅之间,还有一棵广玉兰。
王老师不管枇杷的事,她在意的是广玉兰。这棵广玉兰和桑梓大约同年岁种下或者更早,已经到了园林局会来管一管的规模。王老师嫌弃它挡光,家里已经没有晒台,窗口的光再被挡掉,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王老师请脚手架上的工人帮忙砍掉一点树枝。工人照办。园林局很快赶来了,告诫工人说如果再擅自修树,就是违反规定要被罚款。
王老师的丈夫梁先生说起这件事的时候鼻孔里一直在哼气,“要是那天我在……”
“让人家不要修,那你们倒是自己来修呀。这棵树把家里挡得来光都没有了,怎么不见你们园林局来?”梁先生说这件事嗓门马上大起来。“乡下人么也是不懂,这帮园林局的人,给几根香烟吃吃,就没话讲来,对伐?就是那天我不在,册那……”梁先生大概是没看到那个新闻。就在我们交流广玉兰的那几天前后,有这样一条本地新闻上了微博热搜:上海男子购买香樟树,修剪却被罚款 14.42 万元。来龙去脉大抵是这样的:男子 2002 年的时候花 1.1 万元买了一棵香樟种在自家院子里(想必树很不小),几年之后因为树高挡光,请人把这棵树移到了院子门口的空地上。到了 2021 年,香樟越发高大,越发挡光,于是男子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请人把树修了修。修理方式很粗暴,只留主干一个光杆,其余部分全部砍掉。于是这就构成了破坏公共绿化的行为,被处以(绝对不是几根香烟可以计算的)罚款。“就是那天我不在……”梁先生不完全为争取光线不成而气恼,他主要是觉得自己的决策被几个不懂行的外地工人搅黄了,让身为坐地户的自己很没有面子。不过他自己也发现了,这棵广玉兰被工人锯得失去平衡。“现在都斜了喏……”梁先生说起这个发现的时候竟然有一种天真的口气。然后毫无关联地,他用另一种天真的口气提起了另一棵广玉兰,在他从小长大的路口再往西一百米的样子,邮电医院旁边,有一棵更大的广玉兰,被三堵墙围出一种笼子里的宠物的感觉。
“原来这排房子都有天井,后来都加盖变成了房子,房子又变成了店。”广玉兰太大了,无法变成房子或者店的一部分,这个地方就被绕道留了出来。就好像一棵树变成了一个超迷你院子。
03
砍树是个大事。办公室租在湖南路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一个真理:每当有人要宣示主权,第一件事就是砍树。
这个真理后来在我住的小区里也得到了验证。有邻居投诉树太高树冠太大,影响了采光,天天在群里要物业处理,物业做别的事能拖就拖,但对于砍树这事总是积极主动。我猜想原因大概一是砍树之后可以减少物业的其它支出,比如扫落叶,比如虫害防治,没准还会有间接的安保支出;二是砍掉的那些枝杈还有变现的机会。总之说是修形,结果和那新闻里的做法一模一样——每棵树都修成两三米高的树桩。到了夏天,白蛾成灾,满墙满楼爬满了幼虫,人们想起因为修树的时候所有的鸟窝也都修掉了。那些总是喜欢冲在前面发表意见、当年斩钉截铁地号召修树的女士们,现在又在张罗钉些箱子放些小米召那些鸟回来。我觉得她们跟我们城里的政策制定者还真是很像的。
沈阿姨——我们在湖南路时最重要的邻居,是带领我们发现这个真理的人。那时,她面对的是一群半是机关干部装束半是户外工作服感觉衣服的中年男人,这些男人来自徐房绿化。沈阿姨交代的任务是要砍掉树的三分之一左右的枝杈。对于以绿化为己任的本区最高管理机构来说,沈阿姨这样的要求有悖他们的工作伦理以及管理宗旨。但他们面对的是沈阿姨,沈阿姨从官方角度是楼组长,在私人角度是上海或者任何一个城市里那种有莫名权威和资源的资深女士,而徐房绿化虽说是一级管理机构,但广义上也是沈阿姨的邻居——他们的办公室就在我们的弄堂口。沈阿姨因此认为有义务提升他们的管理水平和业务能力并愿意身体力行适时为他们做出指导。当然,另外一个要考虑的是,只有他们才有更专业的设备来对付这个庞大的香樟树。长年以来,她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与她窗外的大香樟树做斗争,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一直没有放弃。那香樟树是我见过最壮观的一个,树干黢黑充满力量,树冠庞大,笼罩住了我们窗外的大半个天空,只有在它的边缘有那么一小块地方,可以看到三楼沈阿姨家的阳台,那里长年晾晒着沈阿姨和沈先生颜色鲜艳的睡衣和内裤,与香樟树一起构成我们完整的天际线。多丽丝·莱辛讲过一个故事。“每一天,”有个慷慨激昂的人说,“都有人打电话过来,我去现场一看,是棵漂亮的大树。它得花上一百年的时间才能长成这样——跟树木比起来,我们算老几啊?……就说昨天吧,我才把一棵梣树砍到只剩三英尺。可以做张桌子。那个臭婆娘说。就一张破桌子,而那棵树却得长一百年哪。”我得承认,很多时候我跟这个人的想法看起来差不多,喜欢在树木面前保持谦卑,总是想代言它们的样子,但在人面前,那可不好说了,人算老几啊。沈阿姨在指挥徐房绿化的时候,我们就仿佛看到树界的奥斯维辛,新一代的人伦悲剧,人啊,你们作恶还少啊,人啊,第七次物种大灭绝就在我们手中……作为代言人,我们得适时表达我们的立场,制止这种人类暴行。我们克制了这种冲动。一位叫约翰·厄里的社会学家,他把我们这种执着称为“游客凝视”,这通常出现在旅行者身上,他们跑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对异域风情有一种特别的热爱,类似于早期面对北京胡同里早晨公共厕所门口的排队,拿各种粗壮大镜头对准的藏民土著的脸,热爱所有本地的东西,这其中包括没有被随意处置的树——我们觉得这东西是高级的,是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态度,是人与自然。但对于原住民来说,别挡我晾内衣的光。沈阿姨觉得挡住他们家的阳光是不高级的,至于是影响晾内衣还是影响了阳光抚慰,其实并不重要。沈阿姨有权要求阳光。也许阳光真的更重要。
在湖南路那时的“场域”里,这是一种原住民文化和异域主义的文化冲突。我们扮演的是中产阶级矫情的那个角色,社会学家给我们这种行为取了个名字,叫“对他人物品的资产阶级式欲求”——社会学家说当人们把一个物品当作遗产来对待时,就不可避免地打开了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和“他者”的日常生活之间的缺口,后者成为人们“博物馆化欲望”的对象。沈阿姨的日常阳光需求与我们看一棵自由的树之间就是生活与文化遗产之间的区隔。那棵香樟树在我们眼中是博物馆,在沈阿姨那里就是生活的不方便。
说起来,沈阿姨的斗争结果一直都很有限。徐房绿化一直没有来砍树(我很是高兴)。沈阿姨每每跟我投诉官僚主义的不作为之后,就要自己拿一个带着剪刀的长竹竿去够离她最近的枝条。这种蚍蜉撼树般的努力也不是没有成效,它让香樟的某一根枝干的树梢像得了小儿麻痹症一般萎缩了下去,因为沈阿姨只有把树枝拉断的能力,有些树皮还勾连的地方垂在空中,她也就作罢了。时间一久,这一小片树梢发黄枯萎,就好像在一整片绿色的背景板上点上了几个小黄点。
这种充满了象征主义的人类动作后来我在长乐路上也看到过一次。不过不是砍树。6 月中旬的时候,我走过邮电医院门口,发现有人在一棵悬铃木的树干上喷了小广告:办证刻章 187**312898。其中两个数字已经随着掉落的树皮糊掉了。悬铃木进入换皮季,大片大片的树皮剥落,有的时候还会砸中路人。“办证”也翘了起来,如果我伸手按一下,它就会随着发脆的树皮掉在地上。
04
走在这个长乐路田字格里,大部分人看到的就是二球悬铃木。实际上哪怕单就悬铃木而言也不一样。同样遮天蔽日,陕西南路的悬铃木最粗壮,巨鹿路和长乐路次之,新乐路最末。
新乐路的植被似乎都在院落里,越过紧闭的院门可以看到高而瘦的水杉,年岁不大却密在一起的香樟。22 号的园景修得独好,一棵大树认不出来,身上被缠满灯带,与它的一墙之隔的人行道上,一棵梓树有了年头,书皮中空,被填上了水泥,远远一看灰黑两色矗立街口,远胜当代艺术装置。
陕西南路上有一弄堂极窄,却挤满大棵枫杨,这树在二球悬铃木爆球前后,会落下一嘟噜一嘟噜像毛毛虫一样的花。

靠近襄阳路口的首席公馆外墙,梧桐一枝独秀,过了路口有一棵大槐树,再往前走房子都变成了花园住宅,通常都用法国冬青作围墙树。新乐路襄阳公园门口、东正教堂对面有两棵喜树,据说稀有,结的果是翠绿的小毛球——不是真的毛,一堆葵花子皮一般的薄片攒在一起,像小姑娘的头绳——很喜感地挂了一树。把落在地上的捡回去,不过一日就转了褐色。
巨鹿路作协的庭院门口三棵瓜子黄杨,两棵带了花岗岩铭牌。现在树比以前金贵得多,好些编了号,还带着二维码。2002 年立了牌子说它们有 80 岁,到现在也是百岁了。见我看树,门卫爷叔本来要拦,马上改为兴致勃勃引我去看另一棵。“老古董哎,侬手机扫扫看,都有简历的。”如果我看的是人,估计没有这个待遇。
再往前走一点的四方新城,小区道路两边多是香樟和腊梅。
如果不算作协,蒲园旁边那家叫“棉花田”的买手店的,是树景最成气势的一家。两棵大石榴在春末夏初像点着了一般开满一树红花,旁边是两棵梧桐和香樟,顺着树往里走有个小门,可以一路通到办公室楼下那个野园子。
常春藤是藤本,但也值得说一说。它以面积取胜,但也是游客凝视型植物,本地人是不喜欢的。有一天下班,看到楼下来了一个主播,正在对着墙上的常春藤感慨:这些上海的海派建筑上,已经被整片绿色覆盖……
王老师说他们把所有的常春藤都拉掉了。这事我只在常春藤爬过阳台门的时候干过,如果不干预,就会被封在里面——但不是用手拉,是用剪刀剪的。看着是小细藤,其实极韧,用手扯只会拉掉一点皮,然后深深嵌进手掌里。只有在拉扯常春藤的时候,你才会去看它密密的脚。如壁虎吸盘一般。以前去看过一些废墟,灰色水泥墙面上所有的常春藤已经除去,只有凑近了看,才会看到密密麻麻的小点,风化成黑灰色,都是和这幢建筑物生死与共的脚。
在那些可以穿来穿去的弄堂里,无花果树常见。
对门豪宅墙根底下长出一棵毛泡桐,枝干细弱,叶子却很大,心形,看比例像个草本,不知道是不是能挺过冬天。
泡桐跟毛泡桐有点像,但更普遍。普遍到甚至有了入侵物种的感觉。这树可以长在任何地方,而且感觉从来不死。经常看到房顶上,默默有一棵看着挺健壮的小树,差不多就是泡桐。
05
办公室在湖南路的时候,窗外有一天徐房绿化嘿哟嘿哟地喊起了号子。隔壁院子门口有棵泡桐死了——据说死了,平时很少有人注意到它的死,因为下雨之后它会生出厚厚一层绒绿苔鲜,有时候还有长出让人肉麻的木耳,迎着阳光可见其褐色透明的肉质,偶然有松鼠拿它做跑酷跳板,它称得上是一个生态,谁会注意到它已经是一棵内心中空的死树呢?徐房绿化官宣了它的死亡。并且以专业设备把它锯成一个木桩,树桩底部连着根的部分,铺张到有一米粗的直径,中空内心暴露出来,果然里面是碎石和碎砖块。
嘿哟嘿哟喊号子那天是挪树桩。头天来了至少五个工人。穿橙色和蓝色工作服,带着镐和手工锯,又刨又掘,刨去一些烂根桩之后,发现这是一个隐形的大工程。隔日上午,人数多了一倍,作业工具也多了电锯,将树桩围成一圈,还喊起了号子。隔一会儿去看,树桩周边的土石已被挖散,只是根桩还深陷其中,颇像一颗顽固智齿。电锯此时上场,横竖切成几块,切一会儿掘一会儿,又费一番功夫。最后一下,是一个师傅一镐子插进一块大桩,就地拔了起来,至此有电锯照应的作业面全部清除,豁口深至大宅围墙之下,地面上的部分算是清理干净了。

至于泡桐在地下的根系,若用强大的地球为其 CT,估计绵绵不绝,延续数里。《树的秘密生活》曾经提过,树有自己的通信体系,一棵树遭遇变故,其根系上的菌类会迅速传递到另一棵,于是方圆周边的同类会自动产生某种免疫机制,比如抵御虫害的化学物质。虽然不能走动不能言语,也具备某种变通能力。现在这棵泡桐被人如智齿般挖去地面根桩(后来工人又用早先挖出来的砖块重新把烂糟糟的大坑填满),它的友邻们是否会进行最终的告别(想必从宣告第一次死亡开始它们就安排了哀悼),只待微生物把那些地下的根系慢慢销蚀,挨家挨户吸收了去,把老友化作自己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