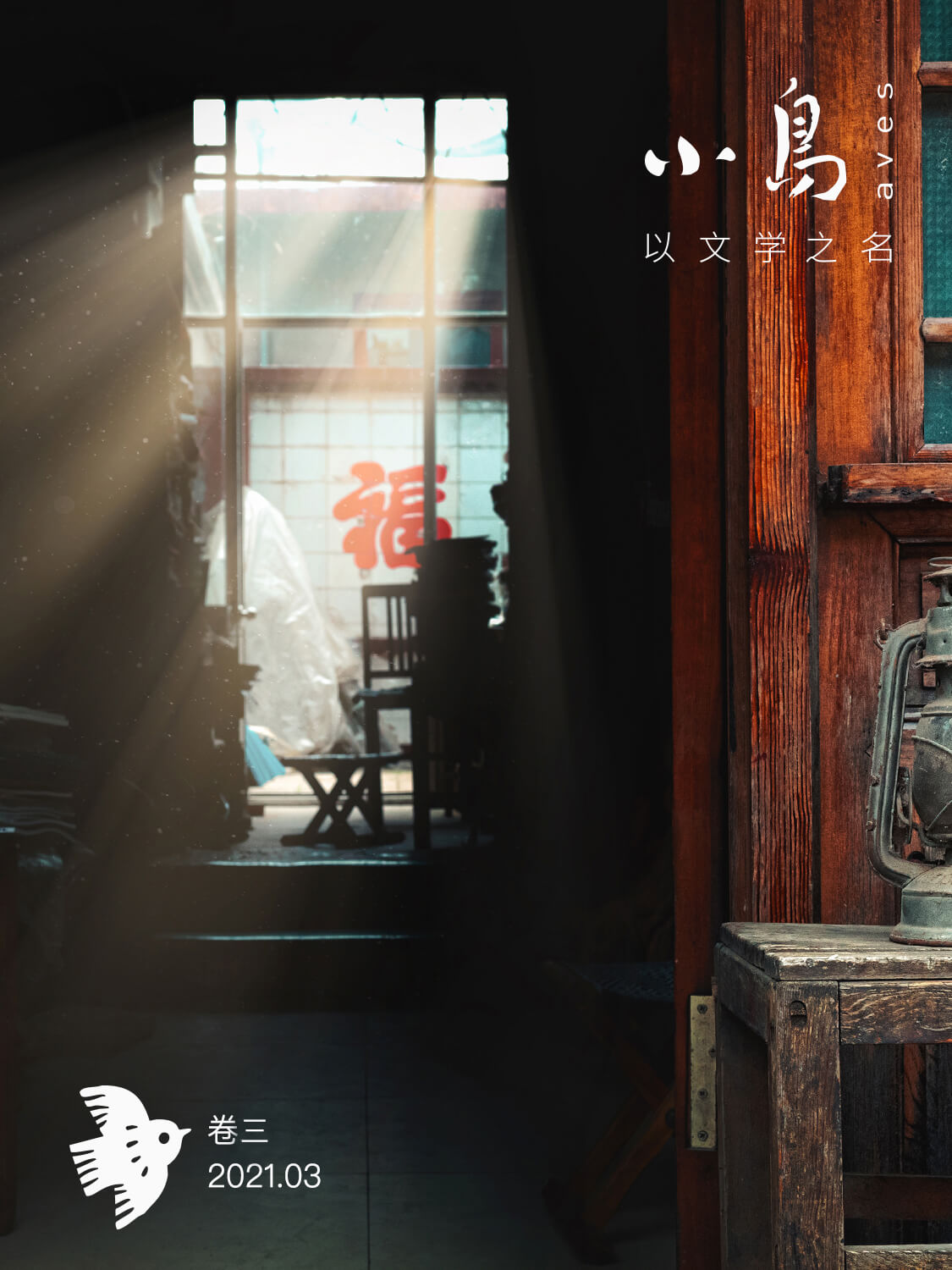一
我回到这个破地儿,是秦楠跟我说,刘步跳楼了,抱着一本新华字典。十五年前,我和秦楠在这吃冷面,那时的老板,是秦楠她爸的战友,叫老严。老严转业后,和秦爸一块儿,给运输队开大车,从元市往烟台运石油。超期服役的苏联老车,赶上大雪,刹车失灵、操纵杆失灵,眼看要追尾,老严方向盘一别,开下路肩,前挡风给冻枝扎漏,人从窟窿里射出去,落在雪地里,居然毫发无损。他爬起来,碰碰车,已经在雪地上冻实诚了,就摘了车钥匙,爬上公路,去找派出所。走了有一里地,老严感觉不到脚了,低头看,竟也没有,往前走两步,还能走,就是没声,光上半身在飘。北风吹拂,四下漆黑,他一屁股坐在路边,发现屁股还在,顺着往下摸,腿也在,再摸底下,是个大冰窠。他心里有数了,掏出火柴,点着烟盒,扔在冰窠上。火光太小,化不了雪,只能看个影儿,他估摸脚还在,就是鞋没了,应该从车里窜出去就没了。鞋丢了,他没兴头再走,那是双新鞋,皮的,回家不好交代。他偎在雪里,上下眼皮一挨,就看见有人撬马葫芦盖一样,要撬走他的车。他跳起来往回跑,钻进车里,把方向盘卸下,扛在肩上,去寻警察,和另一双鞋。
照理说,运输队该给老严开表彰大会,他车上拉着半吨石油,要是追尾了客车,后果不堪设想。可惜他舍生未取义,车毁人未亡,又赶上百天会战,领导就和他商量,分他一辆新解放,把他从跨省长线,调成短线,专跑省内。老严当时没意见,第二天就把车让给了秦爸,说再不碰方向盘。领导寻思,老严这是闹情绪,赶着开春,分了他一套房,48 平,一楼,中门。老严想换个六楼,他住惯了平房,受不了头顶有脚丫子,也住怕了平房,做梦都在爬楼梯。领导劝他,一楼好,临道,对街就是一中,你媳妇没工作,正好干点小买卖。老严琢磨,领导的意思是,公房可以私用?这一犹豫,领导又批了他两架大铁床,纯蓝床架,床头两条大金鱼,鲜淋淋像要游出来。老严赶紧接了钥匙,回村里把媳妇接来,儿子送进运输小学。
安置妥当,时已入夏,老严抱了两个西瓜,去找领导,说想打更。领导一听就急了,那是 1991 年,打更的好找,开车的难寻,况且队里有打更的,是领导叔伯堂哥的岳丈,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但也比老严近。老严说,要不他也舍不得这身技术,实在是不敢,不用打着火,手一碰方向盘,他眼前就两个车头灯,给前车照得通亮,16 排座,第四排是个秃脑瓜亮,一个小姑娘,有病,活不过今年,旁边那个是她妈,怀着六个月的身子,胎儿发际线靠后,头发一半弯弯曲曲,粘在头顶,一半飘在羊水里,像面旗子。领导看他眼圈雀黑,印堂发青,三十出头的汉子,几个月熬成了干儿,现在还满嘴胡话,出车是冒进了点,就让他先进维修组。队里于是炸了锅,说老严大难不死,开了天眼,这要搁乡下,一定有人逼他出马。都说开了天眼的人,头十个算得最准,往后就差点意思,大家都巴结老严,求他给算一算。
秦爸不信这个,每隔半个月,跑了长线回来,照常找老战友喝酒。老严说:你要生姑娘啊。秦楠当时都三岁了,秦爸就骂:我那满月酒、百天酒、抓周酒,你喝马肚子里了?老严说:你回家问问嫂子。这一问,秦爸吃惊不小,媳妇又怀上了。秦爸说:生了老二,全家张嘴喝西北风?媳妇说:开除你正好,一个月就两天着家,姑娘现在都不认你。秦爸说:姑娘叫我大熊,我让的,你管着吗?媳妇:说得好,你也管不着我。秦楠她爸说:有管得了你的,我把你妈找来。他这个丈母娘,从前跳大神,现在赶时髦,信了基督教,两年后还要被骗去练气功。丈母娘一听,开天眼的说这胎还是女孩,马上忘了自己是教徒,撵着闺女去打了胎。
方向盘以外的故障,老严都能修,补胎尤其是把好手,不光能补好,还能让胎爆在去程的中点,前后不差五百米。这个距离非常考究,一是开出去够远,不能回队里换胎,二是回来还要跑十天,新胎也磨成了旧胎,反正肉眼不好分辨。新胎一个 20,旧胎 12,爆一个胎能挣 8 块,跑长途的师傅是赚了,维修组长的外快就缩了水。很快,老严被踢出维修组,去排出车表。自打排上班表,老严每个月去队里两天,闲得够呛,搁家开起了小饭馆,一开十几年,十几年不挂招牌,也不修门脸,但客源稳定,都是战友的孩子。一中没有食堂,他家算个小食堂,学生按月包伙。以前多少钱不知道,到了 2003 年,一个月是 40 块。
秦楠捏着她爸给的 40 块钱,叫声叔,给我点了碗冷面。说是冷面,上来时汤还是热的,烫嘴。我拿筷子一扎,一坨面跟上来,像张金丝饼。秦楠咬一口,吐到碗里说:有冰碴。完了把面饼翻个面,又咬一口,还是吐回碗里。我说:你让我怎么吃?秦楠不理我,往汤里倒醋,一瓶醋倒空,接着倒酱油。我在桌子底下拉她:你叔出来了。她说:叔什么叔,专杀熟人,我弟就是他杀的。又往碗里加了半缸辣椒油,汤色恢复红润。我说:你还没给钱吧?她把方便筷撅成两截,丢在地上,拽着我钻出窗户,去买炸串。串摊人多,摊主让我们自己抹料,秦楠抢不到刷子,就捏着签子,在调料桶里烂滚一气,拎出来时,辣椒面比鸡柳还厚。秦楠说:我要有弟弟了。
2003 年夏至,秦楠的三舅妈生了个男孩,就是刘步。那年我们初三,初中四年制,没有升学压力,秦楠拽上我,逃学去看刘步。他黑黑的,嘴唇外翻,看起来像个非洲同胞。秦楠说:真好看。我说:他右手中指有点短。秦楠说:跟我一样,爱啃指甲。一年后,出了中考考场,我们直奔三舅家,刘步正在抓周,秦楠把一本《尼罗河女儿》,悄悄塞到铺红布的桌上。
那是十五年前的事,那时我们 15 岁。刘步也 15 岁,今年,以及永远。
秦楠来了,比五年前瘦了不少,看起来也就 120 斤。她说:刘步跳楼了。我说:在哪跳的?秦楠说:初四咱班那。我说:那不才四楼吗?她说:学校抽风,把丁香树砍了,他大头朝下,扎进了断根里。我想起那些丁香花的香气,一蓬一蓬紫色的,和栏杆外面音像社放的盗版磁带,“你说你最爱丁香花,因为你的名字就是它”,十五年前很红的歌,可以写进作文里,假装是泰戈尔写的。
我说:有遗书吗?秦楠摇头:三舅妈觉得是早恋,发现他送刘思甄回家,说了他几句,没想到能自杀。我说:你觉得呢?秦楠说:你知道我怎么想的。我看着她:是惠老师。秦楠点头:老惠教过的学生,每个都想跳楼,咱们那届没人跳,是她运气。我说:今天就查这事?秦楠说:先找刘思甄,看刘步留没留下话。我说:真找吗?秦楠说:真找,能当个借口。我说:你找老惠班上学生,跟她打招呼了?秦楠说:不进校园,在门口堵。我站起来说:你堵吧,我看看老惠去。秦楠拽住我:毕业这 15 年,你回来看过她?我说:我闲的?秦楠说:凡她教过的学生,没一个回来看她的,你这不帮倒忙吗?
眼看四点半,一中要放学,我和秦楠从店里出来,过街就是一中正门。我问秦楠:学校赔钱了吗?秦楠说:说赔 20 万,我没细听。我说:要是老惠的责任,能多赔吗?秦楠摇摇头。下课铃响了,不是我们念书时的铁铃,换成了卡农。孩子们背着书包,趿拉着球鞋,一个个挨着墙根,往远处蹭,看着像赶尸队,好像我们看不到的地方,有一根鞭子在抽。
秦楠突然说:不能再让她当老师了。
老惠虽然是汉族,我和秦楠进了她的班,却像回到元朝,成了她治下的第三类人。第一类人,来自一中隔壁的供应小学,父母清一色机关里的干部。第二类人,地调小学毕业,父母是工人还是干部,有待甄别。第三类人,就是我和秦楠这样的,念运输小学,父亲都是跑大车的工人。第四类人,但凡早生一年,都没资格进一中,炼油厂才并入油田,父母毫无根基,就敢把孩子送来给老惠教?也不撒泡尿照照。第五类人,在老惠那就不算人了,俗称“地方生”,每年学费都比油田子女多 800 块。
最后两类人,加起来没有十个,我和秦楠作为名义上的夹心阶层,实际上的下等人,坐在倒数第二排、正数第九排,当起九品芝麻瓜官。直到期中考试后,我才得到拔擢,官升四品,派去给李金杨当同桌。李金杨的妈,我进一中第一天就认识,管水房子的,负责给学生热铁饭盒,他爸开了个小卖部,就在水房子旁边,不管冬夏,终日水汽氤氲,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澡堂子。要是没这个小卖部,李金杨肯定跟我同属第三类人,他的幸运在于,老惠有个儿子,爱吃辣片和鱼皮豆,才上小学一年级,每天都要丢铅笔、名签和红领巾,往后还要丢算盘、书包和计算器。这儿子每天一放学,就跑到我们班,坐在讲桌上,接老惠的班:我说你呢,别说话!你笑啥?给我上走廊站着!我们只要不抬头,不理他就行,最倒霉的是李金杨,要是那孩子说:我饿了!李金杨就得顶风冒雨,跑到小卖部找他爸要两个面包。
我串过去第一天,老惠就把话挑明了:要是李金杨成绩不进步,下学期你哪来回哪去。李金杨很看不上我,认为我是奸细,专门给老惠打小报告,不让前后桌理我。可我要是一摔书,他还真害怕,嗓子立刻尖了,像要哭,我要是不哄他,他能擤一天鼻涕。我心理落差非常大,本来预备当童养媳的,没想到对方是个林黛玉。秦楠看我给李金杨写作业,问我:你喜欢他?我说:就那榆木疙瘩,我伺候不了,考完试你帮我搬桌子。秦楠说:配眼镜的钱,你攒够了?我说:有那钱,我情愿给老惠送点礼。秦楠说:前排好吗?好,我说,空气清新,人口密度低,跟新西兰似的,椅子腿和桌腿之间,能塞进一只脚。秦楠说:你有点出息,往前考,登陆南极。
那是十五年前的事,那时我们 15 岁。刘步也 15 岁,今年,以及永远。
期末考试,我又前进了几名,利用价值提高,累进至第二排,给语文老师的大侄子当同桌。秦楠看此路可行,才开始发力,轻松考进前十,被老惠指派,负责教育局领导家的田公子。一听要给田亘当同桌,秦楠先吓哭了。田亘混蛋出了名,脏话不离口,初一就敢打高三的,就前两天,还砸了班里一块玻璃黑板,但老惠那个势利眼,怎么可能让领导赔钱?结果全班同学,每人平摊五块钱,替田公子买了单。我说:田亘还不如李金杨。秦楠非常丧气:咱又没的选。也是,我们没钱给老惠送礼,只好把自己当礼物,利用自己。
秦楠坐过去第一天,就被田亘气哭了。哭完这一场,秦楠破罐破摔,和田亘谈起了恋爱,就像言情剧里,红袖添香的小丫头,再和少爷情投意合,也是个工具人,她的作用在于,劝少爷改邪归正,使他成为新科状元郎。秦楠成了第二个老惠,每天给田亘吃小灶,出小卷子,改题打分,帮他做错题本,反正不管田亘有多喜欢秦楠,田亘他妈都要更喜欢她一点,秦楠简直从一开始,就走上了贤惠儿媳的道路。后来故事发展到,田亘他妈在一次检查中,和校领导大夸老惠,又在老惠面前,大夸秦楠,给老惠长了大脸。在十四岁的我们眼里,这段感情算是过了明路。
初三之后,换了新的语文老师,我开始烦我同桌,那个前语文老师的大侄子,连他喘气都嫌吵。这天他又在喘气,我骂他:你烦不烦啊?他特别懵。我说:你嗓子眼里的痰都快糊我脸上了!他脸红了,一直烧到脖子根。过了半天,我才发现他在憋气:你神经病啊!他突然说:你放心。我说:什么?他说:我爷是中医,儿科的。那一刻,我完全明白他在说什么。到了下学期,老惠突发奇想,放了学不许我们回家,原地上晚自习。4 点 45 放学,休息 15 分钟,从 5 点钟上到 5 点 45,头两天还讲讲题,后来就做卷子,每个人饿得东倒西歪。饿了两周,老惠从后门进来,右手拎扫帚,拍苍蝇一样,拍住几个说小话的同学,当时秦楠正给田亘讲题,也给她拍了一下,一脑袋的灰。打完人,老惠拿扫帚封住前门,一屁股坐到秦楠桌上,开始骂:操他妈的,我一天天,累得跟狗似的,为了你们,连家都不顾了,我为的是谁?我他妈的没孩子吗?你们家长一个个,穿金戴银,小脸抹佻白,花点钱在你们身上,可剜了她的肉了!回家告诉你们爹妈,谁他妈的告的我,别他妈的装缩头乌龟!大大方方告诉我,我肯定以后不管你了,我肯定把你供起来,让你当太上皇!看最后坑的是谁!看你们爹妈和我,最后哭的是谁!骂到激动处,她抓起秦楠的书,一本扔向打喷嚏的,一本射中撇嘴的,连那个低头抠手的也没放过,搞得我后背直刺挠,好像生了虱子。
老惠被告了,晚自习就不上了,一直也没提收钱的事。直到两个月后,班长看着我们上自习时,忽然哭了,说惠老师多不容易,每天一个人带孩子——我问秦楠:老惠离婚了?秦楠说:她老公跟我爸一样,开大车的。班长抒完情,通知我们:明天每人交 15 块钱。我们上了两周晚自习,十天,每天一块五,其实不算贵。
那是 2003 年,开始是非典,每天下午打扫卫生,喷消毒水。入夏后,学校搞操场硬化,下午就改成后院拔草,搞到后面,学校没钱了,每天组织一个年级的学生去阶梯教室看电影,也不怕传染了。头天看电影,第二天早上就交钱,每个学生一块钱,比租碟贵了点,比电影院是便宜多了,何况我们从小没见过电影院,只去过工人文化宫,银幕底下伸出个主席台。上午交了钱,下午我们回到操场上,搬自己出钱买的地砖,文体生活无比丰富。
上了初四,老惠愈加天恩难测,昨儿被她夸上天的人,明儿就挨批斗,连秦楠和田亘都被她拆开了。她忽然不管你爹妈是谁,也不管你上次考第几,但凡气不顺,她张嘴就骂,伸手就打,搞得我们根本不敢把塑料格尺放在桌面上,给老惠看见,抄起来就打折了,她才不管你那是脖颈子还是后脑勺。老惠身高 1 米 45,我们到了初四,全都长得比她高,于是她发明了新办法,让我们蹲着,她坐在椅子上,骂一句,踹一脚,什么时候你蹲不住,扑通一声坐在地上,什么时候算完。时间一长,我们都养成了最朴素的辩证观,觉得福兮祸之所伏,被夸就是挨踹的前兆。全班人心惶惶,恍如东厂,我们在学习数理化的同时,无师自通了察言观色,极为媚上。田亘那小子,站起来 1 米 8,被老惠踹了一脚,就坐地上不起来了。秦楠说:再不毕业,再来一次侵华战争,咱们都得当汉奸。
二
秦楠堵在校门口,逮着个子高一点,看起来要被书包压死的就问:是初三一班吗?不是,不是,不是——有的不等她张口,直接跳开了,好像她裸露着断肢,夹着一只搪瓷碗,正沿路乞讨。我在她身后,遥遥见着一个像老惠的,都要打个哆嗦。我有十几年,没到过中学了,光看微博,中学女生都美艳异常,不日就能选秀出道。再看短视频,她们说话露骨,早就看穿世情,被包养抛弃了几回。可真站在这,我发现所有男生,都剃着平头,脸上冒痘,所有女生,都头发油腻,鞋底踩着没扦边的校服裤子。就算是送回 2000 年,也跟我们土得不相上下。偶尔迎面走来一个个子小小,头不梳脸不洗的女生,我都想挎住她的手臂,去买一块钱四个的小笼包。我和秦楠,当年也是初三一班的学生,我们毕业了,老惠年复一年地带着一班,和当年一样,带最好的班级,教最好的生源,出最好的战绩——
想啥呢?秦楠抓住我,把我往前拎:一班出来了,老惠今儿没来上课,好机会。
我看到一个男生,背弯得像伏尔加河上的的纤夫,抓住他问:刘思甄出来了吗?他后背像通了电,一下子站直了,书包掉在地上。对不起啊,我赶紧松手。他捡起书包,扑扑灰,背上走了,我看他站直了还没有一米六,八成是初一的。一个高个女生走过来,我问她:你是初三一班的吗?女生说:我二班的。我说:你认识刘思甄吗?刚才那个小个男生突然回来了:她请假了。我说:刘思甄?男生点点头:我是她前桌,你找她有事吗?我指指秦楠:她是刘步的姐姐。男生很白,此时脸上又白了一度,侧脸像极了我初中追的韩星,一时想不起叫啥。男生说:老师不让我们说刘步的事。说完就走了。
秦楠正拦住一个男生问:你们班长是谁?男生高高大大,抱个篮球,身上冒着热气:刚还走我前面,小矮个儿,怎么没影了?我问他:像宋承宪那个?男生说:宋承宪是谁?秦楠说:他叫什么?男生一头汗开始往下淌:吴骓,惠老师的儿子。
我跟秦楠说:老惠的儿子,咱们上学时就七八岁,现在该上大学了吧?秦楠说:死了。我说:什么?她说:你忘了初四开学,老惠一个月没来上班?我说:她不是意外怀孕,去做人流吗?她摇头:那个暑假,她大儿子起水痘,开始没注意,后来发展成病毒性脑炎,拖死了。我说:你啥时候知道的?秦楠说:高一上学期,下雪天田亘来看我,听他说的。要这么算,我们中考时,老惠已经怀孕三个月了,一点没看出来。回想初四那年,老惠除了发疯,把我们班一锥子捅不出一声的乖乖女、全校最有希望的苗子,从二楼实验室拽着领子,拖过长长的走廊,又一个一个台阶,就差薅着头发薅到四楼之外,没再做什么出格的事。我说:老惠的老二,至少比刘步小一岁半,怎么跟他在一个班?秦楠说:你刚没听见,她儿子初一就是班长吗?我想,老惠真做得出来,等于皇上是她,宰相是她儿子,这朝廷还不让她治死了。
学生都走光了,剩下稀稀落落几个,都是被找家长的倒霉蛋。我和秦楠不得其法,只好回到刚才碰头的小店。我问她:你记得这吗?秦楠说:我爸战友开的。我说:你糟蹋了人家不少酱油、醋。秦楠说:是他先糟蹋面的。过了马路,秦楠突然说:生的冷面像塑料,立在墙角,扫帚似的,那么长一捆,也放不进冰箱,不知道咋能煮出冰碴来。原来,秦楠都记得。记得没有刘步的时候,这店就在这了,现在刘步没有了,它还是在这,鸟枪换炮,成了面包店。
一进面包店,秦楠就看见那个抱篮球的大个子,跟同学在长桌子上写作业,两男三女,旁边空着一把椅子,堆满了校服和书包。秦楠走过去,拖一把椅子坐下,看他们没点东西,就把水牌拿过来,让他们点。其他人不吱声,大个子做主,给每人点了一杯最便宜的美式,说作业多,怕困。秦楠让他们先写作业,等初中部的灯熄了,她给每人叫了一份意大利面,吃完了又叫薯条和冰激凌,让他们点自己喜欢喝的。这次孩子们都张口了,有要拿铁的,要卡布奇诺的,发音都是美式英语,比我们当年强多了。我还记得第一次,穿哥特裙的侍者问我喝什么,我说蓝山。我不知道蓝山是一种咖啡豆,是地图上的一个点,是牙买加的一座山。
吃饱喝足,孩子们话密起来。一个女生说:全校就惠老师讲究多,像我们女生,扎头发得用黑皮套,如果你之前是短头发,上了初三就不能留长。男生说:大夏天的,不许我们穿跨栏背心,想穿个裤衩吧,还必须过膝。另一个女生说:我长得太快,校服小了,惠老师就帮我从上一届买了一套,100 块钱。第三个女生捂着嘴乐:我听毕业生说,旧校服是惠老师找他们要的,没花钱。
要说生财有道,老惠是个中老手。我和秦楠那时候,校服是有,都当屁股垫儿使,每周升旗穿 10 分钟就行。老惠不甘寂寞,非给我们搞出一套班服,强制穿,不买不行,75 一套,进货大概 40,每套她净赚 35——要说班里的显贵子女真不少,难得老惠居安思危,家长礼送得再多,也没有蒙蔽她的双眼,扰乱她对金钱的嗅觉。
时间一长,我们都养成了最朴素的辩证观,觉得福兮祸之所伏
男生说:惠老师其实对我们还行,对外班才狠呢。大个子说:可不是,要不是出了事,我还不知道她那大衣是新买的。女生说:听她扯吧,两年前我就看她穿过。另一个女生见我们好奇,就从头说起:过完年,惠老师穿了一件孔雀蓝皮羽绒,在走廊上,被初一六班的陈刚溅上了钢笔水,手指盖这么点的污渍,她非让陈刚照价赔。陈刚家里穷,家长真没钱,就求惠老师,想给她塞个红包,让她拿到洗衣店干洗,她非说洗不掉,让人家赔件新的。男生插嘴道:她还说,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神叨叨的。
看男生那样子,一定不知道黄世仁和白毛女是谁。我想起老惠当年骂齐天一,说他是横路进二,当时的我,也不知道谁是横路进二,我问我妈,我妈不告诉我。后来听老惠骂的次数多了,就明白此人是个傻子,也是,齐天一数学考四十分,当然是个傻子。
等孩子们八卦完,秦楠问:刘步最近惹事了?五个孩子都摇头。一个非常肯定:没有。另一个说:这才开学一个月。第三个,也就是大个子,指着自己说:这个月惠老师一直在骂我,说我一条鱼搅了一锅腥。第四个说:上学期,刘步趁夏天雨不注意,把她椅子搬走了,夏天雨坐到了地上,被她妈带去医院拍片,因为这个事,惠老师说他道德败坏。秦楠说:还有呢?第五个说:说刘步长得像乌鸦。我看看秦楠,照老惠的嘴,这骂得不算狠,等于随口的小幽默。我问:夏天雨受伤了吗?男生说:没有,拍片看了,没骨折。第四个说:他们那一片,就爱搬椅子玩,刘步也被夏天雨搬过,也坐过地上,他就没告老师。秦楠说:这是几月份的事?第四个说:四月份,学校刚停气。秦楠不相信:六个月前?我说:当时夏天雨是刘步的同桌?嗯,大个子说,出了这个事,惠老师就把夏天雨调走,让刘思甄坐过去了。第四个纠正他:是夏天雨转学走了,刘思甄才坐过去。
看来,还得找这个刘思甄。刘步跳楼时,和她是同桌,刘步跳楼前一周,每天都送她回家。
面包店要打烊了,门外一声鸣笛,五个孩子呼啦啦上了车,挤得不可开交。秦楠说:记得我爸来接咱俩吗?我说:我坐后座,你骑在大梁上,掰一半康乐果给我。秦楠说:我喜欢骑大梁。忽然,一个女生跑回来,要了一杯咖啡,加了秦楠的微信。我说:发现没,她喜欢刘步。秦楠眼睛红了:天知道他为什么要死。我说:头一回被老惠骂乌鸦,我也想死。秦楠说:就一个道儿。我说:我还不是故意的,前桌一回头,白衬衫刮在我油笔上。秦楠说:老惠把你的笔袋,直接从窗户扔出去了。我说:多亏是一楼。秦楠说:现在想起来,算个屁。我说:如果我死了,刘步就不用跳楼,老惠也当不了他班主任。秦楠说:你想多了,刘步刚死,学校就说他是癔症,精神不正常才跳楼的。我说:所以是讹传?他根本没抱新华字典?秦楠说:到现在,监控也不给亲属看,学校要保老惠。
第二天,刘思甄还是没来上学,大个子看见秦楠,带球过人一样闪开了,另外几个孩子,也没来面包店写作业。打烊时,秦楠收到一条微信:惠老师看见你了。
第三天是十一长假前,最后一个工作日,下午没到四点,校门口就聚集了片警、驻校警察、政教老师、年级组长和体育老师。一中还是有些进步,至少体育老师和市场接轨了,长得像举铁达人,一触即发的氛围里,手里的握力器仍然一张一合,后来秦楠推了我一把,我才看清是钳子。她说:大假前,一向要大打一架,江湖恩怨了了,才好回家过节。我说:那个人你认识吗?秦楠说:露脚脖那个?我说:戴眼镜,正往这边走,秃顶,在掏烟。坏了,秦楠说,他是校长,姓陈。我说:你快走,去北门。
我往嘴里塞一块口香糖,嚼起来。陈校长走到我面前,没说话,身边的秘书替他问:看您来了三天了,揪住学生就问,是哪家媒体啊?我说:我这儿毕业的,来看老师。秘书笑了:您找哪位老师,跟我进门卫室,我把他电话给您。我说:不急,老师总在那,群架不看就没了。秘书说:什么?我说:你挡我道了。
才两分钟,小混混肉眼可见地多起来,细腿裤,牛仔上衣,敞着怀,口罩拉到下巴底下,单拎哪个出来,都看不出是小混混,可搁在一起,就瞅着贼眉鼠眼。敌人还没放学,他们暂时是良民,当着栏杆里的大盖帽们,掏出烟来抽。一个男生看我在嚼口香糖,凑过来问:还有吗?我说:得换,不白给。他问:怎么换?我说:说道说道,今儿什么恩怨。男生说:几个贱货瞎逼逼,说我朋友的妹子怀上了。我说:你不知道什么是避孕套吗?男生说:我知道啊,又不是我的妹子。我说:你第一个避孕套哪来的?操,他把烟扔到地上。我说:自古以来,一中就是情场,周边那些学校,要是没有一中,真不知道要怎么性启蒙。男生不见了,门口骚动起来,骚动完了还是骚动,干打雷不下雨,我看出来了,这帮孩子是隔壁二中的,另一个情场。
卡农一响,太阳下山,秃顶校长不见了,黏在他身边的影子,马上缩回门里,毕竟他在外面有被围攻的危险。我往北走,去和秦楠汇合,北边树密,铁栏杆有个豁口,十五年前我俩钻过,昨天发现还在那。——不看了?秘书又冒了出来。我说:二中来的,没意思。秘书说:什么?我说:要是从技校摇人,能把脑浆子打出来。秘书说:看来真是校友,校长没认错人,您跟我来吧。
进了校长室,一个秃顶冲着我,抽完烟,他才跟着屁股底下的转椅,把脸扭过来:你什么单位的?我说:没工作。校长笑了:在读博是吧?我说:陈校长认识我?校长说:你是一中知名校友,高二拿了奥数一等奖,被保送北科大,你没去,高考报了北大,没考上,第二年上了清华数学系,对吧?我说:那两年盲报,便宜我了。校长说:老校长一直说,一中教出个女华罗庚,说的就是你。我说:老校长有心,我小时长得锉,放人堆里就没。校长说:中考全市第三十五,是不算拔尖儿,当年在你们一班,排到十名开外了吧?我说:记不住了。校长说:差不多,惠雨带出的班,每年全市前十,她最少占六个。我说:您有没有统计过,她每届学生的就业率、离婚率、自杀率?校长说:她只是个教数学的。所以呢?我说,只要能出满分,你就会保她?校长说:我知道,很多人看不惯惠雨,每年告到教育局的一大把,但这里面不应该有你。我说:惠老师做了什么,您不会不清楚吧?校长说:做什么?她能做什么?现在学校都是监控,学生不止一个手机,她要有什么出格的地方,照片、视频、录音早就放到网上了。我说:现在不是十五年前,我相信她没动手,不然学校不会赔那么点钱。校长说: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你碰见惠雨,成了数学家,你感谢过她吗?惠雨风光了这些年,现在摊上刘步,是她倒霉,是我当校长的倒霉,你嫌 20 万少,那是你不知道,这个钱学校一分没出,都是我和惠雨掏的。我当校长活该,你想想惠雨,她一个月加上班主任补助,才挣三千多,岁数那么大了,孩子还没上高中,你得给她留条后路啊。我站起来说:咱说不到一块去,别耽误您回家。校长说:你回去跟秦楠说,入土为安,再折腾下去,对刘步爸妈不是好事。我回过头:究竟还得逼死几个,学校才能重视?人没了,成绩有什么用?校长说:不是我要成绩,是家长要啊,惠雨不是一届、两届、偶然的好,她是每一届都好,你懂吧?
从学校出来,天已经黑了,秦楠不在面包店,不知道去哪了。路灯黯淡,街道坑洼不平,北风呼呼吹着,送我回到十五年前,挨了老惠的骂,不敢回家说。整件事最恐怖的地方,不是老惠逼学生,而是在她的高压下,真的出了好学生。这种繁荣盛景,给家长造成错觉:老师不让学生怕,净挑学生爱听的说,哄着学生玩,有什么用?还不如像老惠那样,出成绩,出名徒,每年有一两个跳楼的,有什么问题?只要跳的不是我儿子就行啊。
风里驶出一艘大船,很怪,但很眼熟。这是我从初二到高三,住过六年的家属区,刚才没认出来,是因为小区取消了门禁,塑料袋满天飞,地砖碎了一半,油田副业归地方后,物业已经弃管。但这艘两层的大船,夜里仍然神采奕奕,看起来将要启程。记得高中时,一层改成了自行车棚,二层一直是露天,平时大家晾被子,秋天晾白菜和大葱。大船后面,就是 16 栋,3 单元 601 没亮灯,我常坐在那窗台上,想跳下去会怎样。
上了大船二层,我看见秦楠坐在单杠上,还是十五年前她坐的地方。我说:怎么上去的?她说:扶我一把,我想下来。我说:你就为了这个哭啊?她啪地跳到我怀里:现在我特理解那个毕业二十年,回去打老师的,我也想揍老惠。我说:有件事,你不知道。高二晚自习,我拿公用电话,往她家打了一周。秦楠说:骂老惠吗?我说:你把我想得太伟大了,一周,一句话没敢说,电话通了就放录音,是一群大象在嘶叫,老惠还真害怕了,大叫着,老公老公,elephant,elephant!秦楠说:老惠会说英语?
是啊,初中四年,老惠闲得没事,考我们单词时,念的从来都是中文,卑微的和低下的,我老写串。现在想起来,不知道真打过电话,还是编出来骗自己的。
三
十一长假,我们唯一的进展,是拿到了刘思甄的家庭住址。刘思甄住滨江一号院,母亲在税务局上班,父亲以前是派出所所长,去年下海开了干洗店,干得很大,我家退休的老太太都办了卡,洗羽绒服才 9 块 9。我以为秦楠马上会去找她,但每天一碰头,她就带我去三舅家吃饭。三舅妈跟以前一样,边择菜边唠嗑,也不回避刘步,好像儿子在学校上学,晚上还能回来吃饭。三舅明显老了,每顿四两酒,我和秦楠喝啤酒陪着,提起我们高考那阵,他说:本来和孩子老叔说定了,中考完,送他去上海念高中。
每年有一两个跳楼的,有什么问题?只要跳的不是我儿子就行啊。
秦楠的老舅是学涡轮的,毕业后定居上海,秦楠当初报考复旦,也是奔他去的,可惜差了三分,掉档到第三志愿,让某 211 财经大学捡了便宜。大学开学第一天,秦楠给我打电话:你知道吗?《汉谟拉比法典》规定了性工作者的遗产该怎么继承。我说:时代特征吧,毕竟都不避孕。秦楠说:你是说比起法律,避孕套是更伟大的发明?我说:至少在父系社会。过了几天,她又告诉我:《汉谟拉比法典》只是现存的、比较完备的成文法典,这么多定语,一听就不牛逼。我说:法律系还讲这个?秦楠说:我倒想转专业,可这破学校连考古学都没有。我说:回来跟我一块复读吧。秦楠说:书我都卖了,七十三块六。混到大四,人家都找工作,她跑去日本交流,凑齐了日文版的《尼罗河女儿》,一年后回来,招聘季过去了,她直接回元市,成了待业青年,一个月才出一次门,宅家刷剧看动漫,也不多吃,控制体重,以每年 5 斤的速度胖起来。今年入秋,我给她找了个心理咨询师,但刘步出了这样的事,肯定顾不上了。
三舅妈拿起我的杯子,把剩的杯底嗦啰了:刘步学习没你们好,想着他老叔能帮着,考上复旦就好了,他们刘家人啊,死心眼,从老四开始,就要上复旦,老四没考上,就让楠儿考,楠儿没考上,轮到刘步了。要我说啊,这个复旦,不上也没啥,把儿子过继给老四,虽说是面儿上的,你三舅不舍得的。三舅说:我早就想开了,他去了上海,以后再出国,跟死了有啥区别?我又不是卖儿子,又不图他养我老。三舅妈说:我翻着个小字条,原来刘思甄要去上海学舞蹈。三舅说:到底是我儿,恋爱也谈了,没白死。我看秦楠,秦楠举着啤酒瓶,给自己满上,又给三舅妈满上,俩人干了一杯,又要满上,杯子顺着倾斜的桌面,碎在地上,三舅第一下没使上劲,第二下才把桌子掀了。
上尖的猪肉炖粉条,全兜在三舅妈腰上,三舅妈腰间盘突出,常年系磁石腰带,肉汤连着粉条,黏在磨光的磁石上,半天往下掉一根。我还没反应过来,三舅妈已经扑过去,把三舅从玻璃碴子里拖走。我听见她喊:我都说了,再生一个!刘步咱从小没养好,不爱说话,再生一个,你好好对他。三舅说:生你妈逼啊,你都四十几了?
这是最极端的情况,也是我每天去三舅家,都要做好的心理准备,但一般用不上。一般都是三舅妈说:中午吃饺子。我说:韭菜馅儿的?三舅妈说:行,在自己家不怕放屁。然后和我一人一把韭菜,择着择着,三舅妈就想起来:自打上中学,刘步就没回家吃过晌饭。我说:做题吧?是啊,三舅妈说,十一点半放学,惠老师只给半小时吃饭,十二点开始做数学题。我说:刘步成绩怎么样?三舅妈说:还行,没出过年级前五十。要说惠老师啊,带班真有一套,不光管她自己那科,英语、语文、物理、化学她都管。刘步告诉我,惠老师说了,中午做了数学,晚上就能倒出功夫学别的。
每当这时候,秦楠就要躲进厕所哭一会儿,她受不了这个。三舅妈不知道老惠是什么人,可以肯定,刘步没说过,老惠搓弄的羞耻感,让他在一切进行时无法发声,就像被家暴的人。晚上出来,我说:三舅妈不记得了?秦楠说:不记得是好事,明天不来了,去找刘思甄。我说:她还小,备不住比你还伤心。秦楠说:我知道。我说:咱没看见,但刘步是在她面前跳下去的。秦楠说:我不是找替罪羊,我知道我有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