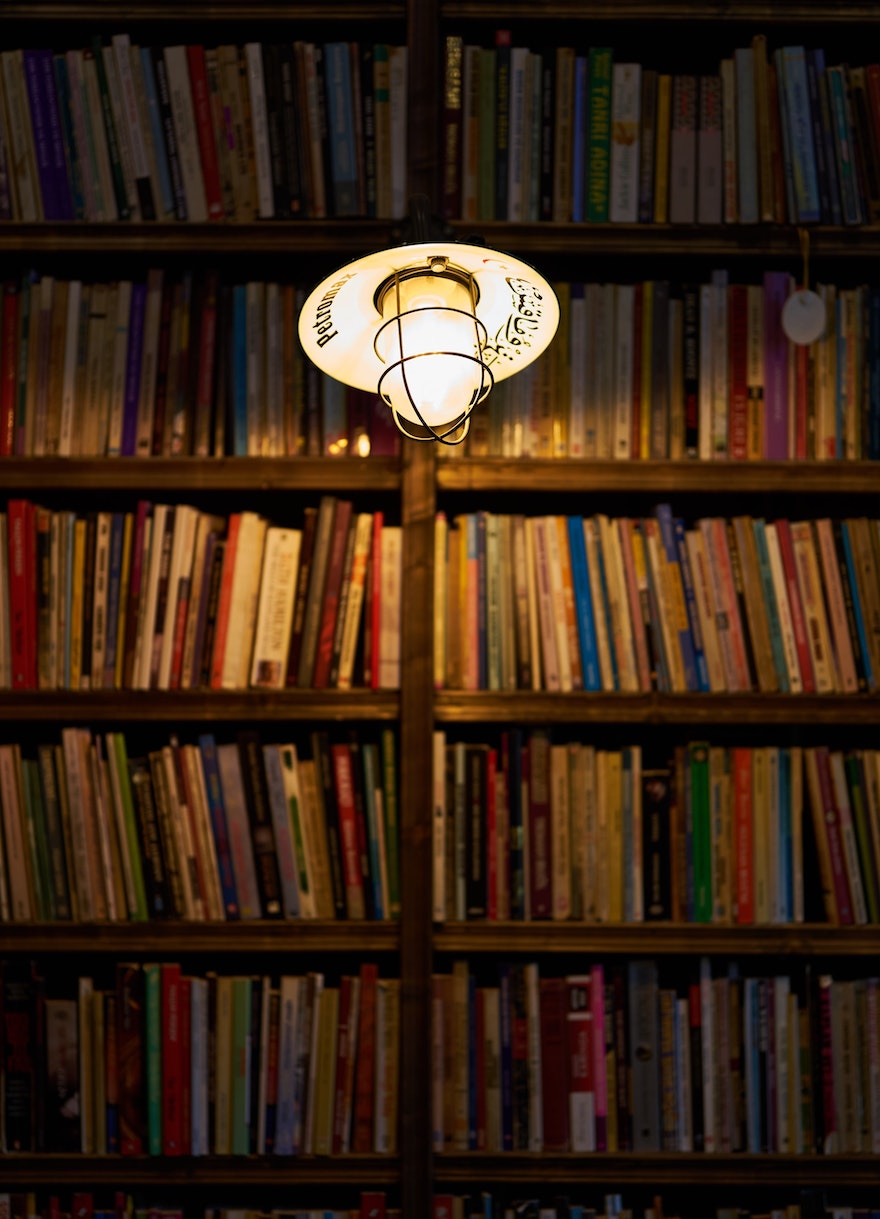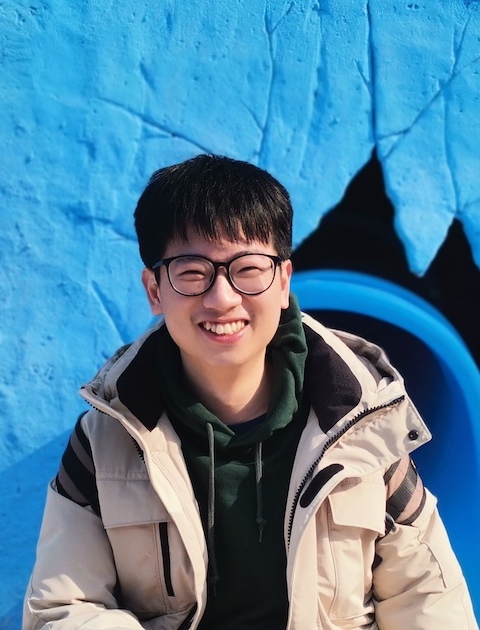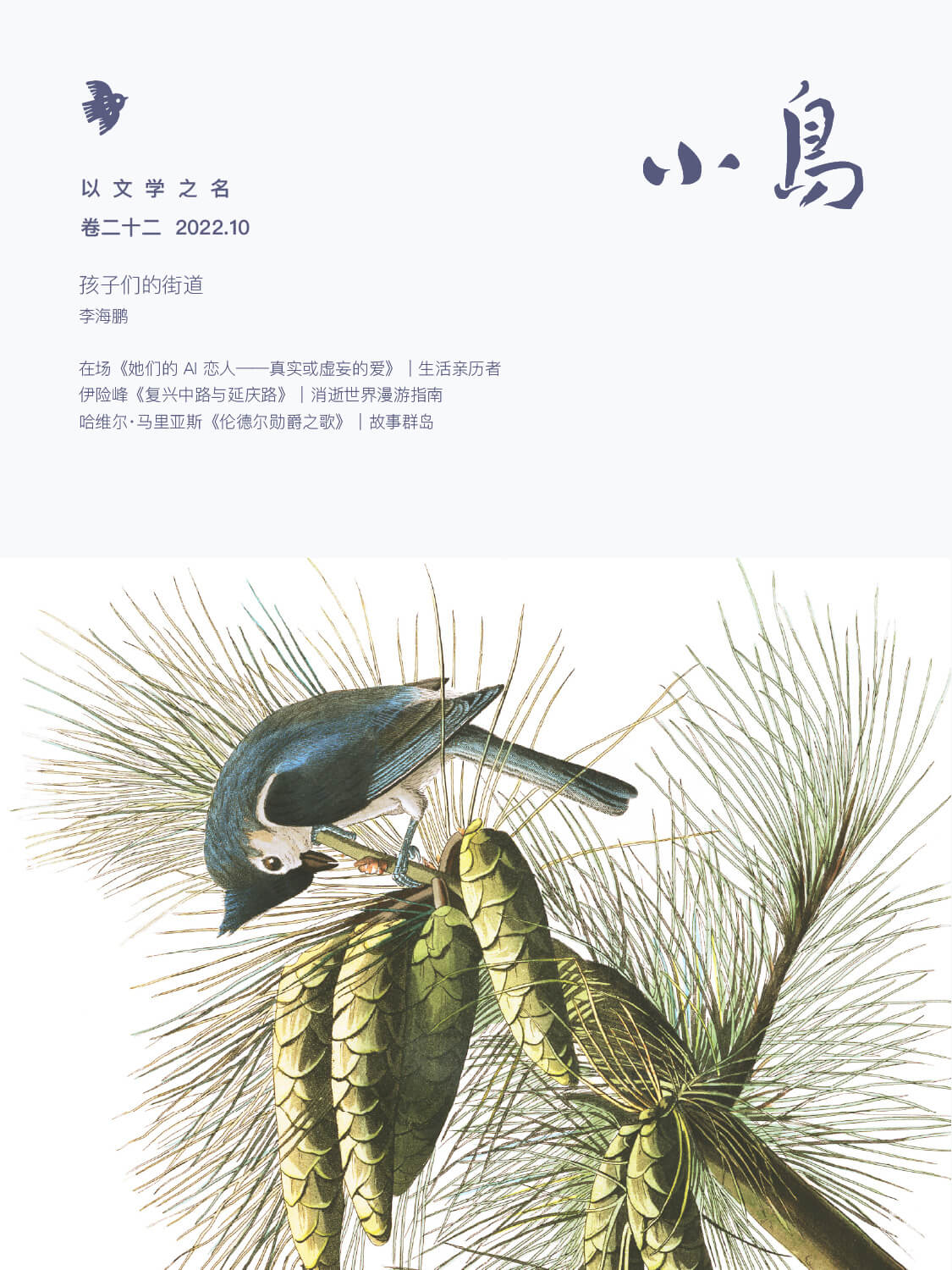9 月 16 日,中国作家余华凭借长篇小说《兄弟》获得俄罗斯“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文学奖”的最佳外语作品奖,奖金为税前 120 万卢布(约 13.7 万人民币)。在莫斯科大彼得罗夫大剧院的颁奖典礼上,余华以视频形式发表获奖感言,回忆自己于 2007 年 9 月前往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寻访列夫·托尔斯泰墓的场景。“列夫·托尔斯泰经历了朴素和震撼人心的一生,他长眠的墓地也是同样的朴素和震撼人心。”他说。
俄乌战争之际,余华接受俄罗斯这一奖项的决定引发许多争议。比如媒体人张弘认为,余华领奖的行为违背作家的基本良知和正义,也不符合现代公民的价值标准。他宣布,自即日起,抵制购买余华的所有作品,并呼吁广大读者响应;作家宋石男觉得,该奖项组织者与普京及其政府关系密切,余华接受奖项却未及时表达反战立场,对正义的追求被个人事务压倒,公共生涯令人惋惜地留下一个醒目败笔。但他不会呼吁抵制余华的作品,认为有点严苛。
也有人为余华辩驳,称该奖是个作品奖,“一部作品写完出版后,就获得了独立的艺术生命,拥有自由传播的权利,成为人类共同的精神遗产,其价值不会受作家的现实行为影响。二战期间曾经支持纳粹的诗人和哲学家,作品至今在全世界传播,享有很高地位,就是例证”。
不过,知识人在面对具有官方背景的奖项时,领取与否的确很容易被看其立场的表达。比如去年,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原本接受了有阿联酋官方背景的谢赫·扎耶德图书奖,但遭到《明镜周刊》等媒体的批评,认为哈贝马斯从一个被控镇压民众的专制君主制国家接受奖项,理应被视为与他长期坚持的原则相矛盾。随后,哈贝马斯拒领此奖,称之前“我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奖项与阿布扎比现有的政治体系有多么密切的联系”。
而且,在战争期间,文学艺术的角色和知识分子的责任本就是焦点问题。有意思的是,在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新闻稿中,余华认为自己获奖的原因是他写下了中国社会巨变中的人性。结合当下世界局势,他认为:“当世界陷入困境时,艺术和文学就会显得十分重要,因为艺术和文学能够让我们在别人身上看见自己,这是心灵和心灵之间的桥梁,也是病人和病人之间的安慰,当这个世界病了,我们所有的人都是病人,没有医生了,医生也是病人,可能病得更重。”
我们也在战争这场巨变中得以看到作家的人性。以托尔斯泰为例,1904 年日俄战争爆发之际,他就写过一篇《“悔改吧!”》的反战宣言。这篇檄文的中文译者们称,“托尔斯泰站在了一个普世人道主义者/基督教安那其主义者的立场上,用痛快淋漓的笔调揭露和痛斥了战争策动者(如当时的沙皇)的虚伪、荒谬和残暴,深入平民立场描写了战争对平民手足的残忍戕害。”
“因为揭露了这场不义帝国主义战争(有别于那些保家卫国之战)的丑陋面目,托翁这篇掷地有声的长文,在沙皇俄国国内只能一直以地下方式传播,1906 年和 1914 年两次正式出版后都被迅速查抄。如今,当我们再次被一个战争策动者拖至历史的十字路口,托翁文章中的一些论断读来不仅毫不过时,而且依然充满力量。”
余华获奖的 9 月中旬后,随着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的撤退,这场战争被一些人认为已到转折点,但俄罗斯核威胁的阴影仍在。知识人们也在发出自己的声音。10 月 6 日至 9 日,乌克兰最大的图书节——利沃夫图书论坛在现场和线上举行。论坛组织者认为这是一场反抗行为,是对限制言论自由和思想交流的挑战,也是全球变革的催化剂。活动参与者包括去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英国作家古尔纳、英国小说家尼尔·盖曼、加拿大作家阿特伍德、土耳其作家艾丽芙·沙法克、《人类简史》作者尤瓦尔·赫拉利、《东西街》作者菲利普·桑兹,还有不少乌克兰作家和学者,等等。
他们讨论的话题之一是,为什么文学在战争时期重要?比如英国医生、作家雷切尔·克拉克称,在正常生活破裂、损伤、动荡、恐惧、不安和不确定的状态中,讲述自己的故事具有巨大治疗潜力。在战争时期见证,可能危险、勇敢、鲁莽或挑衅,但也非常必要;叙利亚作家萨马尔·亚兹别克(Samar Yazbek)说,文学揭露战争的丑恶及其对人类命运的影响,总是着眼于未来。无论多么轻微,写下真相,为被压迫者伸张正义;乌克兰哲学学者弗拉基米尔·叶尔莫连科(Volodymyr Yermolenko)觉得,战争时期的文学是一种亵渎,因为战争的现实无法用语言表达,但它也是一种责任,我们有责任去说话,去见证,去忏悔,去作证。
赫拉利认为,大多数战争起源于某个诗人的头脑。驱使普京入侵乌克兰的是关于假想威胁的童话,以及对权力和荣耀的幻想。这场战争最终可以追溯到 1950 年代普京小时候喜欢的故事,以及俄罗斯儿童今天仍在学校学习的故事。但是,和平也始于某个诗人的心中,他能透过战争的硝烟看到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乌克兰记者捷季扬娜·奥加尔科娃(Tetyana Ogarkova)则称,我们写作和阅读是为了理解和创造现实。
加拿大历史学家玛格丽特·麦克米伦说:“我们需要问吗?战争让我们面对自己的死亡,以及人性中最好和最坏的一面。书籍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一战中,普通法国士兵订购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试图理解他们在战壕中的艰苦战争。二战期间,两本最受欢迎的英文书籍是《青山翠谷》(How Green Was My Valley)和《丧钟为谁而鸣》。你可能喜欢或讨厌圣·埃克苏佩里的寓言《小王子》,该书出版于 1943 年的黑暗日子,是有史以来世界上最畅销的书籍之一。虽然它以流浪王子的死亡告终,但也预示着智慧能找到,爱情最终会获胜。希望也很重要。”
还有什么值得想想……
01
9 月 16 日以来的伊朗抗议仍在持续,目前至少蔓延至伊朗的 30 个省份。在文化界,不少人都表示支持抗议,比如伊莎贝尔·于佩尔、朱丽叶·比诺什、玛丽昂·歌迪亚、伊莎贝尔·阿佳妮、夏洛特·甘斯布等 50 多位法国女性电影人和艺术家,通过剪掉自己的头发支持伊朗女性为自由而战,响应抗议的口号“为生命、自由与女性”;伊朗导演阿斯哈·法哈蒂称:“我邀请来自世界各地和各国的所有艺术家、电影制作人、知识分子,以及所有相信人类尊严和自由的人,通过制作视频、写作或任何其他方式,与伊朗强大而勇敢的男性和女性站在一起。”
半岛电视台报道,伊朗社会科学家曼苏尔·赛伊(Mansour Saei)认为,头巾问题之所以变成危机,是因为伊朗政权不顾周边环境和价值观的发展,仍然只强调传统并复制其传统价值观,从而失去了理解、接受现代世界及其价值观,以及与其进行交流和互动的可能性。新一代成长在不同于伊朗革命第一和第二代人的传统世界,其中很大一部分人已经远离主流,建立了自己的身份,挑战以宗教和社会传统为基础的价值观。
《纽约时报》称,目前的示威活动是伊朗自 2019 年 11 月以来最引人注目的抗议活动。当时,天然气价格上涨引发自革命以来范围最大的暴力骚乱。许多走上街头的抗议者是低收入人群,这些变化对他们的打击尤其严重。再上一轮抗议活动是 2009 年席卷全国的“绿色运动”,由中产阶级和大学生领导,他们走上街头,谴责时任保守派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为连任而舞弊。
要理解这些履发不断的抗议,可能得回到 1979 年伊朗伊斯兰革命才行。正如《好奇心日报》在 2017 年底到 2018 年初那场伊朗抗议时,刊发媒体人刘波撰写的伊朗转型文章所分析:“伊斯兰教本身存在着强烈的不承认个人权威、反对个人崇拜的倾向,这与最高领袖的至高权力存在着潜在的矛盾。而伊朗人口结构的变化,年轻人的增多和城市化的发展,都意味着对目前的权力结构会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
02
未来会有更多创作者走上陈可辛的道路吗?10 月初,Variety 报道称,电影人陈可辛创立了泛亚洲制片公司 Changin’ Pictures。该公司已从亚洲渠道筹集大量资金,旨在开发和制作原创内容,并向各平台推广和授权,不依赖 OTT 平台的制作资金、制作许可和编辑限制。随着全球对亚洲影视人才的日益认可和跨国 SVOD 平台的全球发行潜力,Changin’ Pictures 的目标是成为为流媒体观众提供优质内容的强大制作中心。
陈可辛去年曾在采访中称,自己未来的人生规划是要拍一些全世界都看的中文剧。现在全世界都在看韩剧,为何不看中文剧呢?韩剧的市场就是以前港产片的市场。而且,目前电影不是一个很能支撑作品的工业,但流媒体能给年轻导演提供更多机会。不过,外界一些分析认为,陈可辛这种转变不仅仅是出于个人规划和行业发展,还是中国电影市场环境近年的变化,空间缩小太多,不如干脆放弃,走上另一条路。
比如,Changin’ Pictures 的前五部剧集将在釜山电影节公开,其中一部是由章子怡出演的 The Murderer,正是此前在中国两度立项的电影《酱园弄杀夫案》。还有,几年前先叫《李娜》后更名为《独自·上场》的电影,现在音讯全无。这种境遇不是孤例。前段时间,田壮壮在纪录片中说自己的电影《鸟鸣嘤嘤》(改编自阿城小说《树王》)送电影局审查了两年多,没有任何意见。他也不知道怎样才能找到一个结果。
后来,一份拍完但没上映的电影片单在网上流传,包括陈冲导演的《英格力士》、曹保平导演的《涉过愤怒的海》,等等。最近,上个月我们写过的电影《隐入尘烟》也被下架,取消了在釜山电影节的展映,疑因展现的西北农村被看作批评中国脱贫成就。而今年国庆档的电影票房不到 15 亿,前三年的数字分别是 43.88 亿、39.67 亿、44.66 亿。当然,这种困境不只是影视,图书等创作领域皆是如此。
03
9 月底,以“三农”问题研究闻名的学者温铁军的一段视频采访引发争议。在采访中,他提出“人民经济”的概念,认为其具有四个特征——自主性、在地性、综合性和人民性。“因为是人民的,所以人民性有一个很重要的财产关系上的特征,就是全民所有制。看今天的中国,客观上已经形成占有相当份额的国有企业,人民对这些全民所有制的企业仍然拥有从财产关系到分配关系的基本权利,这些权利怎么体现是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重要内涵。”温铁军说。
这番言论引起向松祚、任泽平、马光远等经济学者的批评,认为温铁军反对改革开放,企图重返计划经济。“他所谓的自主性不就是闭关锁国吗?把外资企业和合资企业都否定吗?他所谓的在地性不就是画地为牢吗?自给自足吗?他所谓的综合性不就是把企业搞成大社会吗?他所谓的人民性不就是重新回到全民所有制的一大二公吗?……温铁军的胡说八道将改革开放全盘否定,以一些莫名其妙,荒唐怪诞的新词汇来欺蒙蛊惑!”向松祚说。
另一边,一些网友力挺温铁军,认为他的“人民经济”是希望老百姓从经济发展中收益,避免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而攻击温铁军的那些经济学者不过是资本代言人,为利益集团服务。
《联合早报》一篇文章称,有关“人民经济”的争论,似乎上升到两条不同发展道路的高度。但是,温铁军这段视频其实今年 5 月就放在网上,开始并没有多少人在意。过去一周因为几个网络知名度较高的经济学者齐声炮轰“人民经济”,突然爆红。“很难想象,官方将用模糊不清的‘人民经济’概念来取代多年行之有效的市场经济理论。这场‘人民经济’之争,也不过是立场不同的网民之间又一次口水战。这在中国舆论场上早已司空见惯。”该文写道。
04
9 月 25 日,历史学者秦晖做了一场“苏联式国家的‘测不准定理’”讲座。他以贝利亚、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等人的前后变化为例,称如果我们要从分析政治人物的经历和流派来预测苏联式国家未来的变化,很容易错,也就是所谓的“测不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这是这个体制可怕,但也不稳定的基本原因,那就是在这个体制下,所有的人都是戴着面具生活,谁都不可能真正认识谁,不知道明天会干出什么事来。不仅老百姓不知道当官的怎么想,这些亲密战友之间也都不知道对方怎么想。”秦晖说。
他认为,“这个体制是对传统价值观的巨大冲击,同时又是一场无神运动,它把人性中的超越性冲击得非常厉害,导致什么都可以做,没有任何底线。运动早期,你可以说一些人带有理想主义,但由于这种运动的运作机制是不择手段、优败劣胜,最后是真正有信仰的人被淘汰出局。所以这种体制随着时代演进,越来越变成一帮戴着面具的人执政,就像川剧变脸一样,说变就变。这是这种体制让人厌恶、可怕的地方。反过来讲,这也是这种体制发生变化的希望永远不会灭的一个理由。”
“这种体制没有一个是真正被群众运动推翻的,当然有些国家巨变时发生了群众运动,但这些运动成功都是因为上层发生了分裂。它不在乎人心所向,这也是‘测不准’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但问题在于,上层好像从来就会出问题。一个重要原因是它的合法性资源实在是太单一。那在党内斗争中,他们就有出牌现象,什么样的牌都可能出。仅仅从经验角度讲,我觉得这种体制的确是‘测不准’。因此,所谓的悲观、乐观,其实都没有什么根据。只要人们都做自己应该做的事,历史进步的概率还是可以扩大的。如果没有人努力,这个概率就不可能大。”
05
几件新冠疫情相关的事情值得记录。9 月 18 日凌晨 2 时 40 分,一辆贵阳往荔波方向的客车发生侧翻事故,造成 27 人身亡,20 人受伤,其中 45 人是隔离转运的贵阳居民;许多地区在放宽对游客检测或者隔离的要求,包括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日本、加拿大等,中国大陆成为仍在实行严格边境管制的唯一主要国家;一位因为过路被集中隔离 15 天的四川民众,写文讲述自己的经历,并起诉了市政府和卫生健康局;
国庆返京防控收紧,不少人因北京健康宝弹窗 3 等问题暂时无法返京;《纽约时报》的调查验证民众关于李文亮医生之死的一些猜测。该媒体获得的病情资料显示,2 月 6 日晚 9 点 10 分左右的心脏彩超报告显示,李文亮“心脏运动消失”。但是,医院领导层要求医疗团队使用人工肺,想向公众表明医院不遗余力抢救,不过最后是否使用,不得而知。2 月 7 日凌晨 2 点 58 分,医院宣布李文亮逝世。
06
几条文化新闻可以一看。德国作家朱迪丝·莎兰斯基加盟“未来图书馆”项目。该项目由苏格兰艺术家凯蒂·帕特森(Katie Paterson)发起,每年邀请一位作家创作,内容封存在奥斯陆 Deichman 公共图书馆,到 2114 年集结成册出版。此前受邀作家包括阿特伍德、克瑙斯高、沙法克等;曾入围布克奖的津巴布韦作家齐西·达兰加姆巴(Tsitsi Dangarembga)因发起和平抗议,要求政治改革,被该国法院判犯有煽动暴力罪;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石因豆瓣网友 @现实的乌托邦 对其著作《<正义论>讲义》给的差评,直接向警方报案,认为其诋毁名誉和人身攻击,做法备受争议。
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称,根据美国人格与社会心理学协会(SPSP)的新政策,他在年度大会上报告研究成果必须提交一份声明,解释他的报告是否以及如何促进公平、包容和反种族主义。海特觉得,大多数学术工作与多样性无关。这些强制性声明迫使许多学者通过编造、扭曲或者发明一些与多样性的微弱联系,背叛了他们对真理的准受托责任。因不满这一政策,他选择未来辞职。这一事件也牵出人们对学术和政治的争议。
纽约大学化学教授小梅特兰·琼斯(Maitland Jones Jr.)因为多名学生联署投诉其课程太难,给分过低,被校方解雇,引发争议。琼斯不认为自己对学生的标准太高,但校方认为这门课的退选率高,学生的评价也不佳。不少老师反对校方决定,认为这会侵蚀老师规划课程内容的自由,也削弱教师的教学方式。一些学生和家长也持上述看法。如何在教师授课自由和学生学习评价中找到平衡,是当代大学教育的棘手问题。这在中国也不例外。
07
年终迫近,各种奖项纷至沓来。比如诺贝尔文学奖颁给安妮·埃尔诺,认为“她以勇气和高度敏锐度揭示了个人记忆的根源、疏远和集体限制”。埃尔诺也成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法国女作家;诺贝尔和平奖表彰民间社会力量,得主分别是白俄罗斯被监禁的人权活动家阿莱斯·比亚利亚茨基(Ales Bialiatski),去年被俄罗斯当局强制关闭的民间社会组织“纪念馆”,以及乌克兰的“公民自由中心”。他们多年来一直倡导人们有权批评权力阶层并保护基本的公民权利。
美国国家图书奖公布决选名单,非小说类中,审视新冠疫情的《无法呼吸》(Breathless)、聚焦弗洛伊德一生的《他的名字叫乔治·弗洛伊德》(His Name Is George Floyd)等入围;小说类中,关于黑人女性的《帕尔马雷斯》(Palmares)、讲述酷儿和移民的《这一切都可以不同》(All This Could Be Different)和《巴比伦城》(The Town of Babylon)等在名单之列。
英国最具声望的非虚构图书奖——Baillie Gifford 奖公布初选名单,《暴力的遗产:大英帝国的历史》(Legacy of Violence: A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不安分的共和国:没有王冠的英国》(The Restless Republic: Britain Without a Crown)、《看不见的孩子:美国城市的贫困、生存与希望》(Invisible Child: Poverty, Survival & Hope in an American City)等 12 本书入围。
08
几部英文世界的新作可以留意。两位华裔作家,伍绮诗和李翊云,分别出版新作《我们失去的心》(Our Missing Hearts)和《鹅之书》(The Book of Goose);莱昂纳德·科恩的遗著《麻风病人的芭蕾舞》(A Ballet of Lepers)出版;曾获普利策奖的美国作家伊丽莎白·斯特劳特出了新小说《海边的露西》(Lucy by the Sea);70 岁的英国作家威廉·博伊德又写了本小说《浪漫》(The Romantic);曾写过《企鹅欧洲史》《希特勒传》的历史学者伊恩·克肖爵士新作探讨《个性和权力:现代欧洲的建设者和破坏者》(Personality and Power: Builders and Destroyers of Modern Europe);《耳语者》的作者奥兰多·费吉斯写了俄罗斯的千年史《俄罗斯的故事》(The Story of Russia)。
09
9 月 20 日,哲学家贺麟诞辰 120 周年,他建立“新心学”哲学体系,是新儒家的代表,同时也是哲学史和黑格尔哲学专家;10 月 1 日,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逝世 10 周年,他以“年代四部曲”闻名,也是为数不多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10 月 8 日,诗人茨维塔耶娃诞辰 130 周年,《小鸟文学》刊发《致一百年以后的你》以表纪念;11 月 21 日是连环画家贺友直诞辰百年,“小人书大智绘——贺友直百年诞辰纪念展” 已于 10 月在上海美术馆(中华艺术宫)一楼展厅面向公众开放;12 月 8 日是艺术家卢西安·弗洛伊德诞辰百年,英国国家美术馆于 10 月举办其特展“卢西安·弗洛伊德:新视角”。
10
9 月 11 日,作家哈维尔·马里亚斯因新冠肺炎引起的并发症逝世,他被看作西班牙文学的国宝,常出现在诺贝尔文学奖的赔率名单上;9 月 13 日,导演让-吕克·戈达尔在瑞士选择安乐死离世,他是法国电影新浪潮代表人物,拍摄有《精疲力尽》《蔑视》等;9 月 15 日,哲学家索尔·克里普克逝世,他是 20 世纪分析哲学最后一个标志性人物,著有《命名与必然性》等;
9 月 22 日,儿童文学作家、《“没头脑”和“不高兴”》作者任溶溶逝世,就在同一天,两获布克奖的英国作家希拉里·曼特尔也离开人世,她以历史小说“托马斯·克伦威尔三部曲”(《狼厅》《提堂》《镜与光》)闻名;9 月 29 日,希腊—罗马史学者保罗·韦纳逝世,他是当代法国重要的古代史权威,著有《古罗马的性与权力》《古希腊人是否相信他们的神话》等。
你现在也可以通过邮件订阅小鸟文学的 newsletter。
题图来自 engin akyurt on Unsp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