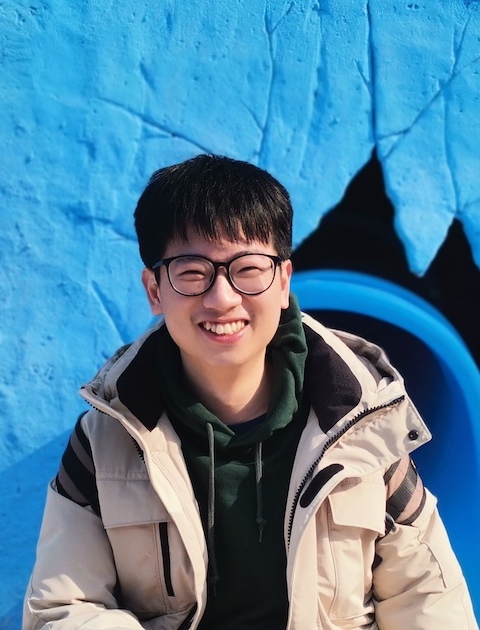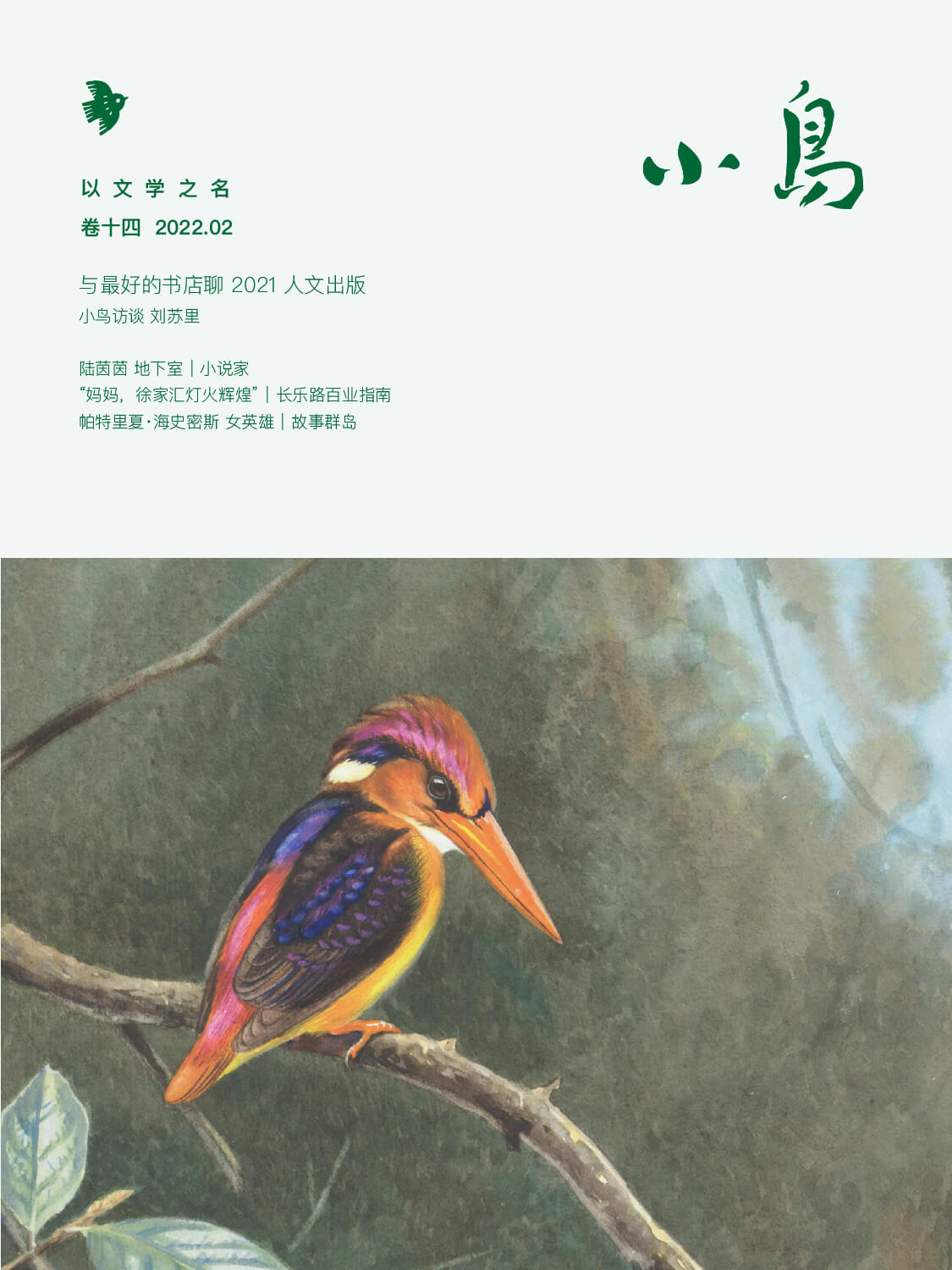“铁链女”事件中的思想争鸣
在中国春节和北京冬奥热闹喜庆地进行之际,江苏徐州丰县生育八孩的“铁链女”事件让我们看到了盛世繁华背后的一种冰冷现实。这起事件发端于社交媒体上的短视频,寒冬,一名生育八孩的女子被铁链拴在一间破烂砖房里,没穿外套,牙齿脱落,神情茫然。
许多网友对此感到震惊和愤怒,迫切希望知道真相。随后,纷繁复杂信息的逐步披露,当地官方前后不一的四份通报,不同人群的讨论和行动,将事件引起的关注和争议推到顶峰。2 月 17 日,江苏省宣布成立该事件调查组,公愤降温。2 月 23 日,调查组发布通报,但反响不一。
无论真相如何,至少就目前信息,“铁链女”事件从多个维度暴露出来的问题足以让我们做不少反思和行动。其中,以知识界为代表的思想争鸣,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发。
最先争鸣的是法学界,焦点为“是否应该提高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刑罚,实现形式上的买卖同罪同罚”。比如,中国政法大学的罗翔教授、黎敏副教授、陈碧副教授,北京大学的王锡锌教授,中国海洋大学的桑本谦教授等,都主张提高刑罚。另一边,北京大学的车浩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的柏浪涛教授等,则主张维持现状。
关于这场争论,北京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彭錞写了一篇综述《收买被拐妇女刑责之辩:他们到底在争什么?》,相对简洁快速地让我们进入讨论核心。他先指出双方争的不是什么,称“法律学人观点相异,但只是在术的层面,关于妇女人性尊严之道,他们没有根本分歧”。
那在他看来,争的又是什么呢?彭錞总结道:“归结起来有两大实质争点:如何用刑罚来准确界定和表征收买被拐妇女之恶?修法提高刑期是否有助于阻遏和解决拐卖妇女之恶?前者可简称为立法层面‘恶之度量’问题,后者为执法层面‘恶之矫正’问题。……‘提高派’认为包括收买者、执法者和旁观者在内的利益相关方会对刑责提高给出正反馈,而‘维持派’则预估零反馈甚至负反馈。双方关于人的社会想象存在根本差异:前者相信人性可被刑罚触动,而后者更悲观。”
彭錞认为,哪方更准确,应该而且可以从经验上作答。这要求法律学人跨出法教义学的“舒适圈”,引入社会科学方法,定量加定性地分析修法重刑究竟会产生什么实际效果。若结论是同时有利于减少收买和解救被拐,则可毫不犹豫修法;若结论是只有利于其中一个目标,则须通过民主审议抉择修或不修;若结论是两大目标均无法实现,则维持现状就是最佳选择。
接着,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仝宗锦对双方和彭錞的某些说法与论证都有不同意见,认为“提高派”似乎并未明确给出买卖同罪同罚(或者提高收买行为刑责)的内在理据,“维持派”的论证和说服力也不太够,彭錞主张引入社科方法并不容易施行,总体而言是否修法可能依然是一个政治决断的问题。
他从“法律如何对待人”这一视角表达观点——“我们究竟是把人当作劳动工具、生育工具、传宗接代工具,还是把人更视为生于天地之间的自由平等的有尊严的活生生的人本身,其中有着根本的不同”。
“如果说娶媳妇、有孩子等所谓刚需的满足是净收益,那么就需要在制度上提高其获取该收益的成本。另一方面,娶媳妇、有孩子的需求当然是重要的,但是能否通过不合道德、减损人类尊严的方式来获得呢?当然不能。我认为立法应该传递更为明确清晰、斩钉截铁的信号。这一立法上的改变,既是基于法律经济学和刑法政策的功利主义考量,同时也当然符合道德主义立场。立法当然不能脱离民情,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本土习俗,但当然可以而且应当倡导价值、引领风尚,从而塑造民情,面向未来。”
除了法学界,经济学者盛洪以某种外部视角发文称,“拐卖妇女儿童罪”在名字上就有缺陷,不该用“买卖”形容这种犯罪行为,这会使人产生幻象,更为接近的描述是出钱唆使人进行劫持妇女的行为。
“我的建议是,取消对拐卖妇女罪行的所有有关‘买卖’的说法……无论如何,当把本不存在的‘买卖’假象去掉以后,人们就不会将这种重罪与‘买卖婚姻’混为一谈,也不会对‘拐卖’与‘收买’的量刑不同而费心思,这两者的性质和程度一目了然:甲乙两人合谋绑架妇女,只不过做了分工,甲去绑架,乙付他钱,这钱不是被拐妇女的价值,而是甲的‘辛苦费’,甲绑架了妇女以后,用暴力胁持到乙处,将对该妇女的暴力控制转交给乙,乙随后对该妇女进行了‘情节特别恶劣的’强奸。这焉能不是令人发指的严重犯罪呢?”盛洪在文章中写道。
值得注意的是,不管哪方,都清醒意识到,单纯加重刑罚并不能彻底解决妇女拐卖问题。长期关注性别平等的香港大学法学院教授贺欣也同意这一点,直接另辟蹊径从“信息”的角度给出解决问题的思路。他认为:“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改变斗争策略——通过增加信息向上流动的渠道,从而减少甚至消灭拐卖妇女的现象。如何打通信息的阻隔,是国家法战胜‘民间法’的关键。”
比如“知乎上有帖子说,有地方成功消灭了拐卖妇女,就在于一方面重罚——将收买与强奸同罪,另一更重要的方面,就是给举报的村民高额资金,鼓励他们向上级公安提供线索。这招之所以有效,就在于收买媳妇很难不让邻居知道,而村民大多不会和钱过不去。通过报警获得信息,要比自上而下的巡查获得信息的成本低很多。上级巡查好躲,处处报警难防。一旦买来的妇女大多跑掉或者获救,就会形成良性循环,传达更明确的信息——买媳妇行不通。此时,村民就不会铤而走险,拿全部身家去做这种买卖。”
所谓“民间法”,其实也揭示出妇女拐卖绝不是单纯意义上的书本法律问题,而是行动中的法律问题,牵涉治理政治、经济发展、社会结构、文化观念等多个方面。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赵宏和清华大学教授郭于华关注的就是“铁链女”事件的公权力问题。
年年说谎,月月说谎,天天说谎,偶尔有一天他说了一句真话,谁能相信?谁敢相信?
赵宏聚焦“公共责任里的缺位者”,包括当地的民政部门、计生部门、村委会、妇联组织、残疾人权益保障组织、公安部门。“正是因为这些当地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集体噤声和漠视容忍,使得公众生疑该地是否早已形成一个买卖妇女儿童的犯罪链条,且有公权力参与其中,由此才使被拐妇女在办理户口、结婚登记、孩子落户等手续问题上一一掉入漏洞。”
“铁链女事件发生后,当地政府在舆论高压下缓慢地进行着调查且如挤牙膏一样放出前后矛盾的通报。这种应对方式使政府的公信力受到了严重拷问。而在最初爆出的视频中,如杨某侠一样神智模糊的被侮辱者,也会喊出‘这个世界不要俺了’。这句话戳中每个有良知的人的内心,同样是对某些公权力不作为的泣血警示。”赵宏在文章中写道。
郭于华在《任你说破了大天》一文中探讨的则是该事件暴露出来的“信任危机”或者“塔西佗陷阱”。她认为,目前我们陷入的是普遍存在的信任危机,而且是人际信任和系统信任的双重危机。前者表现为“杀熟”和“凌弱”;后者体现为如丰县案这类重大事件发生时公众对公权力、权威、专家、官媒、司法等系统的质疑。
“回到丰县一案,信任危机的形成机制颇具代表性。首先,一旦说出第一个谎言,就需要十个、百个谎言来圆;只要欺骗开始,谎言就如同水流顺势而下,无法回头。其次,谎言说惯了,殊难改正。比如一个说谎成性的人,年年说谎,月月说谎,天天说谎,偶尔有一天他说了一句真话,谁能相信?谁敢相信?能否跳出‘丰县陷阱’,能否使信任危机有所改变,要看公权力如何作为,也要看社会力量即公众能否作为。”
“信任的建立需要公众的主体性判断和自主选择,无论个人,还是机构或组织,要得到人民的信任必须有更为公开、公正、透明和高效的作为,这正是重建社会信任结构和良性社会生态的基石。从诚实面对每一个事件做起,从深入细致地调查分析开始,一步一步稳健前行。如此才能制止社会生态的恶化趋势,逐渐形成上中、下、层都享有基本的生存权利,都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的环境。……社会向好、人心向善仍需全社会共同参与,不懈努力。”郭于华在文章中写道。
以社会学者孙立平、经济学者李井奎为代表的观点和前述一些法律学者类似,站在现代性和普遍性的观点看待这一问题。只不过法律学者们更多提及人是目的而非手段,人的自由和尊严不可侵犯、物化和买卖,而李井奎等则强调经济或发展角度为代表的现代文明。当然,“现代”也有不少傲慢和值得反思之处,这里不展开。
比如李井奎认为,消除拐卖的治本之策是让城市文明进入乡村社会。“它从根本上折射出的,仍然是有些地区良治的匮乏。这一切的根源,就在于许多地区的财产权利得不到根本的保障,致使商业和制造业无法有效地从城市进入农村,改良地方治理,实现个人自由和安全。”孙立平则称,我们要告别贫困,同时还要告别贫困时代滋生的愚昧。
除了上述发声的学者,过往拐卖相关的研究和报告也引起许多关注和讨论,比如社会学者王金玲写的《中国拐卖拐骗人口问题研究》,主编的《被拐卖婚迁妇女访谈实录》《跨地域拐卖或拐骗》;民族学者陈业强的《怒江傈僳族妇女跨省婚姻迁移研究》;历史学者任思梅(Johanna Ransmeier)的《清末民国人口贩卖与家庭生活》(Sold People: Traffickers and Family Life in North China);据《中国妇女儿童状况统计资料》,2010-2019 年,中国公安机关拐卖妇女儿童案件立案数为 112703 起,其中共破获 20319 起拐卖妇女案;据《中国走失人口白皮书》,2020 年中国走失人次达 100 万,等等。
其中,普林斯顿大学人口学博士熊婉茹在 2021 年发表的研究中,通过分析中国 26 个省份从 2010 年到 2018 年的 1215 起拐卖妇女并强迫结婚的案件的相关数据,认为重男轻女的父权观念所导致的出生人口高性别比、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的性别迁徙、适婚女性短缺下底层男性面临的婚姻挤压,是导致以强迫结婚为目的的拐卖妇女现象的根本原因。
除了专门的学者,多样的群体或机构也在发声与行动,比如电影《盲山》导演李杨、生物学家颜宁、诗人廖伟棠、媒体人梁文道、杭州单向空间书店和西安方所书店的主题陈列,还有许许多多普通人的讲述,比如知乎答问“农村大量男光棍问题怎么解决?”,都给了我们动容与启示。
加强妇女权益保障,批评根深蒂固的父权观念,尊重人的权利、自由与尊严,等等,可能会是这起事件后人们凝结的共识。评论人维舟称之为“觉醒”,但或许这言之过早,因为我们经历过太多类似事件,寄予厚望,但最后并未如人所愿。毕竟,遗忘是人的常态,变革或进步是一场无比艰难和漫长的路程。
最后,回到思想争鸣的基础——事实与真相。正如《报道不足——“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中的新闻业症候》一文早前统计,“铁链女”事件的媒体报道主要集中在四次官方通报日期左右,此间的空白日期未有媒体发布稿件。而从报道内容来看,媒体几乎全停留在转载及解读官方通报,没有对事件的深度报道甚至详细报道。
是因为机构媒体不愿报道吗?前媒体人(这次还有个词值得品读,叫“前调查记者”)唐建光在文章《关于丰县的朋友圈》中写道:“作为前媒体人,知道只要派出一组记者,分赴丰县、四川、云南,解开谜底并不太困难。然而,今天只能坐看政府‘权威发布’、网友网上‘破案’(似乎只有自媒体到了丰县),朋友圈喊声震天。……多数人只能在信息泥沼中,如盲人摸象,凭借自己得到的一点,激情和焦虑地相信或否定。甚至一点在手,真理我有。……丰县的锁链,盖过奥运的光环,恐怕是十年以来最惨的宣传滑铁卢。官方摧毁了媒体系统,以为从此可以权威发布号一统江湖。然而正常的信息生态被破坏之后,更多人选择‘我不相信’。”
还有什么值得想想……
01
中国的归化运动员并非今年的新鲜事,但北京冬奥会上以谷爱凌、朱易为代表的 30 名归化运动员让这个议题广泛进入大众视野。一边是赢得金牌后成为明星和爱国英雄的谷爱凌,但她的名字并不在美国国家档案局放弃国籍人员的名单上;另一边则是摔倒引发嘲讽的朱易,评论者称她“脸都不要了”、“摆烂”、“尴尬”。如何看待体育和爱国?归化运动员会改变中国人的定义吗?看起来,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为代表的中国国籍血统论似有松动痕迹,但一些网民的前提好像是要拿金牌才算是中国人,才称得上爱国?
02
疫情爆发以来,各地防疫举措的成败得失一直是争议焦点。虽然没到盖棺定论之时,但新近发生的几件事值得关注。一是 2 月 20 日,经过为期三周的占领,抗议强制接种疫苗规定的加拿大卡车司机们的行动被迫终结,191 人被捕,76 辆车被拖走;二是受加拿大抗议行动影响,澳大利亚、新西兰、法国都发生了类似反对新冠限制的抗议;三是丹麦和英国取消新冠限制;四是中国香港的“动态清零”政策似乎失效,疫情更加严峻。
03
美国博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Edward O. Wilson)于 2021 年底去世,但如何评价他的贡献与不足,争议远未结束。争鸣焦点来自威尔逊去世后,《科学美国人》发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副教授莫妮卡·麦克雷莫尔(Monica R. McLemore)的文章《爱德华·威尔逊的复杂遗产》(The Complicated Legacy of E. O. Wilson)。该文章认为威尔逊带有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想法,一些人认为这是抹黑或误读这位伟大的博物学家,另一些人则赞同麦克雷莫尔的观点,还提出威尔逊和一名种族主义心理学家的通信,说是新证据。
04
2 月 13 日,Twitter上一则关于耶鲁大学教授詹姆斯·斯科特和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关系引发争议。斯科特称,他曾经帮助 CIA 在若干国家收集学生运动情报,而且提到他在印尼遇到的许多共产主义学生运动领导人在 1965 年的印尼“九三零”事件中惨遭杀害。如何看待斯科特的行为?怎样思考冷战和学术的复杂关系?微信公号“无知路上”的作者吴衢做了一番考查和探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椰壳碗外的人生》中对美国区域研究历史的回顾也可补充参考。
05
畅销书《当你像鸟飞往你的山》的作者塔拉·韦斯特弗在 2 月发表的文章《我不是“美国梦”的证明》(I Am Not Proof of the American Dream)中反驳了一种对她的常见误解,称她的故事并不是关于如何通过勤奋与坚持最终实现美国梦,而是一个相对健康的教育体系如何为穷困学生留出一条进阶之路。她认为在目前美国的教育体系下,穷学生已经没有这种机会。
这本书在中国也非常畅销,可以放进这几年中国积极引进有关反思美国教育的图书脉络中理解,比如《出身》《我们的孩子》《娇惯的心灵》《精英的傲慢》《爱、金钱和孩子》《寒门子弟上大学》,背后折射出中国社会对教育公平和阶层流动问题的焦虑与担忧。
06
这些年,国外影视进入中国,或主动或被动都要做些“本土化”删改。2 月,美国情景喜剧《老友记》回归中国流媒体服务平台,不过遭遇编辑删减,包括涉及同性恋场景,这让一些观众感到不满。类似的,1 月,腾讯将电影《搏击俱乐部》经过审核的版本上传到其流媒体平台,片尾强行插入顺应体制的完满结局。这一做法引发争议,随后腾讯悄悄撤下这个版本,恢复原版结局。
如果说《老友记》和《搏击俱乐部》是被动删改,那么新书《红毯:好莱坞、中国以及文化霸权的全球斗争》(Red Carpet: Hollywood, China, and the Global Battle for Cultural Supremacy)聚焦的故事则是主动删改,讲述好莱坞的卑躬屈膝和中国软实力的崛起,比如《碟中谍 3》《007:大破天幕杀机》等都有应中国要求的删改内容,还有一些电影,如《变形金刚 4:绝迹重生》,则会增加讨好中国人的情节,让中国飞机从机器人劫掠中拯救香港,而非美国飞机。
07
因为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对言论自由的保护,美国政府无权审查或禁止图书出版。但是,在民间,任何个人或团体若认为一本书不适合阅读,可向学校或图书馆提出下架要求。这些被要求在学校或图书馆下架的书在美国语境内称为“受到挑战的书”或“禁书”。每年,美国图书馆协会还会公布“禁书”排行榜,让公众了解学校和图书馆的情况与思潮变化,像《了不起的盖茨比》《杀死一只知更鸟》《人鼠之间》《使女的故事》等名著都曾被挑战。
但是,最近有所不同。《纽约时报》的报道《禁书在美蔓延时》(Book Ban Efforts Spread Across the U.S.)就梳理了变化,称在美国学校,挑战关于性别和种族身份认同的书籍并非新鲜事,策略性和政治化的行动才是,目前就是如此。
看起来,这些青少年远比那些自以为是禁书的成年人智慧和成熟。
比如在怀俄明州,检察官考虑起诉图书馆员工,因为该图书馆储存了像《Hi,和孩子轻松聊聊性吧》(Sex Is a Funny Word)、《同志之书》(This Book Is Gay)这样的书;在俄克拉荷马州,一项禁止公立图书馆保存有关性行为、性\性别认同书籍的法案被提出;在田纳西州,一学区的董事会投票决定将获普利策奖的图像小说《鼠族》(Maus)从八年级的学生课程中删除,因为其中涉及裸露和脏话。
《纽约时报》称,全美各地的家长、活动家、学区董事会成员、立法者正以几十年从未见所见速度挑战书籍。据美国图书馆协会,该组织在去年秋天收到“前所未有”的 330 份挑战申请,其中每份申请可能囊括多本书籍。
根据教育工作者、图书管理员和言论自由倡导者等反对禁书人士的看法,这种改变不仅仅是频率和数量,更重要的是背后的策略和场所变得政治化了。在社交媒体的帮助下,保守团体试图将挑战推向议会、执法和竞选,尤其今年还有中期选举。
在支持禁书那一边,有观点认为父母有权挑战一本书是否合适,比如一些书籍涉及口交等性行为的内容,可能对小孩产生不利影响。而且如果父母担心某件事,政治也需加以关注, 2022 年是父母投票的一年。
关于禁与非禁的争议,除了新的政治化改变,相比过去,两方的成年人在观点上似乎并没有给予多少新的见解。在结果上,那些被禁的书也毫不意外地成为畅销书,比如《鼠族》进了亚马逊畅销榜,《大西洋月刊》盘点了一份推荐书单《阅读那些学校想禁止的书》(Read the Books That Schools Want to Ban)。2 月 16 日,企鹅兰登书屋 CEO 马库斯·多勒(Markus Dohle)还宣布向言论自由组织美国笔会捐赠至少 50 万美元,以对抗当前美国的禁书行为,认为这与美国民主的未来息息相关。
最有意思的是未成年人的声音。比如《卫报》报道了宾夕法尼亚州一个禁书俱乐部的青少年们。该俱乐部成员年龄在 13 到 16 岁之间,每两周聚会一次,阅读和讨论美国受到挑战的书籍。他们称:“成年人在禁书,但他们没有征求我们的意见。”无独有偶,《纽约时报》也刊登了各地青少年对于禁书事件的看法,异常丰富。看起来,这些青少年远比那些自以为是禁书的成年人智慧和成熟。
08
2 月,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称,历史学者何兆武的遗作《上班记》将于 2022 年 4 月在该社出版。文靖在序言中写道:“《上班记》十几年前就写好了,因为聊的时候都混在一起,和《上学记》几乎同时完成,最多只差了半年。何老嘱我先别发表,‘因为有的人还活着,说了会惹麻烦’。的确,《上学记》给他惹了一些麻烦,某甲、某乙不依不饶。何老天生从来就不喜欢与人争,听了只是点点脑袋,用一种‘我也可以理解’的语气,说:‘冯友兰的姑娘有不同的意见,不过……’不过,从来他没有公开回应,就算别人敲锣打鼓吵翻天,他也任他们说。”
除了《上班记》,还有两本英文新书受到关注,一本是讲述东德秘密警察斯塔西(Stasi)故事的《斯塔西诗歌圈:试图赢得冷战的创意写作班》(The Stasi Poetry Circle: The Creative Writing Class that Tried to Win the Cold War)。在核战争的阴影下,从 1982 年春到 1989 年冬,一群斯塔西每月下午四点到六点在柏林聚集一次,学习诗歌、韵律和修辞的课程。该组织在内部被称为“契卡写作圈”,7 年时间内制作了两本诗歌选集。
作者菲利普·奥尔特曼(Philip Oltermann)找到了这个斯塔西诗歌圈的一些成员采访,并结合档案材料,告诉我们这是当时东德希望通过诗歌打击资本主义,赢得文化战争的努力。不过,当斯塔西们沉浸在诗歌,陶醉于想象的模糊时,结果却适得其反,政权固有的意识形态受到挑战与质疑。
另一本是《安静之前:论激进思想的意外起源》(The Quiet Before: On the Unexpected Origins of Radical Ideas),《纽约客》、《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多家媒体都刊发了书评。作者高尔·贝克曼(Gal Beckerman)通过对几个世纪和不同国家社会运动的研究发现,简单的谈话和思考行为中蕴含力量,我们说什么,以及如何说,将决定激进想法是否能改变世界。
他探讨的案例包括 1635 年法国开启科学革命的通信、1839 年英国关于投票权的请愿书、1935 年尼日利亚的纳姆迪·阿齐基韦(Nnamdi Azikiwe)和报纸、1992 年美国为女性发声的杂志、2011 年的埃及和社交媒体,和最近的新冠以及“黑命攸关”运动等。其中,《纽约书评》刊发了新书关于 1968 年苏联的一章,讲述诗人纳塔莉亚·戈尔波涅夫斯卡(Natalya Gorbanevskaya)的故事。她是萨米亚特(samizdat)的代表,一生象征着一个由诗人、思想家和活动家组成的网络,敢于挑战极权主义国家所取得的成就。
09
2 月 6 日,李文亮医生逝世两周年,许多中国人仍会想起他和疫情早期的回忆;2 月 19 日,邓小平逝世 25 周年。站在今天这个节点,如何看待和继承他的遗产,再次成为一个话题;2 月 24 日,胡适逝世 60 周年,《小鸟文学》刊发了纪念文章。除此之外,最近几年,以江勇振的《舍我其谁:胡适》(第四部,国师策士,1932-1962)为代表的研究热衷批评晚年胡适在政治上的表现,认为其软弱,但黄克武去年出版的《胡适的顿挫:自由与威权冲撞下的政治抉择》则希望人们体认到 20 世纪中国知识分子面对威权的艰苦与坚持自由理想之可贵。
10
2 月,波兰语翻译家易丽君(1934—2022)去世,她译有维托尔德·贡布罗维奇、亚当·密茨凯维奇、奥尔加·托卡尔丘克等人的作品;法语翻译家罗新璋(1936—2022)去世,他深受傅雷影响,译有《红与黑》等;媒体人曹景行(1947—2022)去世,他长期从事时事评论,父亲为民国报人曹聚仁(1900—1972);美国出版人杰森·爱泼斯坦(Jason Epstein,1928—2022)去世,他是《纽约书评》创办人之一,兰登书屋前编辑总监,曾发起经典书籍的“平装本革命”;美国社会学者、活动家托德·吉特林(Todd Gitlin,1943—2022)去世,他认为学术与政治从来不是割裂的,深度参与 1960 年代的社会运动,著有《新左派运动的媒介镜像》等;美国医生、人类学者保罗·法默(Paul Farmer,1959—2022)去世,他是推动全球公共卫生平等化的先驱,非虚构著作《越过一山,又是一山》曾讲述他的故事。
感谢阅读,如果你有其他建议,请邮件 info@aves.art 与我们沟通。
题图图注:当地时间 2 月 24 日,乌克兰东部卢甘斯克地区,一名妇女和一名儿童向巴士的车窗外观望。图片来自视觉中国